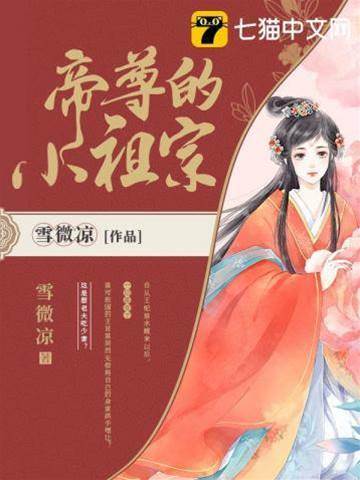《公主在上:國師,請下轎》 第220章 香豔刺殺,陡生驚變
天澈宮,蘭陵泉,波湧,春無邊。
泉池兩側蔓延在水上的枝葉,正開滿繁花。
花蔭下,人秀可餐,剔的,染著水珠,在日下如玉般瑩潤。
泉中的饕餮盛宴,是帝王的盛宴,是憫生的盛宴。
十年十壺海皇,再加上以采補之法善用八千後宮,十年時,人非但不老,反而比之從前的清瘦,更顯英武,彩滿。
他半倚在水中的玉床上,拈著犀角杯,看著滿池嬪妃水中嬉戲,有意無意地在他面前賣弄風姿。
環燕瘦,活生香,看得久了,卻有些百無聊賴。
忽然,那水中一聲巨響。
驚得鶯鶯燕燕尖著湧向憫生,“君上!有水怪啊!救命——!”
蘭陵泉中央,嘩地站出一個人來。
一紅袍了個通,實又起伏分明的子,一張魂牽夢縈的臉。
憫生擱下犀角杯,出許久不見的笑,聲音依然如從前般清雅好聽,“阿蓮。”
蕭憐看看對面,滿園活蹦跳的生鮮,圍繞著一個裹著浴袍,袒膛,的憫生,正用好奇、吃驚、探尋的眼看著。
再看看自己,正渾地站在人家澡堂子中央。
紅,你還真是會選地方!
所謂靈氣最盛,最易開啓巫陣之,竟然是蘭陵泉!
而且,還趕了個人家全家一起泡湯的好時候!
趁人沒穿服殺人,是不是有點太不要臉了!
蕭憐將心一橫,算了,管你們穿沒穿服,我沒時間!
也懶得多說一個字,左手殺生鏈揚起,從水中如一尾巨大的紅鯉般躍出,直取憫生。
憫生沒想到會來,本就驚喜,如今見面就殺,倒是更是驚喜。
他擡手推開邊的人,卷了滿的薄薄白袍,接下殺生鏈一招。
Advertisement
“十年不見,如此相逢,真是別開生面。”
他袍的廣袖揚起,掀起水珠,如一道水簾,在斑駁的日下,揮灑如水霧,池上立時顯出一道若若現的彩虹。
蕭憐一言不發,只是招招殺機。
憫生十年前坐在椅上事,能耐本就深不可測,這十年,又非虛度,此刻功力增長幾近駭人,全未將的殺招放在心上。
“阿蓮,那日我親自率海王艦隊去接你,你卻不肯跟我走,如今,為何又自己來了?”
他像是不知要殺他,只是看著從銀發到紅都,發著狠勁兒,咄咄人,像只齜牙爪的小母。
按照原本的計劃,該是五人合力刺殺憫生,而如今,卻只有一個人。
蕭憐咬牙,拼了!
殺了他,東煌群龍無首,陷混,勝楚帶著人大軍,就可以從海上長驅直。
兩個人打得水花燦爛,蘭陵泉本就不大,見到有人行刺駕,滿池子的屁人,尖著胡找裳擋住要害,對著外面喊,“救駕!有刺客!快來人救駕!”
“閉!”憫生喝止,“全都滾出去!”
他擰了蕭憐的手腕,再放開,由著繼續施展,“過去,從未舍得與阿蓮手,如今看來,卻是錯過了許多!”
蕭憐狠狠甩出殺生鏈,麒麟拳劈面而去,雖用盡全力,卻像是千斤重錘打在了棉花上,完全起不到半點作用。
不覺間,出一點煩躁,被憫生犀利的雙眼立刻捕捉到,“阿蓮是知道我明日要駕親征,特來相送?”
“送你下地獄!”終于說了第一句。
憫生招招讓了幾分,清朗的聲音有些寂寥,“十七年前,我就已經在地獄了,阿蓮。”
他與錯而過之際,手掌帶著水鏈,在的臉頰上輕輕掠過,“阿蓮,我所做的一切,都是因為你,可在你心中,可曾有過一星半點我這個憫生哥哥?”
Advertisement
蕭憐埋頭進攻,不能聽,聽了會心,卻依然忍不住喝道:“你背叛了他!”
“是他先棄了你!棄了我!棄了我們所有人!”憫生的聲音,溫了一份,怨恨多了一分,“他只為自己洗清青白,將你扔在神皇殿!溫庭別是不會放過你的!我求他讓我帶你走,可他卻不答應!如果當時,我能帶你走,木蘭樹下的一切,都不會發生!”
他攥住殺生鏈的中央,將拉到前,“阿蓮,我曾跪在地上,為你苦苦哀求,可他本置若罔聞!他害怕我將你帶走了,就再也尋不回來!他要將你控制在掌之間,哪怕是死,也要歸在他的名下!可我不同,我只要你解,你過得快活,至于你邊站著的是誰,枕邊睡著的是誰,都無所謂!”
“你沒資格將這一切歸罪于他!當初是你慫恿溫庭別將我上絕路!”
“沒錯!我是做了!可你若不死,又何來後面的自由?又如何能擺聖的命運?阿蓮,我早就為你準備好了一切!就算後來沒有勝楚,我也會親手為你召喚方寸天,將你複生!”
“就憑你?你有資格請下方寸天嗎?”
“只要是東陸的皇帝,就有這個資格!這東陸真正的皇帝,始終都是我!”憫生握著殺生鏈的手,又向自己這邊了一分,“阿蓮,你重返西陸後,我在背後為你籌謀多,瓊華所做的一切,都是經我授意,如果沒有我,你今日又如何立在此!”
他定定看著,眼中全無半點悔意,“阿蓮,你在西陸的每一天,做了什麽,我都知道,我時時刻刻看著你,我只要你好。”
蕭憐用力想搶回殺生鏈,“所以你在我與他大婚之際,勾結鮫人,洗神皇殿,數百海王艦,集火神都!這就是你要我好?”
Advertisement
“那是因為你終究嫁了他!”憫生眼圈有且泛紅,聲音的強調有些,“你嫁了他!他勝楚憑什麽自詡為神!他憑什麽就能得到一切!我偏要毀了他的一切!”
“憫生!你這個瘋子!”
“我早就瘋了!我從一開始就是個瘋子!一個誰都看不見的瘋子!”
兩人立在水中,僵持不下,這時,外面傳來一個子的聲音,帶著鼻音,滿是磁,“君上何在?”
憫生眉頭一皺,擡手強行將蕭憐給按進水中。
外面進來的是湘九齡,回示下,後跟來的太監宮將蘭陵泉中瑟瑟發抖的嬪妃們都裹了大氅,接了出去。
之後全不顧男之嫌,看向立在水中的憫生,“君上,刺客呢?”
憫生淡淡道:“死了。”
“呢?”
“化了。”
湘九齡冰冷的眼將蘭陵泉掃視了一周,一片淩糜爛。
“采補之法,的確可以延年益壽,可君上如此放縱,并非良方。”
憫生水下摁著蕭憐的手,在頭頂輕輕了一下,“國師良言相勸,本君記住了,以後必當節制。”
他說著,整個人沒水中,了蕭憐的下,直接將自己的覆在的上,蕭憐想要掙紮,卻被他摁住。
兩合在一起,卻只是渡了一口氣,沒有半分多餘的作。
稍後,憫生又重新浮出水面,作出頗為這水中溫暖的模樣,“國師還有什麽事?”
湘九齡卻全然沒有要走的意思,“本是前來護駕的,現在看來不必了,不過,本座還有一個好消息,要告訴陛下。”
“國師請講。”
“駕親征這件事,陛下不用去了。”
憫生神一怔,水下的蕭憐也是一愣。
湘九齡背著手,在水邊往複逡巡兩步,“勝楚的艦隊,本就沒有來東煌。”
“什麽?”憫生一驚,手中按著的蕭憐了,又被他重新按住。“他去了哪裏?”
猜你喜歡
-
完結55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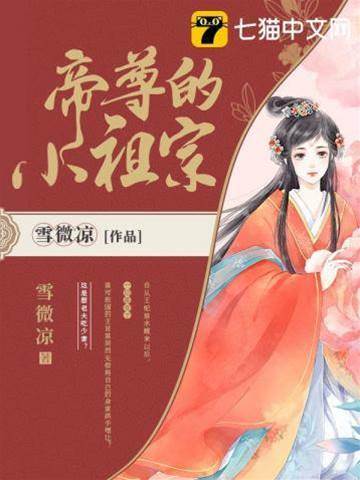
帝尊的小祖宗
自從王妃落水醒來以后,一切都變了。富可敵國的王首富居然無償將自己的身家拱手相讓?這是想老夫吃少妻?姿色傾城,以高嶺之花聞名的鳳傾城居然也化作小奶狗,一臉的討好?這是被王妃給打動了?無情無欲,鐵面冷血的天下第一劍客,竟也有臉紅的時候?這是鐵樹…
99.6萬字8 11327 -
完結157 章

農家惡婦
何娇杏貌若春花,偏是十里八乡出了名的恶女,一把怪力,堪比耕牛。男人家眼馋她的多,有胆去碰的一个没有。 别家姑娘打从十四五岁就有人上门说亲,她单到十八才等来个媒人,说的是河对面程来喜家三儿子——程家兴。 程家兴在周围这片也是名人。 生得一副俊模样,结果好吃懒做,是个闲能上山打鸟下河摸鱼的乡下混混。
48.4萬字8 8137 -
連載636 章

此夜逢君
繼母要把她送給七十歲的變態老侯爺,蘇禾當夜就爬上了世子的床。一夜春宵,世子惦上了嬌軟嫵媚的小人兒。寵她、慣她,夜夜纏綿,但隻讓她當個小通房。突有一日,小蘇禾揣著他的崽兒跑了!他咬牙切齒地追遍天下,這才發現她身邊竟然有了別的男人……怎麽辦?當然是抓回來,跪著求她騎自己肩上啊。
116.3萬字8.18 2279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