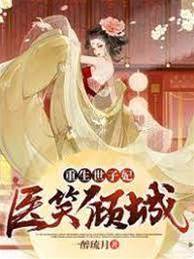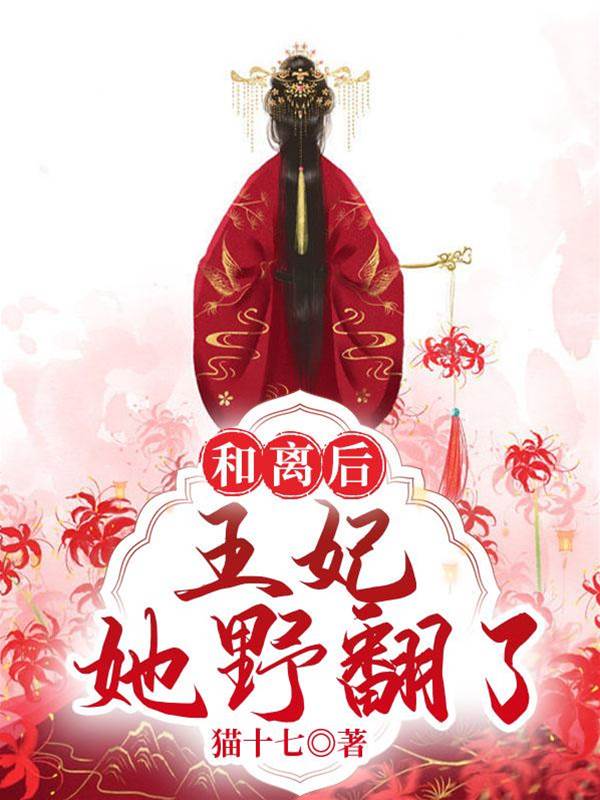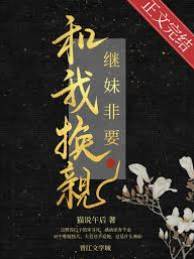《折竹碎玉》 第222頁
但若崔循發話,分量自是不同,便是再怎麼不願,也只能應下。
因飲酒的緣故,崔毅臉泛紅,眼瞳也不似平日那般清明,仿佛已經被酒氣浸,毫不避諱地看著面前的崔循。
崔循神寡淡道:「這等事終究要講究緣分二字。既如此,若執意強求,豈非傷了福澤?」
崔毅了,還再說,被崔循清冷的目掃過,倒似被當頭潑了盆冰水,冷靜下來。他不敢辯駁,只乾應了聲「是」。
崔循也不再多留。
略沾了沾酒,算賀過喜,便離席回房。
這時辰,蕭窈還未從學宮回來,山房自是雀無聲。
崔循便不曾回臥房,只在前頭的書房,隨手翻看蕭窈這些時日看的書。
也忙得厲害,這冊講史的書斷斷續續看了近半月,也沒看完。其中夾著片秋日裡銀杏葉做的書籤,算不得緻,但是自己看中撿回來製的,一直用著。
難得有這樣清淨的時候,崔循卻驟然發現,自己靜不下心。
哪怕是他用了這麼些年的書房,也點了慣用的香,卻依舊難以專心致志看上幾頁書。總時不時走神,想著蕭窈此時應在何。
他知道蕭窈的安排。
想要在蕭霽歸程時出破綻,螳螂捕蟬黃雀在後,看看能否釣上條魚來。
不會當真拿蕭霽冒險,返程的車駕中,會是扮作蕭霽的侍衛。
Advertisement
這時辰,應當已經塵埃落定。
今晨,他著意叮囑蕭窈「早些回家」,興許過不了多久輕快的腳步聲。或是雀躍地同他講,今日事,又或是同他抱怨自己白費心思。
無論是哪種形,他都已經在心中擬好了說辭。
可臨近黃昏,暮四合之際,來的卻是沈墉。
「公主遣臣來告知您,諸事順遂,不必擔憂。」沈墉躬抱拳,又道,「刺客悉數擒獲,太子殿下無虞,方才已由臣親自護送回宮。審問之事由……」
沈墉尚未稟完,已被崔循毫不留打斷。
「公主在何?」他落在書頁上的手微微收,脆弱的紙張隨之皺起。
沈墉將頭埋得愈低:「公主無恙。只是許久不曾在學宮留宿過,甚是想念,也想陪班大家說說話,今日便不回府。」
崔循稍稍鬆了口氣,卻不肯信,沉默片刻後忽而道:「傷了?」
沈墉:「……」
雖三言兩語就了餡,但他覺著,此事實在不能怪自己。
畢竟他常與軍中那些直來直往的人打道,又怎麼能指他瞞得過眼前這位呢?
但蕭窈發了話,也不能就此承認。
好在崔循並未再問。
他這樣一個辦事妥帖的人,甚至沒來得及將那片銀杏葉書籤放回原,已站起,出了門。
第111章
Advertisement
澄心堂後, 蕭窈曾住過的屋舍又收拾出來。
翠微雖未曾隨行,但青禾做事已經比先前穩妥不知多,吩咐人去行宮取了從前的衾枕寢。備了炭爐, 熏了香, 收拾得極為妥帖。
人吩咐學宮的廚子, 煲了蕭窈喜歡的湯。
又特地備了餞,好喝完苦藥之後, 能含著緩一緩。
而蕭窈在對著微微搖曳的燭火反思。
原不該挨這一刀的。
只是當時才與桓維聊完, 得了想要的承諾, 占了上風, 心中便不可避免地有些自得。又因迎面而來的僕役看起來實在年輕, 量與差不多, 倒像是堯祭酒側的書, 便沒當回事。
好在因自小習弓箭, 的眼力要比常人好些,反應也還算快。
日映出刃上鋒利的時, 及時抬手,擋住了原本劃向頸側的匕首。
冬日厚重的大氅與多起了些遮攔的效用。
周遭的侍衛立時上前制住那人。
命無虞,小臂雖傷,但好歹沒傷及要害,醫師理過也已經止了。
止敷藥時, 班漪在側陪著, 臉煞白,氣都快不順了。
蕭窈自然是疼的。
只是此事實在是自己疏忽, 沒臉嚷, 也不願師姐揪心,便強撐著一滴淚都沒掉, 甚至還出點笑意安班漪和青禾。
Advertisement
「你今夜不若留在學宮,好好歇息。」班漪不放心就這麼回去,擔憂傷口崩裂,叮囑道,「醫師時時候著,若有何不妥,也好及時理。」
這提議正合了蕭窈的心思,立時應下,青禾安置去。
倒不是擔心傷勢。心中有數,知道這傷並沒那麼嚴重,而是不大想回去見崔循。
兩人同床共枕,這傷決計是瞞不過去的。
只一想
他的反應,蕭窈便覺頭上也作痛,便想著能晚一日是一日,說不準明日這傷便看起來沒那麼嚴重了。
接過青禾手中的瓷碗,忍著苦,一鼓作氣喝完那漆黑的藥。
正要拿餞,卻聽門外傳來侍衛的質疑:「誰敢擅闖……」
這侍衛是宿衛軍的人,認得蕭窈,卻不認得這位行跡匆匆的客人。
話音未落,便被六安攔下:「這是崔師。」
哦豁,小夥伴們如果覺得不錯,記得收藏網址 或推薦給朋友哦~拜託啦 (>.
: | |
猜你喜歡
-
連載101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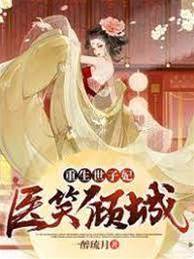
重生世子妃醫笑傾城
真假千金】她楚妙,本是丞相府嫡長女,卻與村婦之女錯換了人生;被家族尋回,成為父母與皇室的一顆棋子。她被哄騙嫁給平南王的嫡子蕭容瑾;公公是從無敗績的戰神,婆婆是燕國首富之女,丈夫體貼溫柔也是頂天立地的好男兒,蕭家兒郎個個尊稱她為一聲“嫂子”。可她滿眼是那站在陽光下的白月光,負了蕭家滿門。蕭家倒,她被家族棄如螻蟻,捧那村婦之女為帝後,告訴她“你天生命賤,怎配得上孤”。重生回來,蕭家七子皆在,她依然是他的世子妃,蕭家眾人捧在掌心的嬌嬌媳;但這一次,她要顛覆這江山!
97.1萬字8 71407 -
完結626 章
寵妃是個女魔頭
前世,她是眾人口中的女惡魔,所到之處,寸草不生。 因遭算計,她被當做試驗品囚禁於牢籠,慘遭折辱今生,她強勢襲來,誓要血刃賤男渣女!
115.2萬字8 7780 -
完結25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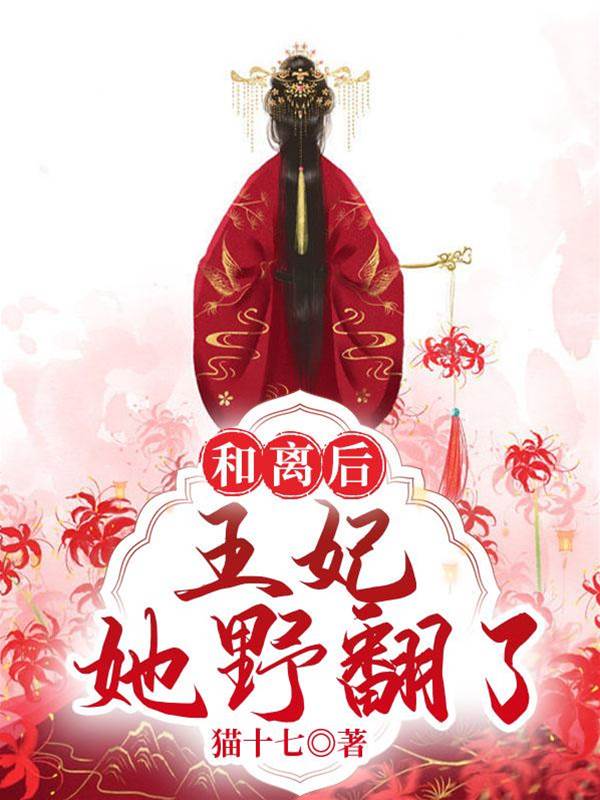
和離後,王妃她野翻了
【甜寵 穿越 追妻 虐渣 醫妃】三好醫生意外穿越,成為棒打鴛鴦的惡毒反派,當場被未婚夫退婚羞辱。她內心鎮定反手虐白蓮,退婚書摔到渣男臉上。為了名譽,跟腹黑太子達成協議。你幫我擦屁股,我幫你擋桃花。攜手攻破敵方陰謀時你來我往,互生情愫?她吃幹抹淨準備開溜,誰知太子立刻反悔。“殿下,您不能如此出爾反爾啊?”“怎麼,把本宮睡了,你就不認賬了?”
43.3萬字8.18 44627 -
完結43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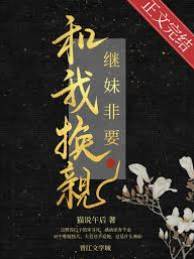
繼妹非要和我換親
宋尋月繼母厭她,妹妹欺她,還被繼母故意嫁給個窮秀才。怎料沒多久,窮秀才居然翻身高中,后來更是權傾朝野。她一躍成為京中最受追捧的官夫人,一時風光無量。但只有她自己知道,這玩意背地里是個多麼陰狠毒辣的東西,害她心力交瘁,終至抑郁成疾,早早亡故。重生后,就在宋尋月絞盡腦汁想要退婚時,她同樣重生回來的繼妹,卻死活要和她換親。為了擺脫前夫,宋尋月咬牙上了郡王府的花轎。都說琰郡王謝堯臣,母妃不受寵,自己不上進,除了身份一無是處。可等真的嫁去郡王府,宋尋月才發現,謝堯臣居然這麼有錢!而且他還貪玩不回家!過慣苦日子的宋尋月,一邊品著八種食材熬制的鮑魚湯,一邊感動的直哭:家有萬金,府中唯她獨大,夫君還不愛她,這是什麼神仙日子?謝堯臣上輩子只想做個富貴閑人。怎知那蠢王妃借他之名奪嫡,害他被父皇厭棄,死于暗殺。重生后,謝堯臣備下一杯鴆酒,準備送蠢貨歸西。怎知蓋頭掀開,王妃竟是前世病逝的顧夫人。謝堯臣冷嗤,看來不必他動手。可時間一長,謝堯臣發現,他這個新王妃不僅身體康健,還使勁花他錢。每天吃喝玩樂,日子能過出花來。謝堯臣坐不住了,憑什麼娶回個王妃使勁花他錢他還守活寡,他是不是傻?于是在那個良夜,他終是進了宋尋月的房間。老皇帝當了一輩子明君,可上了年紀,兒子們卻斗得一個不剩。悲痛郁結之際,他那廢物兒子和王妃游歷回來了,還帶著個小孫子。一家三口紅光滿面,圍著他又是送禮物又是講游歷趣事。又感受到天倫之樂的老皇帝,輕嘆一聲,就把皇位送出去了。謝堯臣:?宋尋月:?在顧府悔恨難當的宋瑤月:???
70.6萬字8.18 5591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