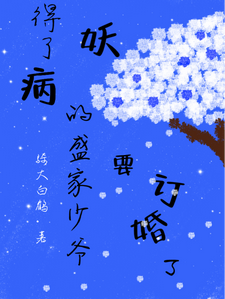《燃燼》 第155章 別離開我
“弄得這麼狼狽,我幫你好好洗一洗。”
“洗干凈了,就沒有酒味,沒有別人留下的氣味了。”
領口的鈕扣被解開,到涼意,姜海猛然清醒過來,啪地揮開那只手,掩著服往后退。
用了十十的力氣,男人白皙的手背迅速泛起一抹紅。
鄒言保持著作,頓在那里沒,他的眼里浮起幾分茫然。
“別我,你別我……”
明明泡在溫熱的水里,姜海卻到渾發冷。
為什麼會變這樣?
起初沒想過擁有,所以能平靜看待他與未婚妻的親。
而現在,只要一想到白芊輕小腹的模樣,想到他的手、他的曾過其他人,就止不住地犯惡心。
哪有什麼,全是的自我安,自我蒙蔽。
“后悔了?”
“想去找他?”
“已經開始討厭我了,之前,不是寧可下藥,也要得到我的嗎?”
男人的語氣很輕,甚至稱得上溫,可作卻格外暴。
修長有力的手指,完全無視的抗拒,扯住領口索直接撕開。
嘶啦——
大片大片地暴在白熾燈下,晶瑩的水珠滾落。
以前是趣,眼下,姜海頭一次因為無助而真正地到了恥辱。
的破布料甩落在地板上,從浴室到臥室,到蜿蜒著水痕。
“不要,我不要——”
哭喊著,踢著,可惜如蜉蝣撼樹般,始終無法阻止覆在上方的人。
鄒言垂著眼,一滴汗水從額角落,落在纖細的鎖骨上,反出他眸底的猩紅。
他俯下,狠狠吻住不斷開合的紅。
將那一聲聲抗拒,徹底封住。
“早上好,二爺。”
“早上好,邱醫生,今天我們要進行什麼治療?”
坐在沙發上的小年,穿著一黑的中式對襟,四肢修長,脊背拔,語氣禮貌又客氣,俊秀的臉蛋上卻沒什麼表。
Advertisement
老醫生笑了笑,道:“已經不需要再做任何干預了,您真的……比我任何一名患者,都要努力,我已經沒什麼能夠幫到您的了,明天我就會離開鄒家。”
“明天就見不到你了嗎,我會難過的。”話雖然這樣說,但年的臉上依然沒有任何波。
難過兩個字,仿佛只是說說而已。
邱醫生卻一副很是欣的樣子,笑得眼尾的皺褶都多了好幾道。
“我也會想念您的二爺,對了,送您一個小禮。”
一旁的助手蹲下,將手里一直拎著的竹筐放在地上,打開蓋子。
好幾分鐘過去,沒有半點的靜。
年抬頭看了眼墻上的掛鐘,微微皺起眉。
剛準備開口,一顆茸茸的小腦袋探了出來,圓溜溜的大眼睛先是警惕地四下張,接著小鼻子,怯怯地了聲:“汪。”
微皺的眉頭頓時擰個川字。
可沒等他拒絕,老醫生搶先道:“你就當是復健治療吧,配方是,先給它取個名字,然后每天撥出至一個小時,親自喂食,陪它玩耍,最重要的是,要對它表達喜。”
“表達喜?”
“要對它說,我喜歡你。”
“我……喜歡你。”
“對啦。”邱醫生站起,“記住,每天都要說哦,小最是赤誠,你付出幾分的心意,它便能回報你幾分,甚至更多。”
“喜歡,一定要表達出來,的共鳴能得到對方的忠誠,這些,沒辦法通過治療來傳達,只能靠你自己去領悟了。”
老醫生走到大門口,又轉過,笑著說道:“二爺,放輕松些,其實你已經比有些普通人做得還要好了。”
“嗚……”
年垂下眼,不知道什麼時候,小狗爬到了自己附近,正扭著胖胖的小子,哼哼唧唧的,不敢過來,也不愿意離開。
Advertisement
他面無表地出手。
手指修長又漂亮,還帶著淡淡的檀香味。
小狗仰起頭,在空氣里嗅了一圈,最后好像還是最喜歡他的味道,顛顛兒地小跑著湊近。
的小舌頭了出來,上的他的指尖,一旁的保鏢嚇了一跳,趕來制止。
卻在即將到的剎那,胖乎乎地子被撈了起來。
小年單手將小狗托在掌心,對上那張膽怯的圓眼睛,一字一頓道:“我,喜、歡你。”
“汪!”
烏黑的圓眼睛一亮,小舌頭又了出來,呼哧呼哧地扇著,像是在笑。
他扯了扯角,也第一次勾起了明顯的弧度。
接下來的日子里,他按照醫生的叮囑,無論多忙,都會撥出時間來陪小狗。
給它喂自己挑選的零食,給它洗澡,打網球的時候也會允許它在旁邊玩耍,幫忙把球叼回來。
不過他始終沒給小狗取名字。
他設下一個期限,如果三個月之后,對方還能始終如一的陪伴在自己邊,到時候,會正式做個狗牌。
就在兩個多月的某天,他遇到了邱醫生的助理。
“老師他……回老家的路上,被車撞了,當場亡……”
助理站在街頭,嚎啕大哭。
他愣了好一會兒,只出干的兩個字:“節哀。”
回到家中,他進了書房,把出事當天的通監控調出來反復看。
晚上吃飯的時候,他頭一回在飯桌上開了口。
“邱醫生的車禍,是你做的。”
啪!
溫云虹重重摁下金楠木的筷子,冷冷地投來一眼:“你這是什麼語氣,在質問我嗎?”
他抿角:“為什麼?”
“為什麼?你居然還問我為什麼!如果我不這麼做,那麼早晚有一天,外面所有人都會知道,鄒家下一任繼承人,是個瘋子,是個怪!”
Advertisement
“你知道每次我帶你出去的時候,我的心有多累嗎?呵,你當然不知道,就算我現在死在你面前,你也只會說一句節哀!”
人歇斯底里地尖一通后,慢慢地平息下來。
起,來到小年后站定,彎下腰,近他的耳邊,以安地語氣,輕聲道:“小言,你不用想太多,你不愿意去思考的,媽媽都會幫你,你只需要……做好你自己的事。”
“汪汪!”
他循著聲音走過去,一群與自己年紀差不多的年正圍著小狗在玩耍。
見到他,幾個人眉弄眼。
鄒遠良站出來,道:“二弟,這是你的狗?我們打個賭怎麼樣?”
“沒興趣。”
“別啊,聽說你養了它兩個多月,我們都很驚訝呢,這可是你難得一次表現出喜歡的緒,只是不知道,你養的狗,是喜歡你,還是更喜歡我們,怎麼樣,賭一把吧?你贏了,以后這狗的糧,我都包了!”
他站在走廊下,眼神淡淡:“不用,我贏了,今年一整年,你們都不要出現在我面前。”
“你!”
鄒遠良臉一變,剛想發火,被后幾人立即拉住。
“別沖。”
“你跟他較真做什麼……”
鄒大磨了磨后槽牙,道:“行,那如果你輸了呢?”
“我不可能輸。”
比賽的規則很簡單,不用食引,只能站在原地呼喚,看小狗會選擇去哪邊。
兩分鐘后,勝負揭曉。
著連看都不看自己一眼,黏在鄒遠良邊,搖頭擺尾、一臉討好小狗,他的眸底,出現了一裂痕。
“哈哈哈哈……”
年們轟然大笑,小狗跳上跳下地,尾搖得跟螺旋槳一樣,顯然比平時和他在一起時,要興歡快得多。
“璟言輸了,懲罰他什麼好呢?”
Advertisement
鄒遠良十分大度地擺擺手:“算啦,連他養了這麼久的狗都不親近他,還不夠可憐嗎,況且再怎麼說,我也是他哥,就不為難他啦!”
對于這次輸的滋味,其實他并沒有太大的覺。
在他眼底,就是場鬧劇,跟小孩子扮家家酒一樣。
不過這前前后后,加起來浪費了他十分鐘的時間。
必須回書房去了。
他出手,對那只小狗道:“過來。”
小狗轉沖著他汪了聲,繼續撲騰去了。
他沒有強求,離開了花園。
第二天一早,他照例在打網球。
球忽然驚一聲,跌坐在了地上:“狗……狗……”
他走過去,小狗的尸橫臥在草叢里。
皮開綻,模糊,已經分不清部位。
他出手,捻了一點在指尖。
早就涼了。
“邱醫生,你說錯了。”
他著口的起伏,喃喃道:“真正地喜歡,本不需要用所謂的心意去換,而是應該……從一開始,就把它關在籠子里。”
“如果我早一點這麼做……你們都不會離開。”
黑暗中,鄒言猛地睜開眼。
他做夢了。
夢到很久很久之前的事。
“嗚……”
邊傳來哽咽聲,他掀開被子,人正蜷著抱自己,像是也做了什麼噩夢,時不時搭一下。
他俯下,輕吻對方汗的鬢發,幾不可聞地低嘆一聲。
“別離開我。”
下午五點多,茍子鑫拎著保溫桶踏進病房。
護工正背對著他收拾什麼,床頭柜上有一只空碗,碗底殘留著湯。
他一個箭步沖過去,厲聲問道:“這什麼!”
護工大吃一驚,手一抖,差點把碗給摔了。
“茍、茍先生,這是醫院送來的例湯。”
“醫院送的?”他皺起眉,“從什麼時候開始的?”
“就……前幾天吧,一般是中午一碗清淡不油膩的湯,晚上一碗雜糧粥,粥熬得非常爛,米湯似的,很好消化,茍老先生喝得可香了。”
茍子鑫的臉并沒有因為這番話而好轉,他丟下句“你先別走,看著我爸”,然后匆匆跑了出去。
他徑直來到護士站,叩了叩臺面:“請問305室的什麼例湯,是你們送的嗎?”
小護士抬起頭,滿臉茫然,正要否認,茍那張風流倜儻的臉映眼簾,當即恍然道:“哦,是你啊!”
“誰讓你們送的,快說!”
男人一副如臨大敵的表,令小護士十分不解。
“我們護士長特意為你家病人申請的福利,兇什麼兇嘛,又沒要你的錢……”
茍子鑫怔住:“……福利?”
小護士懶懶地坐了回去:“你要有什麼問題,直接去問我們護士長吧,就在樓上408,給病人換藥。”
“不需要全解開,兩粒扣子就行了。”
冉一邊代,一邊剪紗布、準備藥品。
一抬頭,發現躺在床上的人已經把自己的上半了個。
男人抖著晃的肚子,笑嘻嘻道:“,哥的腹咋樣?”
一聲不吭,像是沒看見一樣,自顧自理傷口。
“恢復得有些慢,應該是沒忌口,不能喝酒,不能吃辛辣,否則……”
“哎呀,又沒關系咯,慢就慢點,只要你能每天來給我哥換藥,就算住上一年半載,我也樂意!”
“占用醫療資源,是不道德的行為。”
垂著眼,用鑷子卷起紗布浸泡到碘伏里。
男人還不知道自己即將承什麼,仍在咧著笑:“哥還有更不道德的呢,要不要試試——嗷!”
冉嚇了一跳,疑地瞪著自己手中的鑷子。
好像,還沒手哪?
“咸豬手都到醫院來了,連護士也敢調戲!”
悉地嗓音,輕佻,玩世不恭,卻又充滿了正義。
一如當年。
“喂,小護士,嚇傻了?要不要我幫忙報警,告他個猥,送他去局子里蹲上幾天?”茍子鑫問道。
“別別!大哥,放過我吧,我錯了,我以后再也不敢了!”
冉回過神,迅速用冷然包裹住自己,淡聲道:“不用了。”
說完,推著小車走了出去。
“哎,等等!”他追上前,“你別怕啊,對付這種人,就得一步到位,絕不姑息,不然他回頭還會招惹你……”
“是啊,沒有你,我早解決了,多管閑事。”
茍子鑫難以置信自己聽到了什麼:“哎,你這人,怎麼這樣!”
“怎樣?”
“好心當作驢肝肺!”
“哼,我只是實話實說,走開,別擋路。”
著對方快步離開的背影,茍只覺得被打擊到了。
猜你喜歡
-
完結293 章

以歲月換你情長
她是寄人籬下的孤女,他是成熟內斂的商業奇才。 一場以利益為前提的婚姻,把兩人捆綁在一起。她不過是他裝門麵的工具,他卻成了她此生無法消除的烙印。 真相敗露,他用冷漠把她擋在千裏之外;極端報複,讓她遍體鱗傷。 她傷心欲絕想要逃離,卻意外懷孕;反複糾纏,他們一次又一次陷入了互相傷害的死循環裏無法自拔。 四年後歸來,她不再是從前軟弱、備受欺淩的宋太太……
72.1萬字8 844570 -
完結528 章

離婚後我撿走霸總的崽
沒有生育能力的喬依被迫離婚,結束了四年的感情。心灰意冷之下去小縣城療養情傷,卻無意中拾得一個男嬰。出於私心,喬依留下孩子撫養。四年後,一排鋥亮的高級轎車停到喬依的樓下。顧策掏出一張卡:這是兩百萬,就當這四年來你撫養我兒子的酬勞。喬依把孩子護在身後:孩子是我的,我不可能和他分開!顧策邪魅一笑:那好,大的一起帶走!
80.3萬字8.09 95956 -
完結112 章

乖不如野
都說女追男隔層紗,秦詩覺得沈閱是金剛紗。明明那麼近,她怎麼也摸不到。 沈閱是秦詩的光,秦詩是沈閱的劫。 秦詩見到沈閱,就像貓見到了老鼠,說什麼也要抓到,吃掉。 原以爲是一見鍾情,後來沈閱才知道,他竟然只是一個影子。 他從未想過,他會成爲別人的替身。 那天,秦詩坐在橋上,面向滾滾長江水晃着兩條腿,回頭笑着對沈閱說:“我要是死了,你就自由了。我要是沒死,你跟我好,好不好?”
19.8萬字8 1325 -
完結11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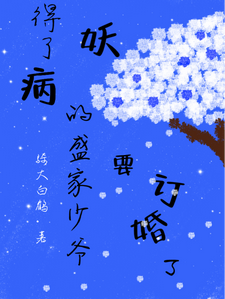
得了妖病的盛家少爺要訂婚了
因為自家公司破產,弟弟生病,阮時音作為所謂未婚妻被送進了盛家。盛家作為老牌家族,底蘊深,財力雄。 而盛祁作為盛家的繼承人,卻極少出現過在大眾眼中,只在私交圈子里偶爾出現。 據傳,是有不治之癥。 有人說他是精神有異,也有人說他是純粹的暴力份子。 而阮時音知道,這些都不對。 未婚妻只是幌子,她真正的作用,是成為盛祁的藥。 剛進盛家第一天,阮時音就被要求抽血。 身邊的傭人也提醒她不要進入“禁地”。 而后,身現詭異綠光的少年頹靡地躺在床上,問她:“怕嗎?” 她回答:“不怕。” 少年卻只是自嘲地笑笑:“遲早會怕的。” “禁地”到底有什麼,阮時音不敢探究,她只想安穩地過自己的生活。 可天不遂人愿,不久之后,月圓之夜到來了。 - 【提前排雷】: 女主不是現在流行的叱咤風云大女主,她從小的生活環境導致了她性格不會太強勢,但也絕對不是被人隨意拿捏的軟蛋,后面該反擊的會反擊,該勇敢的照樣勇敢。我會基于人物設定的邏輯性去寫,不能接受這些的寶子可以另覓佳作,比心。
2.1萬字8 65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