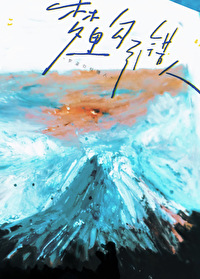《孟小姐嬌軟入懷,京圈大佬寵瘋了》 第265章:最優解
姜徊定定看著,“你舍得把我一個人留在這?”
孟津稚沒說話,只是微微偏轉開頭,視線沉默地向窗外。
能察覺得出來,姜徊口頭說是想綁,但不過是一點小趣,所以沒怎麼抗拒。
——可是他傷不一樣。
眼睫,半晌開口:“舍得。”
姜徊神倏然冷了下來,“你是個心狠的人。”
孟津稚不反駁,只是提起眼睛看向姜徊,語氣平靜:“你是個瘋子。”
針尖對麥芒,誰都不讓。
旁邊的傭人想要上來勸架,只是看著姜徊和孟津稚這個樣子,了,又被姜徊下一個目功噤聲。
氣氛安靜片刻。
姜徊上前,“我可以不你。”
孟津稚聽出來他語氣里的附加條件,一時沒有吱聲。
姜徊聲音不徐不疾:“但我必須要抱著你睡,不然睡不好。”
“……”這男人說著示弱的話,但還是如此的盛氣凌人。
也不知道是誰就教他的。
遠在天邊的應話默默打個噴嚏。
孟津稚:“只能抱著睡,不能做其他的。”
姜徊眼睛帶笑,“可以。”
孟津稚嗯了一聲,讓傭人把廚房里的湯端出來,讓姜徊坐在沙發上吃完,就指揮著他到樓上休息,自己則是留在樓下理公務。
不知道是不是的錯覺,在得知回到京市之后,所有人的態度都變得格外好說話了。
事不說事半功倍,卻也比之前的效率要好上太多。
孟津稚理完,也就半個小時。
傭人給端了一碟水果。
孟津稚吃了兩口,就起去樓上看一眼姜徊。
男人躺在床上,眼睛闔著,頭發溫馴地搭在邊緣,比起以往要乖順不知多倍,孟津稚就坐在邊,手替他試了試額頭溫度。
好在一切正常。
只是這個想法并沒有持續太久——
Advertisement
因為到夜里的時候,姜徊發燒了。
孟津稚也是被男人的溫度熱醒的,臉埋在沉峻膛里,燙得嚇人,而他的手臂又將裹著,差一點就讓呼吸不上來。
孟津稚費很大勁才從姜徊的懷抱里掙扎出來。
抬眼看過去。
姜徊眉頭皺,額頭上都是熱汗,看著非常不舒服。
孟津稚躡手躡腳地起床,到樓下翻出醫藥箱,家里的常備藥都有,還有冰涼,應該是姜徊擔心冒刻意準備的。
孟津稚全部帶上樓,把冰涼上姜徊的額頭,再給他喂了一次藥。
姜徊顯然是燒糊涂了。
起來吃藥,也是理智游離的況。
過了好一會,他才意識到孟津稚在自己側,聲音喑啞:“你去次臥休息,我明天自己理。”
孟津稚沒說什麼,喂他吃了藥,就去次臥了。
姜徊凝視著的背影,抿作一條直線,隨后他又虛虛閉上眼睛。
姜徊沒有看見的是,孟津稚在十多分鐘又回來了,抱著一大床棉被給他蓋上,再守在邊,時不時用溫度計測試溫。
天剛亮的時候,姜徊的溫度漸漸退下。
孟津稚也到隔壁休息了一會。
一夜沒睡,這一睡,就是昏天地暗。
還是傭人過來起床吃中餐。
孟津稚是一個人吃的,姜徊繼續在樓上,晚些時候,應話送文件過來讓孟津稚理,姜徊就在這時讓應話上樓去。
他們的對話完全隔絕了孟津稚。
孟津稚也不問,理完文件,就開始研究姜氏近十幾年的項目,有些事不是一朝一夕能做的,能力也不是憑空出現的,在這之前,只能自己先打好基礎。
看完文件,捋了一下思路。
傭人給端來湯,孟津稚如夢初醒,抬手了自己僵的脖頸,端著湯上樓。
Advertisement
門沒有關嚴實。
聲音從里面出來。
“寧家撐不了多久了,可能會在最近找上夫人。”
“應助理,你跟了我這麼久,應該知道這麼做。”
應話斟酌道:“我明白,只是姜總——”
他頓了頓,說:“寧泰要是找不到夫人,很有可能會直接找上姜氏,姜氏最近的不,他們要是真找上門,還找了施,對我們可能不利。”
姜徊先前塑造的妻人設還在那。
只要寧泰拋得下面子,對姜氏公然施,那麼姜徊的人設就會崩塌。
誰會相信一個妻的人會對自己的岳家不管不顧呢?
即使后續有澄清,但他不幫寧家是事實,所有人都會在真心上打一個問號,應話現在說這話其實還有一個目的,就是暗示姜徊可以適當的公布孟津稚的世,這樣姜徊不幫寧泰就可以水到渠了。
但是這樣就等同于……
要把孟津稚當初的過往和傷口撕開,告訴眾人,曾經是如何的生活,讓再會一遍痛苦。
姜徊沒有說話。
應話低聲音:“這件事,老爺子也是同意的。”
姜徊眼睛一利,“應話。”
應話知道很大膽,但事實上這麼做對姜氏是最好的,而且——
他當著姜徊的面,又道:“姜家會記得孟小姐的恩,孟小姐也不用改頭換面的和你結婚了,其實于于理,是一舉兩得的好事。”
后半句說的是孟津稚最開始被改名字的事。
“我同意。”聲橫進來。
姜徊倏然抬頭看去。
孟津稚平靜走了進來,和姜徊對上視線,半晌說:“這是最優解。”
姜徊沒有接話,只是問:“你是怎麼進來的?”
“門沒關。”
姜徊目落到應話的臉上。
應話心虛低下頭,他沒說話,只是側攥著的手收攏。
Advertisement
孟津稚開口:“你沒有必要怪他。”
上前兩步,坐到姜徊邊,替應話擋住了絕大部分的姜徊目。
“你不要怪他,你應該是清楚我一開始是這麼想的——”說,“如果不是當初沒有辦法,我也不會回到寧家,而且寧家對我來說,沒有半點恩,我也不會對他們手。”
早在姜徊送寧愿進去的時候,孟津稚就知道自己和安若之已經不共戴天了。
寧泰雖然偏袒,但也是利益驅使。
毫不懷疑,要是真的半點價值都沒有,寧泰早就把甩開了。
姜徊眼眸沉沉,語氣比剛才還要冷:“你知道要是這個輿論被推到高會發生什麼嗎?”
猜你喜歡
-
連載2176 章

九爺,你家小祖宗不想負責
1V1HE雙潔強寵安南笙哭著喊著要嫁的男人讓她在結婚當天就獨守空房,狗男人卻抱著他的心上人哄了一天一夜。雖然是自己求來的結果,但安南笙不打算把日子跪著過下去。該離就離。她自己本身就是豪門,一心一意的良人不好找,美男還不是一抓一大把?恢複單身的安南笙立誌要喝遍美酒睡遍美男,結果美男隻是摸到小手,轉頭她自己就被人吃幹抹淨。安南笙被大佬逼得無處可逃:“五星好評給你,不負責行不行?”
200.6萬字8.33 160629 -
完結40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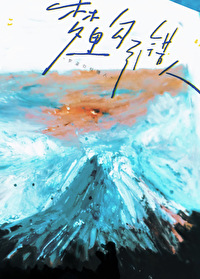
夢裏撩錯了前任的眼盲弟弟[救贖]
你是我假意裏的唯一真心。”雙向救贖!!!1鄭相宜擁有“控夢”的能力,得知前網戀對象家世顯赫後,她決定在夢中接近他。出乎意料的是,前任的夢裏是一片虛無。鄭相宜在夢裏引誘“前任”,少年在她指尖挑動下呼吸也變得急促。她喊前任的名字,沒有看到少年悄悄攥緊的拳頭。後來,鄭相宜得知自己一直以來進入的都是盲眼少年陶時安的夢。她入錯夢了。盲眼少年是前任的弟弟,家世優越,長相俊美,溫柔體貼,已經喜歡上了她。鄭相宜沒覺得愧疚,反倒很開心——“這下更好騙了。”陶時安是個瞎子,看不到她臉上的胎記,也看不到她藏在微笑背後的心。2鄭相宜一直在騙陶時安的愛和錢。陶時安溫柔又克制,得知真相後心甘情願為愛折腰。他真的是個很善良的好人,仍捧著真心告訴她:我都知道,我不怪你。等你媽媽同意我們就結婚。鄭相宜拒絕了,并提出了分手。在大雪紛飛的冬季,陶時安固執地拉住她不肯放手,紅著眼反複問著為什麽。“你是個……內容標簽:豪門世家 天之驕子 都市異聞 治愈 美強慘 救贖其它:眼盲
11.5萬字8 164 -
完結203 章

索吻!狂撩!讀心!假千金被寵壞
【讀心+多大佬+病嬌霸占=修羅雄競場】溫酒扶老太太過馬路出車禍,居然傳到一本同名同姓的女反派身上。 且這個女反派只愛勾引男人們,這些男人還都是原書女主的慘死炮灰舔狗。 系統奧利給:【只要茍到大結局,得到所有慘死炮灰舔狗的喜愛值一百~就可以實現您一個愿望,并且還額外贈送上輩子所有技能,以及吃瓜系統。】 有錢有權有美貌的她能答應? 溫酒:必須答應! 面對某霸總。 【沒想到有些人表面高冷,實際上舔狗,主動半夜送女主和男主開房~還覺得女主是無辜的。】 面對某天才黑客。 【你為了保護女主主動委身一群綁匪……實際上是女主自導自演找的人哈哈哈,懵逼了吧~】 其他三個大佬舔狗聽著渾身瑟瑟發抖,以為逃過一劫。 【你們三個更慘!賽車手車王被燒傷、清冷佛子神醫被變態們折磨、國民影帝背女主黑鍋。】 溫酒的目光又亮晶晶看向另外一群大佬們。 王室公主,暗殺家族,傭兵集團,財閥世家等等…… 大佬們:你不要過來啊! …… 某天,溫酒發現這五個舔狗大佬和其他大佬看她的眼神變了,不僅不討厭了,還紛紛爭著和她單獨約會。 溫酒察覺到不對,剛打算跑卻被他們堵在床上。 “酒酒,我們之間你到底選誰!” “還是你都要?” 溫酒:糟了!她好像招惹到一群變態了。 救命啊啊啊!
40.2萬字8 16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