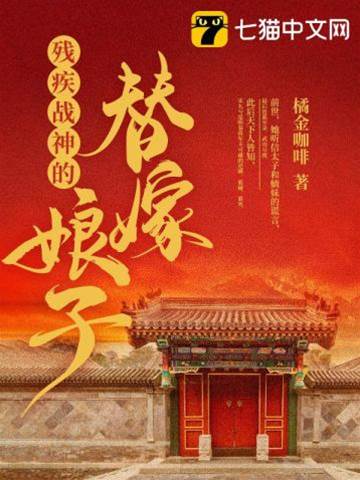《侯府在逃小妾》 周府
周府
雖說周環山在錦州也不過住了一月,家當卻十分可觀,其中多是當地富貴人家送來的“薄禮”,裝了整整九輛馬車,聲勢浩。
于人前,衛辭頗重規矩,略帶警告地看宋一眼,只好訕訕撤回手,由香葉攙著走下。
今日宋戴了面紗,單一雙杏眼在外頭,倒是語還休,分外靈。小步跟上衛辭,輕聲問:“京中不管員行賄麽?”
衛辭挑眉:“我瞧著你倒是管。”
癟了癟,識趣地止住話頭。
周環山親自將二人迎正廳,規矩極了,連餘都不曾瞟向宋,語含尊敬:“公子大駕臨,不知所為何事?”
“把你那個春紅綠紅的小妾來。”
“桃紅?”周環山宦海浮沉幾十年,不過兩息,便明白衛辭是為了他恩寵正濃的外室而來,忙不疊喚了丫鬟,“去芳華閣。”
衛辭無意候在這裏聽兒家閑談,留了香葉與蒼,自己則同周環山去書房。
半刻鐘後,桃紅頂著一層厚重脂過來,乍看眉目致,可眼尾的疲態卻難以掩飾。
宋屏退丫鬟,打量的目上下一掃,桃紅知心思敏銳,當即往後了。見狀,宋輕輕“哼”一聲:“做什麽?”
桃紅素來怕宋擺出這副樣子——
明明生得俏,慍怒之下眼瞼微闔,卻無端生長出蓬氣勢,仿佛是睥睨天下的清冷仙子。
“好好好,我認輸。”桃紅耷拉著肩坐下,神略微不自在,“咳,前兩日你差人來尋我,那會兒子沒好利索,便回絕了。”
宋狐疑地轉了轉眼珠,見桃紅的形一如往昔,唯有面白如牆,離得近了,還能看清簌簌下落的細膩塵。
“你病了?可瞧過大夫?”
桃紅偏過頭,故作輕松道:“無礙,畢竟府裏姬妾多得數不清,爭爭寵起點爭執,又不會死人。”
Advertisement
“我不信。”宋說著要去夠桃紅的手,卻被敏捷躲開。
“對了,大後日眷便要先行啓程。”
桃紅出一勉強的笑,扯開話題,“你作何打算,將來可會去京城。”
宋否認,順道將玉蕊的際遇提了一提,試探地問:“你當真想在後宅耗上一輩子?”
聽聞玉蕊非但了奴籍,甚至自己做主挑了一門親事,桃紅瞳孔微震,緩了緩神才道:“……竟也舍得……”
“方二下了獄,縱是舍不得榮華富貴也要舍,總比丟了命要強。”
宋趁熱打鐵,“我同玉蕊有意盤個店鋪,就自個兒做老板,雖說比不得跟著貴人們來得錦玉食,但勝在自由自在,你覺得呢?”
桃紅似是仍于驚詫之中,失魂落魄地點了點頭。
“桃紅姐姐。”宋正道,“現在可願告訴我你因何患病了吧。”
“我……我說不出口。”
好歹是不再抗拒,宋極有耐心,自顧自地斟了杯茶,由得桃紅慢慢思忖。
興許只過了一時片刻,興許是過了好半晌,桃紅囁囁喏喏地開口:“周大人,他不能人道。”
“噗——”
聽言,宋一口茶噴了出去,嗆得眼尾通紅。秀眉跟著輕挑,沒好氣地瞪了瞪,像是怨桃紅竟將此等辛說與自己。
鮮活的模樣終究是逗笑了桃紅,頓時有了從前依偎取暖的覺。
“好吧,事是這樣的……”
原來,周環山的正妻乃是武將之,締結良緣的頭幾年,和,接連生了兩個孩子。
漸漸的,好本作祟,周環山羨慕起同僚們左擁右抱、妻妾群。
周夫人懷第三胎時,他與表妹被捉在床,剽悍的武將之用彈弓中男子要害。周環山心俱傷,自那以後便不能人道。
Advertisement
亦是從那時起,周夫人對他再無所謂,甚至做主替他納了表妹。
久而久之,周府姬妾群。
京中人士無不道他風流、亦羨嫂夫人大度,誰能想到個中藏著如此可憐又可恨的緣由?
桃紅嘆息一聲:“周環山暗地裏可怕得很,□□迫我們爭寵,還,還得拴著狗鏈子。要不是衛府來人,我能歇上幾日等紅印消下去,真是……”
宋咬了下,一陣一陣一泛起惡心,眸子也因淚意變得清亮如星。
“給我憋回去。”桃紅故作兇惡地瞪,手中卻誠實地遞來幹淨方帕,“我了好幾層的,要是哭了不得難看死。”
悲傷沖淡了幾分,宋握住桃紅冰涼的手,輕聲說:“你想離開嗎?”
桃紅答不上來,只道要再想想。
也是,們學了十餘年的討好貴人,所做所求不過是尋得一棵大樹庇蔭。倘若眼前陡然出現岔路,反而不知道該如何走。
宋不強人所難,且清楚桃紅上有著原住民的韌,即便沒有自己,桃紅依然能過上好日子。
既如此,便由時間來給出答複。
/
回程,宋前所未有的安靜。
衛辭將書頁翻得嘩嘩作響,卻也不見轉頭看一眼,登時氣得牙。
他轉念想,兒家的事雖無趣,可宋畢竟是自己房中人,關懷兩句應當無礙。遂將書卷收起,狀似無意地問:“都聊了什麽?”
宋回過神來,極盡委屈地看向衛辭,眼淚說掉就掉,豆大一顆,冰雹一般砸上他心頭。
衛辭滿腔憤憤登時皆散了,將人按坐至上,一手穩住纖細腰肢,一手索到帕揩了揩的眼角,偏偏眉頭仍是皺著,好似如臨大敵。
年心,反倒令宋愈發難,忍不住埋他頸窩放聲痛哭起來。
Advertisement
“為何只有我這般幸運。”語調低緩,近似呢喃,“們又做錯什麽了呢……”
猶記得初衛府之時,宋如屢薄冰,是以無暇顧及旁人。如今清了衛辭脾,日子舒坦至極,反倒重又變得心,總想將姐妹都拉上一把。
宋歉疚地了他上的水漬,紅著眼道:“公子,可是我太貪心了?”
“嗯。”衛辭笑一聲,“我早前便說過,你就是個得寸進尺的家夥。”
小臉皺一團,有些不願承認:“也沒有罷。”
忽而,有龐然大逐漸蘇醒。
兩人俱是一僵。
衛辭難得尷尬地紅了耳朵,卻明目張膽地將人按住,淡聲道:“逃什麽,本公子又不會在這裏辦了你。”
宋面上泛起紅,錯開眼神,悶悶地說:“你真是、真是,不知該說什麽才好。”
綿的語調罵起人來倒像是撒,以至于猙獰隨著心跳竟兀自跳了跳。
他嗓音沙啞,無辜道:“它自己的。”
宋哪裏還有心傷春悲秋,擡手捂住他的:“待會兒你要如何下去?”
衛辭順勢吻了吻的掌心,骨眼神掠過霧蒙蒙的眼,自然而然地憶起平日夜裏,宋未著寸縷橫于錦被之上,亦是這般淚意盈盈。
呼吸霎時變得重不堪。
頗不自在地挪了挪,卻見衛辭猛地閉目,一臉歡愉與痛苦織的神。
“……”宋罵道,“不知。”
衛辭好似聽到了天大的笑話,一掌拍上的弧度勾人的:“坐穩了。”
語罷,雙“手”齊下,輕而緩地挲著,待略顯粘稠的津溢出許,順勢將指腹了進去。
宋與他廝磨了許多日,早已先一步有了反應。舌尖自發地舐起指節,兩瓣一一,仿佛在吸吮著甜膩的果。
Advertisement
他冷清的眉眼染上迷離,耳垂紅如珠,作卻割裂得冷靜,極盡溫地逗弄宋,一邊問:“到底是誰不知,嗯?”
聞言,宋無地開他的手指,了:“不是我。”
“呵。”
衛辭略躬起背,低頭吻住不知好歹的,一手得了閑,顧起被冷落的地方。
宋清晰到他賁張的理,偏偏脆弱的舌尖也被含住,獨屬于衛辭的氣息鋪天蓋地地湧來,從裏至外將沾染。
勝負令卯力擡手,上的結,如願聽衛辭悶哼一聲,停下攻城掠地。
滾燙的汗珠暈了鬢角,令衛辭了幾分疏離,多了幾分魅。
略怔了下,已經憶不起緣何到了這一步,卻順從心仰起小臉,去尋他令自己甘之如飴的。
馬車原就不得顛簸,此時卻了助益,t宋極快力地垂上他肩頭,劇烈息道:“好了好了,我不要了。”
衛辭見好便收,用方帕簡單清理。
反倒宋有些坐立不安,赧地問:“那、那你怎麽辦?”
他一本正經道:“路上時辰太短,不夠我用,還是回府裏了慢慢來。”
“……”
有寬大袖擺掩飾,行走間倒也瞧不出問題,唯獨宋從他墨黑的眸中窺見了驚濤駭浪。
兩一,試圖商量:“不若先用晚膳?”
“弄完再用。”
“等你弄完都不知何年何月了。”
衛辭置若罔聞,擡眼示意值侍衛離開,待院門關上,強勁有力的雙臂將宋一把抱起。
失重令不得不攀附住健壯軀。
他倏爾閃過一個念頭,決意即刻付諸行,便將宋至牆上,由居高臨下地掌控火勢。
張與不安,使得宋前所未有的敏,明明方才已得到滿足,卻又水般舐他的角,雙亦箍著勁瘦的腰,仿佛世間僅剩下彼此。
猜你喜歡
-
完結136 章

逆天五寶:主母她是個受寵體質
一朝穿越,她直接就當起了便宜媽,寵愛一個遊刃有余,一下子五個寶寶真的吃不消。 她刷著小算盤打算全都退還給孩他爹,卻突然間發現,這一個個的小東西全都是虐渣高手。 她只需勾勾手指,那些曾經欺負她害過她的就全都被她五個寶寶外加娃他爹給碾成了渣渣! 爽點還不止一個,明明一家七口五個都比她小,結果卻是她這個當娘親的成了全家人的心尖寵。
12.5萬字8 41511 -
完結52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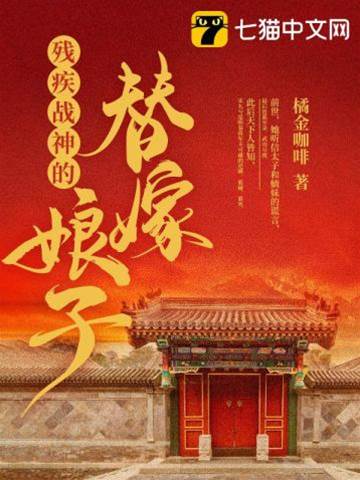
殘疾戰神的替嫁娘子
【重生+男強女強+瘋批+打臉】前世,她聽信太子和嫡妹的謊言,連累至親慘死,最后自己武功盡廢,被一杯毒酒送走。重生后她答應替嫁給命不久矣的戰神,對所謂的侯府沒有絲毫親情。嘲笑她、欺辱她的人,她照打不誤,絕不手軟。傳言戰神將軍殺孽太重,活不過一…
97.6萬字8.18 35390 -
完結645 章

盛唐無妖
穿過盛世大唐茶都還沒喝一口被迫上了花轎遇上了口味比較重的山村女鬼... 老師傅:姑娘,世上竟有你這般如此骨骼精奇、命格貴重、百邪不侵... 顧曳:說人話 老師傅:你命硬,可驅邪,上吧!
176.8萬字8.18 7847 -
完結608 章
盛寵世子妃
一覺醒來,現代大齡剩女變成了農女,內有渣爹狠毒嫡母,外有惡鄰惡霸環伺,怎麼破?種田發家,智商碾壓!貪心親戚是吧?我讓你搶,到嘴的都給我吐出來!白蓮花是吧?我讓你裝,將計就計虐你一臉!什麼?後臺?隨手拎個世子當苦力算不算?某夜,世子大人可憐巴巴地湊過來:"娘子,他們說,你沒付我工錢…""嗯?"…
94.8萬字8 8861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