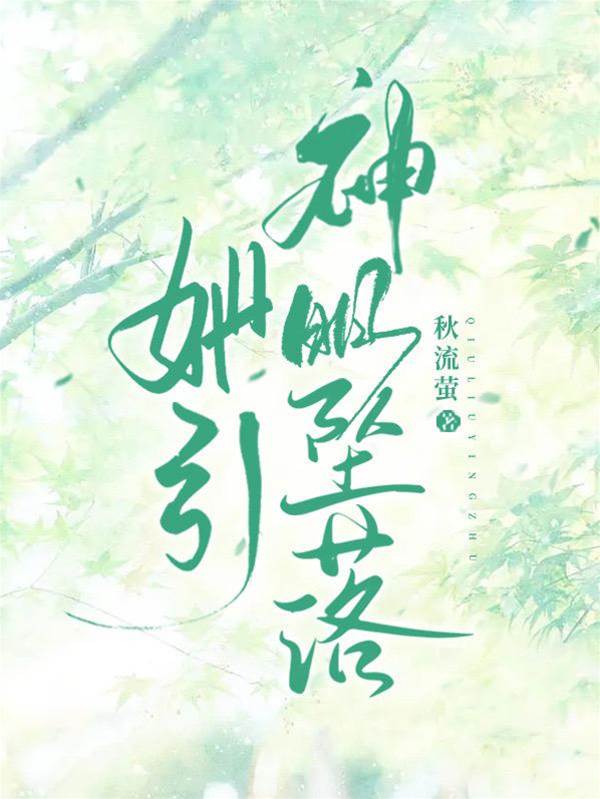《禮物》 第14章 第 14 章 派出所門口手拉手
第14章 第 14 章 派出所門口手拉手
梁曼秋是真的傻,戴柯這顆金剛腦袋不知道被籃球砸過多回,怎麽可能一次壞掉。
戴四海嘆氣,“小秋,你看哥哥現在不也活蹦跳,哪裏傻?”
梁曼秋可不敢看。
戴四海:“但是以後不要再打架,特別不能再用東西打頭,能做到嗎?”
梁曼秋立刻點頭。
“還有你,”戴柯目如箭,紮向他的親兒子,“肯定是你先打妹妹,打哪裏了?”
戴柯不答,梁曼秋更不敢吱聲。
阿蓮哄道:“不用害怕,告訴阿伯,大D打你哪裏?”
章樹奇說:“小秋,我們現在在派出所,大D不敢打你。你現在說出來,就是留下他打你的證據。以後他要是再打你,我們新賬舊賬一起算。”
戴柯了,似要頂,旋即給戴四海一個犀利的眼神頂回去。
只能倔強地吸了兩下鼻子。
“小秋?”戴四海作為一家之主,鼓勵道。
梁曼秋擡起半張臉打量一眼戴柯,仍是有些不敢直視,“哥哥薅我頭發,頭皮都快薅掉了……”
戴柯喊冤:“哪有那麽誇張!”
戴四海:“大D,我沒問你。”
阿蓮忽然心思一,“小秋,你剪短頭發就是因為這個?”
梁曼秋單是想起渾被掣肘的無力,胳膊便起皮疙瘩。
戴柯忍不住回:“誰先用鐵盆敲我頭?”
“好了,”戴四海出聲制止,“大D,你以後不能打妹妹,能做到嗎?”
戴柯沒吭聲。
章樹奇也催促,“大D,做個男人,妹妹是用來保護的,不是用來欺負的。”
戴柯冷冷哼了聲,“誰喜歡打細狗,一把骨頭。”
鬧劇終于快要迎來尾聲。
章樹奇作為中立方,總結般道:“這一次雙方都有錯,大D錯在不信任小秋,先手打小秋;小秋錯在不告而別離家出走,讓阿伯他們擔心。”
Advertisement
兩位當事人不吭聲就相當于默認,年人心高氣傲,一骨,寧向長輩認錯,絕不向同輩低頭。
“這樣吧,”章樹奇說,“這次主要因為大D不信任小秋,才引發這一系列麻煩,幸好沒有釀大錯。不然你們餘生都要為自己的過錯埋單,特別是你,大D。”
戴柯下微揚,本該跩裏跩氣,但剛哭過,紅著一雙眼,渾著一別扭的傲氣。
章樹奇:“為了避免類似事發生,小秋可以向大D提三條要求,只要不過分,大D需要無條件滿足。這次事就一筆勾銷,以後誰也不許再提,行嗎?”
戴四海第一個附和:“我同意你們小奇哥的主意。”
戴柯:“誰知道過不過分。”
章樹奇:“小秋,擡起頭來,想好了嗎?”
梁曼秋出著的雙手,擱上掰弄手指頭,“第一……”
仍是不由自主瞥戴柯一眼,要他批準才敢繼續似的,“哥哥以後要相信我。”
戴柯:“以後那麽長,誰知道你會不會撒謊?”
戴四海:“大D,你就先答應小秋。”
梁曼秋:“反正我不會你的東西。”
戴柯早覺到錯怪了,但認識和承認錯誤是兩個維度的事,困難等級不同。
“哦。”古怪應了一聲。
“哦是什麽意思,做男人爽快一點。”
章樹奇不知道第幾次給戴柯進行男人式洗腦教育,青春期的男生完男人的蛻變,對戴柯這種“幫派頭目”卓有效。
“知道了。”戴柯拖腔拉調,仍是有點不耐煩。
梁曼秋的腰板直了一點,“第二,哥哥不要再打我。”
戴柯睨一眼,“要是你先打我呢?”
章樹奇:“孩子的力氣能有多大?還不如籃球砸你疼。”
又轉頭跟梁曼秋吩咐,“小秋,打男人不能打臉,其他地方隨你打。”
Advertisement
他擡起戴柯的胳膊,拍拍,“你要打打胳膊,看這肱二頭,多結實,快賽過我了。”
同的好像帶毒,戴柯不了似的,不著痕跡回手,繼續兜著。
“不打就不打,骨頭死,硌疼我手。”
梁曼秋的語氣越發松弛,“第三,哥哥以後不要再我細狗。”
章樹奇點頭笑道:“這個我同意,小秋那麽可的一個孩,起了這麽難聽的外號。”
戴柯:“哪裏不像細狗?”
梁曼秋仗著有人撐腰,“你才像。”
戴柯前一步,要揍似的,嚇得梁曼秋不由後仰,雙臂立刻叉在腦袋前,護住自己。
“哎哎——”戴四海出聲阻攔,“剛答應過的不打小秋。”
戴柯悶悶道:“我手都沒拿出來。”
梁曼秋坐回原形,垂下手:“反正不能細狗。”
戴柯:“不細狗什麽?”
阿蓮久違地進話,“就小秋呀,多可的名字。”
戴柯甩過一個“關你屁事”的眼神,不太樂意外人手。
梁曼秋一直是細狗的存在,瘦不拉幾,不太會梳頭發,雙馬尾經常耷拉,跟細狗的耳朵似的。乍然要安上小秋的名字,好像變一個陌生人。
不出口。
“就小秋,”戴四海催促道,“跟你說過多次不能給別人起花名。”
梁曼秋像細狗一樣眨眼睛,似乎也期待在他心裏建立一個新的形象。
“梁曼秋。”戴柯吐出三個字,心裏補全四個字:死梁曼秋。
梁曼秋癟了癟,只能退而求其次。
章樹奇拍了一下手,“總比細狗好,那麽從現在開始,君子一言駟馬難追。今日事今日畢,握手言和,可以嗎?”
又替瞧瞧兩頭倔驢,“大D,做男人就要主一點。”
阿蓮也趕梁曼秋起走到戴柯跟前。
Advertisement
戴柯不不願從兜掏出手,既不看手,也不看梁曼秋,一副要不要的傲慢。
在想跟同齡生手拉手一起玩的年齡,梁曼秋被當“艾滋妹”孤立,錯過了那段親時,以致跟人握起手來特別鄭重其事,特別敏。輕輕握住比自己大了一圈的手,比自己涼一些的手,一只屬于男生的手。
戴柯漫不經心虛攏五指,馬馬虎虎算回握。
心裏只有一個覺:真小,好像再用力一點就能碎。
章樹奇:“好,從現在開始,出了派出所才能松手。”
戴柯立刻甩開梁曼秋,“憑什麽?”
章樹奇:“就憑我是警察,在派出所我說了算。”
章樹奇一手牽著一頭倔驢,把他們拉到詢問室門口,面對著青山派出所大院,重新將兩人的手扣在一起。
“拉好,”章樹奇說,“一秒多加一個鐘頭。”
戴四海一直在旁看著章樹奇替自己教育兩個小孩,表偶有古怪,不但沒出言制止,還火上添油。
“聽小奇哥的話,不然上手銬啊。”
章樹奇哭笑不得,“海哥,別嚇唬小孩。”
戴柯懷疑章樹奇真能幹得出來,只得若有似無拖著梁曼秋的手。
梁曼秋在小學聽多了桃八卦,誰和誰拍拖,誰和誰拉手甚至咀,總覺得牽著戴柯的手怪怪的。
有點尷尬。
另一只手不由攥,哪知就像沒法同時左手畫圓右手畫方,竟不小心握了戴柯的手。
戴柯瞥一眼,困中似帶著點排斥,稍稍松了勁頭。
梁曼秋腳趾抓地,悄悄松開指尖,險些出他的掌心。
又給他住了。
戴柯可能覺拉著不舒服,變換姿勢,撈著的手,像拖小孩走路。
章樹奇理完兩個小孩的矛盾,又帶戴四海見一下另外一個當事人家屬。
Advertisement
周舒彥的父母已經聽片警複述一遍案經過,就是一件可大可小的事,往大了看是不尊敬逝者,往小了看只是一個蘋果的事。
周家原本也有一個姐姐,19歲病逝,長眠在青山墓園裏。
戴四海做小生意接形形的人,還是第一次上有人跟死人搶食的事,難免尷尬,連連道歉。
周家父母著和談吐可見家境優越,素質較高,思想也較為開明。
周母聽說梁曼秋在外流浪兩天,想起已故的兒,不忍苛責,說這事就算了。
戴四海要拉梁曼秋過來道歉,周母也說免了,小姑娘在外兩天也了不苦,他們也沒損失什麽,正好讓他們知道兒子最近都去了哪裏。
周家父母便要把周舒彥領走,路過手拉手的一對兄妹,不忍多看兩眼。
如果他們家姐姐還在,應該也有這樣和諧的場面。
周舒彥的目落在梁曼秋和戴柯握的手上,好奇又疑,很能看到同齡人還這樣手牽手。
被長輩著拉手,戴柯已經認輸,但給一個差不多同齡的男生一直盯著,多有一點沒面子。
而且對方還算個帥哥。
戴柯輕輕甩開梁曼秋的手。
這下,沒面子的了梁曼秋。
“哥哥……”梁曼秋撓了撓兩天沒洗的頭發,信了章樹奇的警告,真怕要加時賽。
戴柯雙手抄兜往派出所門口走。
“大D,幹什麽去?”戴四海問。
“買水喝,死了。”戴柯頭也不回。
梁曼秋替看看戴柯和大人,猶豫一秒,追上去怯怯出聲:“哥哥,等等我。”
“髒死了,離我遠點。”戴柯急挪開一步。
梁曼秋有後數道視線保駕護航,撓撓頭,大著膽子靠近戴柯。
戴柯一避再避,“死細狗,把虱子傳染給我,你就死定了。”
“哪有……”梁曼秋後知後覺,“哥哥,你說話不算話,剛答應不我細狗。”
戴柯便沒跟多吱一聲。
……
梁曼秋被戴四海趕回碧林鴻庭好好洗了澡,才能回檔口。
戴柯也慘遭足,百無聊賴切著電視臺。
路過的街坊看到梁曼秋的影,好奇多,“喲,小姑娘找回來了啊?”
“是啊,”戴四海笑著接話,“多虧了章警。”
等街坊一走,戴四海立刻繃臉,“大D,小秋,你們過來。”
兩個小孩回來後沒說一句話,梁曼秋還多瞥幾眼戴柯,戴柯一點眼神也不給。
戴四海發令:“你們兩個,繼續在門口拉著手,拉到吃飯為止。”
戴柯劍眉倒豎,“憑什麽?!剛不是在派出所拉過了嗎?”
梁曼秋也為難地扯了扯角。
戴四海:“在派出所是小奇哥說了算,在家是我說了算,你們是不想吃飯還是想挨打?”
“哥哥……”梁曼秋兩樣都不想,小心翼翼重新拉起戴柯的手。
戴柯一副氣炸的猙獰表,卻不敢掙開梁曼秋的手。
猜你喜歡
-
完結1091 章

失憶后我成了法醫大佬
十三年前全家慘遭滅門,蘇槿患上怪病,懼光、恐男癥,皮膚慘白近乎透明,她成了「吸血鬼」,選擇在深夜工作,與屍體為伴;他背景神秘,是現實版神探夏洛克,刑偵界之星,外形豐神俊朗,愛慕者無數,卻不近女色。第一次見面,他碰了她,女人當場窒息暈厥,揚言要把他送上解剖臺。第二次碰面,她手拿解剖刀對著他,看他的眼神像看一具屍體。一個只對屍體感興趣,一個只對查案情有獨鍾,直到未來的某天——單宸勛:你喜歡屍體,我可以每天躺在解剖臺任你處置。蘇槿:我對「活的」沒興趣……
196.7萬字8.18 22956 -
完結1233 章
七零年有點甜
何甜甜一直以感恩的心,對待身邊的人。人到中年,卻發現一直生活充滿謊言的騙局里。重回七零年,何甜甜在小銀蛇的幫助下,開始新的人生。換一個角度,原來真相是這樣!這輩子,再也不做睜眼瞎了。這輩子,再也不要錯過辜負真心相待的青梅竹馬了,好好待他,信任他,有一個溫暖的家。******
215.3萬字8 54157 -
完結877 章

失憶后,偏執總裁寵我成癮
生日那天,深愛的丈夫和其他女人共進燭光晚餐,卻給她發來了一紙離婚協議。 原來,三年婚姻卻是一場復仇。 意外發生車禍,夏初薇失去了記憶,再也不是從前了深愛霍雲霆,死活不離婚軟包子了! 霍先生:“夏初薇,別以為裝失憶我就會心軟,這個婚離定了!” 夏初薇:“離婚?好,明天就去,誰不離誰是小狗。”第二天,夏初薇敲開霍雲霆的門。“霍先生,該去離婚了。” 霍先生:“汪!”所有人都知道她愛他至深,但唯有他,他愛她多次病入膏肓。
157.9萬字8 60448 -
完結10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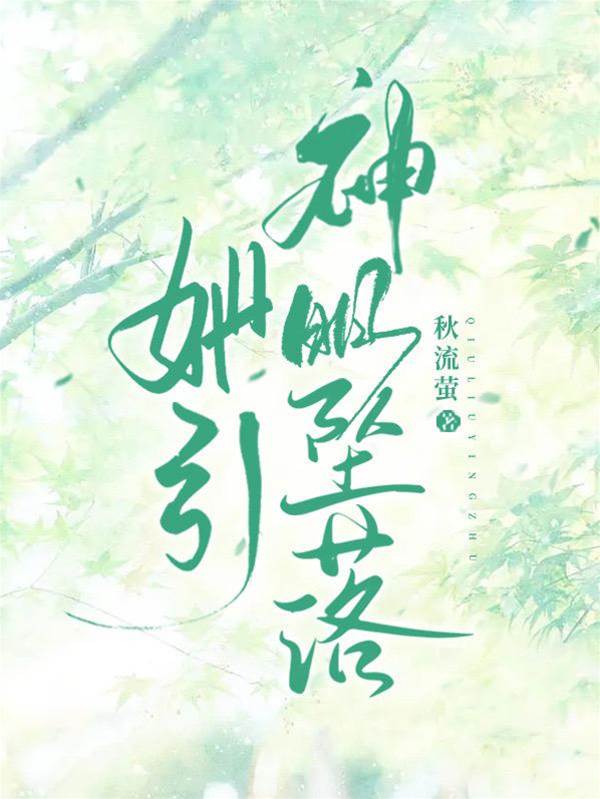
她引神明墜落
沈黛怡出身京北醫學世家,這年,低調的母親生日突然舉辦宴席,各大名門紛紛前來祝福,她喜提相親。相親那天,下著紛飛小雪。年少時曾喜歡過的人就坐在她相親對象隔壁宛若高山白雪,天上神子的男人,一如當年,矜貴脫俗,高不可攀,叫人不敢染指。沈黛怡想起當年纏著他的英勇事蹟,恨不得扭頭就走。“你這些年性情變化挺大的。”“有沒有可能是我們現在不熟。”宋清衍想起沈黛怡當年追在自己身邊,聲音嬌嗲慣會撒嬌,宛若妖女,勾他纏他。小妖女不告而別,時隔多年再相遇,對他疏離避而不及。不管如何,神子要收妖,豈是她能跑得掉。某天,宋清衍手上多出一枚婚戒,他結婚了。眾人驚呼,詫異不已。他們都以為,宋清衍結婚,不過只是為了家族傳宗接代,那位宋太太,名副其實工具人。直到有人看見,高貴在上的男人摟著一個女人親的難以自控。視頻一發出去,薄情寡欲的神子人設崩了!眾人皆說宋清衍高不可攀,無人能染指,可沈黛怡一笑,便潦倒萬物眾生,引他墜落。誰說神明不入凡塵,在沈黛怡面前,他不過一介凡夫俗 子。
20.2萬字8 45509 -
完結80 章

幸福不脫靶
他連吵架時擲出的話都如發口令般短促而有力:“不許大喊大叫!給你十秒時間調整自己,現在倒計時,十,九……” 她氣憤:“有沒有點兒時間觀念?需要調整十秒鐘那麼久?” 他是個很霸道的男人,對她裙子長度引來的較高回頭率頗有微詞:“你可真給我長臉!”見她呲牙笑得沒心沒肺,他板起來臉訓她:“下次再穿這麼短看我不關你禁閉。” 她撇嘴:“我是滿足你的虛榮心,搞得像是有損安定團結一樣。” 我們的小心願,幸福永不脫靶。
24.6萬字8 90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