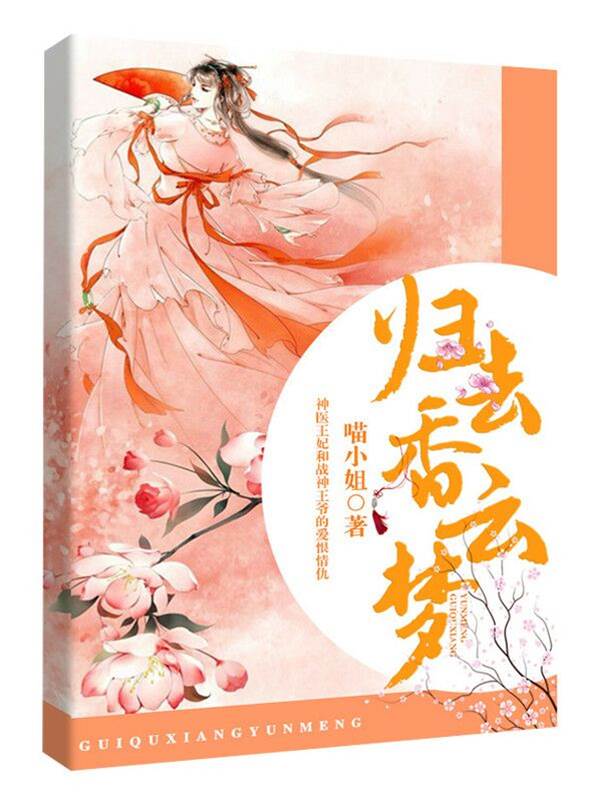《梟虎》 初爭執 小鬧怡情
初爭執小鬧怡
趙虓把摟在懷裏,腦子裏納著悶,覺這月的變化真可說是翻天覆地的大。尤其今兒勸言的這番話,著實讓他料想不到。
此前瑟畏懼那模樣還印在他腦海裏,是什麽讓忽地有了敢直陳利弊,不顧綱常地與他頂撞的膽量?
聯想態度的轉變,對他說話的語氣,瞧他的眼神……難道這是心不在他上了?
寧悠自然不知道趙虓這一筋的腦子裏竟想著這個,還緩著,他已氣勢洶洶地再度抵上來。
“殿下,不要了……”
氣地推他,可趙虓兀自氣著,哪管肯不肯,掰開便將那壯什了進來。
這一下讓痛得直,見他置若罔聞如此魯來的,脾氣也蹭地上來了,推著他的膛迫他退出去。他巋然不,錮著不讓躲,則蚍蜉撼樹,死抓著他手臂跟他較勁兒。
兩人互不相讓地擰著,寧悠力弱,被他攥得腕子都紅了,痛了,還是咬著牙不吭一聲,倒是不慎把他胳膊上抓出幾道印子來。
趙虓一頓,寧悠這才知畏。
前兒還在想著伴君如伴虎,怎就這樣不理智起來?哪怕他不治的罪,就是脾氣上來給一掌也夠得了。
可這回卻想得是,忤逆便忤逆了,要殺要剮,且看他如何吧!
趙虓著的眸,剛沖上腦門的反而消退下去,見一副要與自己同歸于盡似的堅決,只得作罷。撒了手,扭過胳膊看了看被抓傷的地方。
好麽,這向來溫順的兔子似的,也會撓人了。
他跪坐著,嘆了口氣,“何故這麽抗拒我?”
何故?這還需問?
他實在壯實,整個人像座山似的巋巍在跟前,更不要說底下那什有多雄偉,就這麽毫不客氣支棱地對著。
Advertisement
寧悠憤,幹脆別開臉不看,氣著道:“并未。”
“并未?”趙虓著下轉過來,“看也不願看我,這并未?”
只得怨懟地看向他。
趙虓覺著自己八是落什麽病了,被又是抓又是打地,還這般大不敬地瞧著,怎麽忽然就一點兒惱不起來?
他一陣煩躁,道:“你是厭我了,還是倦了跟我做這事了?”
這是哪來的定論?寧悠匪夷所思,“殿下何出此言?怎就忽然說到厭了倦了?”
“都沒有?”
見他作真問此,登時氣急:“妾怎麽會,這才親多久,妾心悅殿下還來不及,怎至于……您怎能這般想我!?”
心悅?方才是說了心悅吧?
趙虓這才安心了,上來,摟著囫圇地吻,胡茬蹭得臉頰刺痛,“那前面兩回舒服那樣,難道是做出來給我看的?怎得忽然就不讓弄了,還一副堅貞不屈的模樣?”
這男人的腦子到底是怎麽長得?
寧悠真個是佩服,捶他道:“再是舒服了也該有個度不是?妾勸著殿下節制,殿下不聽也就罷了,可妾的子也得能承得住您的恩澤啊。這一晚上三五回地來,誰人得了!妾現在渾無一不酸痛,殿下何曾問上一句?關切半點?妾也是個活生生的人,不該是殿下洩的工和玩!”
還沒提他行事孟浪、沒輕沒重,事後不幾日上總是莫名有淤青,想是被他、撞如此。自己是什麽力氣,自己不知收著些麽?何時才懂什麽溫?
趙虓被斥得無,訝然道:“我還以為你是拒還迎……合著真是弄得痛了?”
寧悠適時示弱,噙著淚點點頭。
“哪兒疼?”
“腰疼,也疼……尤其那最疼。”
趙虓便將手移到腰眼上,笨拙地起來。
Advertisement
這太不似他的舉讓寧悠麻了一皮疙瘩,簡直覺得眼下這才仿佛置夢境一般。甚是不由懷疑,到底醒是沒醒?
直到他問:“從前也是著的?”
才如夢方醒地“嗯”了聲。
“為何早不說,忍到今日了才發作我?”
“妾不敢忤逆殿下。”
“現在卻又敢了?瞧這給我抓的。”
忙他胳膊:“妾不是有心……”
他哼聲:“這口惡氣想是憋得久了,忍無可忍,無需再忍?”
不敢應。
趙虓就算作默認,若有所思地道了聲“也好”,又說:“往後我盡量節制著。不過,你方才對我那指摘也未免有些得寸進尺。”
“妾指摘殿下什麽了?”
“什麽洩玩之說,簡直口無遮攔。今兒我不與你計較,往後你也引以為戒著些,別緒上來了就胡說八道的,沒個規矩。”
寧悠心說難道不是麽?就算沒這心思,所作所為可不就是這樣?
但念在他今日態度甚佳,更難得放下段伺候一回,就不和他爭個高低對錯了。
低眉順眼地答:“妾記著了。”
他手上力度不輕不重地正正好,寧悠被他得松乏愜意,舒服地枕在他口瞇眼小憩。
不多會兒,他停了下來,忽而問:“你說不是張公讓你來勸我,那你怎知左都相與我有何齟齬?建孜窮困更兼有雪之事,你又從何得知?”
寧悠心覺糟糕,這還難解釋了。
建孜城中況,這陣尚未探聽到什麽,天象更是變幻莫測。便是以張德謙與陳棠之運籌帷幄,也只能做大概猜測罷了,又怎敢比肩這二位呢?總不能說有觀天之才、能未蔔先知吧?
以後這樣事還多著呢,得好好找個讓他得以信服的理由。
稍思索一下,道:“從大玄騎帳中出來,恰好上張公,妾便問了他事因果。至于這建孜的況,父親以前略提過馬友此人,說他作戰雖勇,但無理政養民之才。妾覺著,建孜之地古來貧瘠,被他占據這六年,即便他休養生息積攢了些錢糧,但恐怕也沒遭到鄔延盤剝,想來只會更加窮困。”
Advertisement
趙虓仔細聽著,點點頭:“那降雪一說?”
“是妾猜測的。殿下作戰,總歸要考慮最壞的結果不是。冀北雖幹燥,但也偶有雨雪,妾昨日初來乍到,便覺得這兩日天氣意外潤,料想著恐怕會有一場雪。”
寧悠好容易編出這麽些來,楚楚地眨著眼,著趙虓,心說您可千萬別再往下問了。若再問,這點兒學識也就該見底了餡兒了。
幸好趙虓也真沒再問,瞧著的眼裏竟有幾分審視欣賞之意。寧悠只覺自己剛經了場大考似的,如釋重負下來。
老天爺好像也幫著自圓其說一般,當天夜裏,項梁大營就下了一場薄雪。
翌日寧悠早早起了,打算與趙虓同去請陳棠回來。
趙虓起後,看換了騎服,頗有些颯爽之姿。雖喜得挪不開眼,還是皺眉問:“今兒就準備開始練著了?”
寧悠伺候著他穿戴洗漱,搖頭道:“妾是要與您一道去見左都相。”
“怎麽,你還怕我食言,敷衍你不?”
遞上漱盂,道:“非是如此,只是想替殿下做些分憂解勞事。左都相那倔脾氣比之殿下不遑多讓,妾從中調和著,這事也就順當不是。早些將他請回來,也免得貽誤戰機。”
趙虓覺所言有理,便沒有拒絕。
從營房出來,見到帳子上有雪痕,他意外瞄了寧悠一眼,似有所悟地琢磨起來。明明有幾分遠勝男兒的聰慧德才,以前何以跟他藏著掖著的,故作怯懦模樣?
陳棠老家在順安往北十五裏的棲山縣草臺,自項梁大營過去有近二百裏地,快馬加鞭也得一日才到。為趕時間,趙虓安頓好諸事後,只帶了左聿的殿前十八衛輕裝簡行。
寧悠昨日剛得了匹好馬,今日拳掌地想單人單騎,他卻不允:“你與我同乘。”
Advertisement
“為何……”
才開口就被他打斷,“哪那麽多為何?”
當著左聿和衆侍衛,寧悠不敢駁他面子,只好乖巧應了。
他掐腰把托上馬背,自己跟著翻上來,拿披風把一裹,夾一下馬腹,對手下人喝道:“走!”
一出大營,他便揮鞭打馬,疾馳起來。
凜凜寒風呼啦啦地招呼在寧悠面上,十五歲的還細皮地,哪得住這刀剌似的刺痛。早料著有這一遭,便拿條帕子系在腦後,把臉半蒙住,總算能好上些許。
趙虓低眸掃,心下念叨著氣、麻煩,但手上還是把被風吹開的袍子給裹了些。
猜你喜歡
-
完結62 章

大佬的心尖寵[古穿今]
定王卿沉,俊美無儔,才貌雙絕,十九歲掛帥出征時從敵軍的陣營里撿回來一個小姑娘,小姑娘安安靜靜的從未說過一句話,整日將自己縮在一個巨大的黑色斗篷里,只敢躲在暗處偷偷摸摸的瞧他。 這麼一個膽小內向的小姑娘,卻在黑衣人偷襲時,不管不顧的沖出來替他擋了致命的一劍。 小姑娘醒來后穿成了一名十六歲的少女,又嬌又弱還患有心疾,被化身為年級大佬的王爺又撿回了家里,大佬桀驁乖張像頭舔血的狼,卻小心翼翼的把她捧在心尖上。 小劇場: 某日,一直縮在殼子里的小姑娘主動的伸出頭來,跑到他的房間里,眨巴著大眼睛,癟嘴道:“房間里好冷……” 某王爺十分正經的從柜子里又拿出了一床被子遞給她。 而最后的最后,卻是某王爺的手僵的不知道該往哪處放,懷里還拱著一個小姑娘。 卿沉:娶她,是他一千年前便想做的事情。 食用指南:又冷又暴躁的年級大佬X又乖又軟萌的小姑娘 1V1甜寵!不甜你打我! 男主一步步的把女主寵成粘人精,古代的故事是雙向暗戀。 男主只是剛開始失憶了,他和古代的王爺是一個人!
16.4萬字8 18080 -
完結1000 章

嬌妻傻婿
顧義,顧財主家的“傻”兒子,一不小心失足落水,嗆昏了。宋宛月正好路過,給他做了人工呼吸,救活了。本以為會得到豐厚的報酬,卻不想人家上門提親了。宋宛月傻了,宋家人怒了。宋老大:“我就這一個心尖上的女兒,這輩子不准備讓她嫁人,出門左拐,慢走不送。”宋老二:“癩蛤蟆想吃天鵝肉,讓他多照照鏡子!”霸氣的宋奶奶:“這麼多廢話幹什麼,把他們趕出去!”躲在門外偷聽的男主“哇”一聲哭了,“她親了我,若是不嫁給我,我就一輩子娶不上媳婦了。”眾人:……
174.5萬字8.33 67385 -
完結13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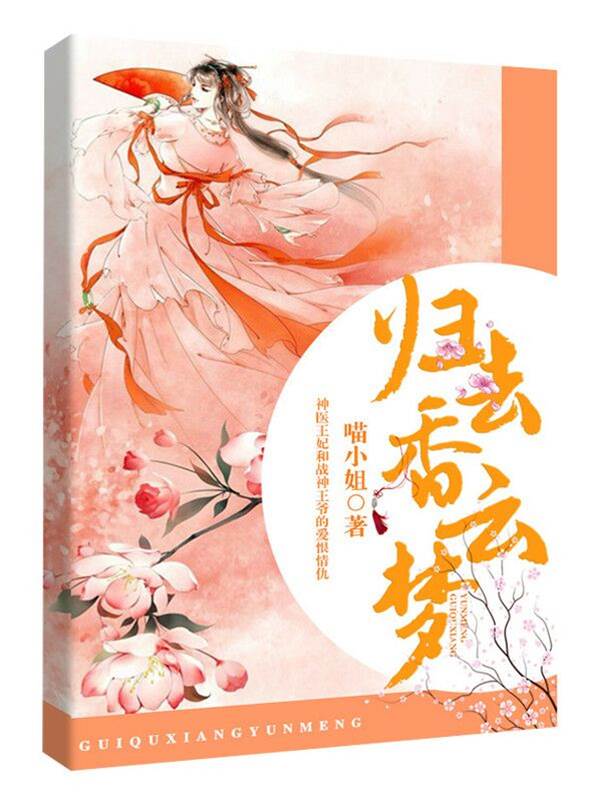
歸去香雲夢
前世女學霸意外穿越竟變成了一個傻子!賭場賺錢發家致富,英勇智鬥心機綠茶,裝傻挑逗帥氣鮮肉,卻意外落入感情陷阱......
22.4萬字5 1632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