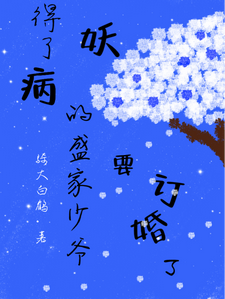《美強慘重生后,被病態容爺纏哭了》 第1卷 第101章 你是我藏的男人
這晦氣家伙怎麼突然回來了?
虞婳看了眼時間,這才下午兩點鐘,容硯之不是應該在公司麼?
逢臨慌慌張張,到找躲藏的地方,甚至打開了柜。
程無雙卻是站直,一副無所畏懼的樣子。
逢臨急忙拉著要一起躲進柜里。
程無雙甩開,一正氣,“我沒干什麼虧心事,躲躲藏藏像什麼樣子?”
“我就不信,容硯之連朋友的權利都不給虞婳。”
逢臨不死心,又拽住程無雙手腕,“我跟你說真的,容硯之太危險了,咱們先藏起來……你都不知道……”
“行了。”虞婳打斷,著額頭,白了逢臨一眼。
“你這鬼鬼祟祟的樣子,不知道的還以為,你是我藏的男人。”
容硯之那智商,以及行力。
虞婳再也不敢小看他了。
他這個時間段回來,必然是知道逢臨帶著程無雙來找了。
逢臨突然帶個陌生人來水榭莊園。
容硯之疑心重,有了風聲,肯定會回來看看是怎麼個事。
他現在最怕跑。
逢臨一噎,“那現在怎麼辦?”
虞婳淡定道:“既來之則安之,容硯之沒資格管我社圈。”
外面的王叔又敲了下門,“夫人……”
“回來了就回來了,”虞婳出聲,冷淡道:“怎麼?難不還要我頂著這副軀親自下樓放鞭炮迎接嗎?”
王叔怔了怔,說:“爺得知您朋友來了水榭莊園,特意回來招待……”
虞婳:“……”
就知道,容硯之忽然出現沒什麼好事。
呼了口氣,捂著口下床。
程無雙見狀連忙上前扶住,擔憂地蹙眉,“你先躺床上去吧。”
虞婳擺手,虛虛地站起來,“我沒事,走兩步路還是可以的。”
Advertisement
不能讓逢臨和程無雙兩個人去面對容硯之。
誰知道容硯之會不會突然發神經。
虞婳穿好鞋,巍巍地走到了門口。
打開門的瞬間,王叔轉頭離開。
容硯之頎長高大的軀映了虞婳眼簾。
虞婳:“……”
男人筆直地站著,笑意不達眼底,看起來格外危險,視線懶洋洋地在虞婳后的逢臨和程無雙上游離了一圈。
只是被簡單看了一眼,程無雙就覺到了窒息,像被無形的手鎖住了嚨。
曾經以為,容硯之只是在傳聞里恐怖如斯。
如今只是見一眼,就怯了膽。
默默挪到了逢臨后。
逢臨:“???”不是姐,你剛才的氣勢呢?
逢臨干笑一聲,對容硯之解釋道:“那什麼,我就是擔心阿……虞婳,特意來看看好了沒。”
容硯之薄輕掀,“我這都還沒問,你急著解釋什麼?”
“我夫人平時朋友不多,逢先生既然這麼有心,我也不好多說什麼。”
逢臨尷尬一笑,又拉住程無雙的手,帶著緩緩挪,背門墻,十足,“是吧,我們真的就是簡單的聊聊天,容爺千萬別多想,要,要是沒什麼事,我們就先走了。”
他跟程無雙繼續待在這里只會給虞婳添麻煩。
總不能不怕死的跟容硯之抬杠頂。
能做的只有默默離開。
程無雙頭皮發麻,覺都不是自己的了,只能被逢臨牽著鼻子走。
但潛意識,還是告訴不能丟下虞婳。
正要甩開逢臨,跟容硯之對抗。
就聽到容硯之出了聲,“等等。”
逢臨腳步頓住。
容硯之看了看虞婳,又抬起流暢冷的下頜,指了指程無雙方向,“新朋友嗎?不介紹一下?”
Advertisement
程無雙立馬跟蔫兒了的花朵似的,方才蓄力的勇氣,仿佛一下被磨平。
容硯之地位太高。
可以說全京城的人,都要看他臉過日子,仰仗著他。
想到容硯之網傳的各種罪行。
有點虛了,若是形單影只,沒有家人,一定會虞婳兩肋刀,才不管這個男人多厲害呢。
可偏偏有家人,而且家人在京城也是響當當的人。
不能拖累家族。
好氣啊,一勁頭無發泄。
腳尖過鞋子地板,咬牙切齒。
“夫人,你的這位新朋友似乎對我很不滿?”
程無雙是個不會偽裝的人,喜怒都寫在臉上。
別說容硯之擅長觀測人心,就是不擅長,也能看出這人對自己的不滿。
虞婳扯,深吸了口氣,散漫道:“容硯之,你嚇到我的朋友了。”
容硯之怔愣半秒,隨即淡然道:“那真是抱歉。”
察覺到他的怪氣,虞婳也懶得計較,“讓他們先走,有什麼事,你來問我不是更好?”
容硯之:“我有說不讓他們走?我只不過是想知道我夫人這位新朋友什麼底細,有錯?”
程無雙雖然害怕容硯之,但也不想虞婳被為難,所以主介紹自己,“我、我程無雙。”
“姓程?”容硯之別有深意,“京城姓程的名人可不,我就認識幾個,你父親什麼名字?”
程無雙渾冰涼,現在只后悔為什麼沒有聽逢臨的,躲進柜里藏起來。
虞婳不悅,“容硯之,你能不能別嚇我朋友了?”
“我就是好奇。”容硯之抬了抬下頜,“好心”問倆人,“有車嗎?我讓司機送你們離開。”
逢臨知道這是下逐客令的意思,其實不用下逐客令,他們本來就待不下去了,想趕跑。
Advertisement
“有車有車,不用送,我們這就走。”
逢臨和程無雙直接遁了。
倆人離開前還不忘給虞婳一個心疼的眼神。
見他們走了,虞婳松了口氣。
容硯之漆黑深邃的眸翳,視線定格在虞婳上,眸在口上下游離。
“不疼嗎?跑下床。”
虞婳:“你突然回來查崗,比疼死更可怕。”
說完,轉過,慢慢走向床。
容硯之進了房間后,關上門,邊說:“你要是不做虧心事,害怕什麼?”
好一個莫名其妙的理論。
虞婳懶得跟他爭,躺回床上,蓋好被子,閉眼捂不理他。
容硯之嚨溢出一聲低磁的輕笑,緩緩走到虞婳邊。
這時,目被一旁的邀請函吸引了過去。
他抬起頎長的指尖,捻起了那封邀請函,淡淡道:“S.T研究院?”
虞婳一僵,睜開眼,看見邀請函落到容硯之手里,下意識出手想搶。
猜你喜歡
-
完結293 章

以歲月換你情長
她是寄人籬下的孤女,他是成熟內斂的商業奇才。 一場以利益為前提的婚姻,把兩人捆綁在一起。她不過是他裝門麵的工具,他卻成了她此生無法消除的烙印。 真相敗露,他用冷漠把她擋在千裏之外;極端報複,讓她遍體鱗傷。 她傷心欲絕想要逃離,卻意外懷孕;反複糾纏,他們一次又一次陷入了互相傷害的死循環裏無法自拔。 四年後歸來,她不再是從前軟弱、備受欺淩的宋太太……
72.1萬字8 844570 -
完結528 章

離婚後我撿走霸總的崽
沒有生育能力的喬依被迫離婚,結束了四年的感情。心灰意冷之下去小縣城療養情傷,卻無意中拾得一個男嬰。出於私心,喬依留下孩子撫養。四年後,一排鋥亮的高級轎車停到喬依的樓下。顧策掏出一張卡:這是兩百萬,就當這四年來你撫養我兒子的酬勞。喬依把孩子護在身後:孩子是我的,我不可能和他分開!顧策邪魅一笑:那好,大的一起帶走!
80.3萬字8.09 95956 -
完結112 章

乖不如野
都說女追男隔層紗,秦詩覺得沈閱是金剛紗。明明那麼近,她怎麼也摸不到。 沈閱是秦詩的光,秦詩是沈閱的劫。 秦詩見到沈閱,就像貓見到了老鼠,說什麼也要抓到,吃掉。 原以爲是一見鍾情,後來沈閱才知道,他竟然只是一個影子。 他從未想過,他會成爲別人的替身。 那天,秦詩坐在橋上,面向滾滾長江水晃着兩條腿,回頭笑着對沈閱說:“我要是死了,你就自由了。我要是沒死,你跟我好,好不好?”
19.8萬字8 1325 -
完結11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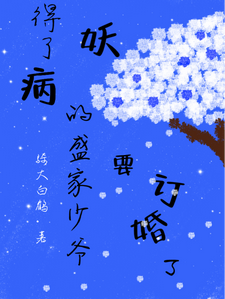
得了妖病的盛家少爺要訂婚了
因為自家公司破產,弟弟生病,阮時音作為所謂未婚妻被送進了盛家。盛家作為老牌家族,底蘊深,財力雄。 而盛祁作為盛家的繼承人,卻極少出現過在大眾眼中,只在私交圈子里偶爾出現。 據傳,是有不治之癥。 有人說他是精神有異,也有人說他是純粹的暴力份子。 而阮時音知道,這些都不對。 未婚妻只是幌子,她真正的作用,是成為盛祁的藥。 剛進盛家第一天,阮時音就被要求抽血。 身邊的傭人也提醒她不要進入“禁地”。 而后,身現詭異綠光的少年頹靡地躺在床上,問她:“怕嗎?” 她回答:“不怕。” 少年卻只是自嘲地笑笑:“遲早會怕的。” “禁地”到底有什麼,阮時音不敢探究,她只想安穩地過自己的生活。 可天不遂人愿,不久之后,月圓之夜到來了。 - 【提前排雷】: 女主不是現在流行的叱咤風云大女主,她從小的生活環境導致了她性格不會太強勢,但也絕對不是被人隨意拿捏的軟蛋,后面該反擊的會反擊,該勇敢的照樣勇敢。我會基于人物設定的邏輯性去寫,不能接受這些的寶子可以另覓佳作,比心。
2.1萬字8 65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