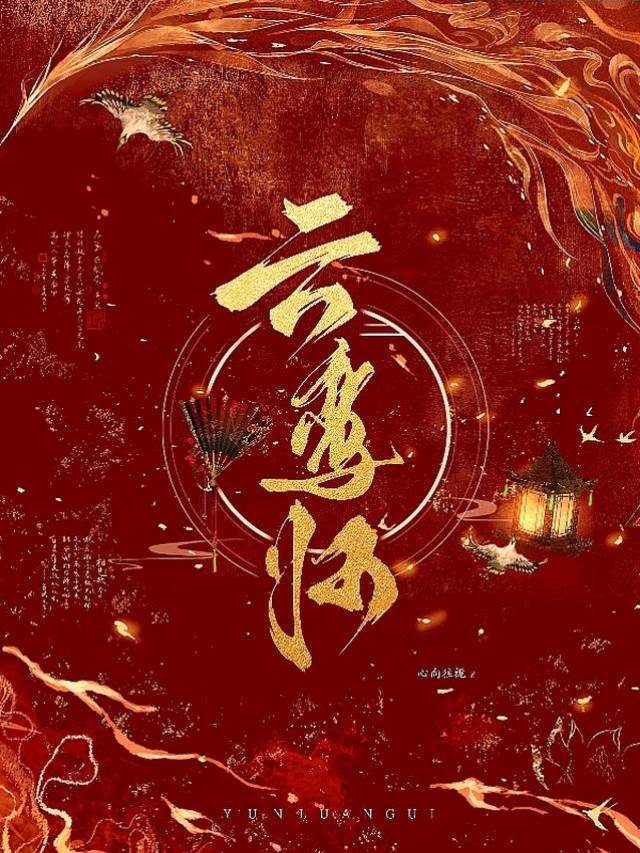《掩嬌啼》 第57章 你變了!
更別說越明珠去送酸梅湯時,裴晏遲顯而易見的寬容跟優待。
不過即便是他也沒有想到,裴晏遲轉眼跟皇帝求了賜婚,婚後還這般如膠似漆。
……捉不,捉不啊。
砰砰兩聲,房門被叩響,是莊河呈上裴晏遲要的相關所有邸報。
見狀,顧詠沒有再多待。
隔壁耳房裏裝潢樸素整潔,有一張裴晏遲平日用來午休的小榻,越明珠歇在上頭閑著沒事,隨手拿過書架上的書開始翻閱。
裴晏遲看的那些書不比市井街坊的話本,全都看不懂,盯著麻麻的白紙黑字直人犯困。
還好他有在旁邊批注的習慣,越明珠幹脆只看他的批注了。
裴大公子字如其人,矯若驚龍,筆三分,哪怕越明珠不懂書法,也覺得這字跡十分賞心悅目。
這回專門拿的是一本風土志,因為這種書上面圖多,看起來稍微有趣一點。
草草翻過幾頁,越明珠才發現這上面標的地名有點眼。
好像在哪裏聽說過。
越明珠重新翻回第一頁,後知後覺地見書名跟前言提到了杭州府。
好巧,竟然是老家的風土志。
越明珠坐直子,聚會神地翻了翻。
往後幾頁,裴晏遲勾出了地圖上幾,又在下面筆者的解釋裏劃了一句話——
依其奇巒獨貌,山四通八達,山避世不出。
越明珠看了半天,發現他勾的全都是山。
咦。
他怎麽專門標記了這種地方。
越明珠在那兒生活了十餘年都沒有聽說過這個偏僻的地名。
……難道是他之前南下鎮端王之時所需?
正胡思想著,門外忽然響起了裴晏遲的嗓音:“明珠,走了。”
每本書都草草翻兩頁,翻過半個書架,竟然不知不覺就打發走了一個多時辰。
Advertisement
越明珠起將風土志塞回原,連忙推門跑出去。
裴晏遲括頎長的形站在門外。天比剛剛暗了許多,走廊上掛起燈籠,暖的灑落在他墨黑的錦服,平白令他多了幾分人味。
越明珠一眼就看見他的襟有些淩。這男人卻還鎮定自若地站在那兒等,似乎恍若未覺。
一想到等會兒離開通政司的路上會見很多人,越明珠提醒道:“你要不理一理襟?”
裴晏遲看了一眼,提醒道:“好像是你之前弄的。”
越明珠走過去,踮起腳尖,手替他糙地整理了一下。
理完之後,才問:“子淮哥哥,你剛剛自己沒發現嗎?”
裴晏遲:“是嗎,沒發現。”
越明珠心中一:“那你剛剛沒見人吧?”
裴晏遲:“見了。”
“…………”
裴晏遲故意道:“好像見了多人的。”
越明珠的小臉一下子垮了下來:“那怎麽辦?這看起來這麽明顯,別人肯定都看得出來……”
若不是越明珠臉皮薄,主要替他理,裴晏遲其實完全不介意頂著剛剛的襟離開通政司。
他不大在意地道:“我跟我自己的夫人親熱而已,不是很正常?”
越明珠心頭一,實在不知道裴晏遲怎麽能頂著這張冷得生人勿近的臉說出這種話。
強調起這件事的嚴峻:“你的同僚要是知道你是這種人,背地裏肯定都會說你的。”
很意外,裴晏遲竟然頷首附和:“我的確已經聽到了。”
越明珠皺起眉:“他們肯定都會笑……”
裴晏遲:“很多人說我們很恩。”
越明珠凝噎。
裴晏遲著,好像沒看見的臉紅得可以滴,緩緩補充:“——我也覺得。”
越明珠聽不下去了,覺得來這兒接裴晏遲好像是個錯誤:“我們還是快點回去吧。”
Advertisement
外邊的天已經暗了下來,離開的路并不是來找裴晏遲時的那一條,人很,一路上就見零星幾道人影,并且分外短暫,幾步路後就坐上了馬車。
越明珠本來想像從前那樣坐到裴晏遲對面的,然而剛一上去,就被男人攬到了他上。
剛剛在墨齋裏就是這個姿勢,越明珠沒覺得有什麽不對。
車轂聲漸起,馬車行駛向太傅府。
即將回到悉的地方總會讓人放松一些,越明珠倚過去跟他講話:“我的紅糖米糕你吃了嗎,味道怎麽樣?”
當然是不出所料的非常難以恭維。
裴晏遲斟酌著用詞:“比較有新意。”
這聽上去像是個誇贊,越明珠眼睛一亮:“那我明天晚膳再給你做吧!”
廚娘可都誇做得賣相極好,本不像是新手。越明珠一被誇就高興,原本還不習慣下廚,如今倒起了興致。
裴晏遲沒應,就當默認了,接著問:“那湯藥呢?”
裴晏遲:“喝了一半。”
越明珠想了想:“那如果娘問起來,我就說你喝完了。”
低聲解釋道:“這好像是專門找人開的方子,用很多天材地寶熬了兩個多時辰,要是知道被你浪費了,肯定很可惜……”
聲音戛然而止。
越明珠向裴晏遲。
在上下顛簸當中,有什麽存在異常突出。
“怎麽不繼續說了?”男人一臉平常地道,“我也很好奇這碗湯藥的來頭。”
他看上去跟剛才沒什麽區別,然而越明珠又到悉的存在正擡頭起來,即便隔著裳都人難以忽視。這反應對而言已經全然不陌生。的臉驟然一熱:“這可是在外邊,你想幹什麽?”
白日裏明明才警告過他,裴晏遲怎麽一轉眼就明知故犯了。
Advertisement
到底有沒有把的先禮後兵放在心上!
裴晏遲慢條斯理地說了兩個字。
越明珠覺自己純潔的耳朵又瞬間被污染了:“你你你你你——”
曲起的指節叩著椅面,裴晏遲的表跟他下的表現完全南轅北轍。
剛剛才說了幹。你兩個字,他面上仍是平靜無波,唯獨語氣出一點危險:“我也想問你,專門送壯。的湯藥給我是做什麽。”
突然出現那些雜事,他心本來就不算好。
以至于剛喝下去還沒注意到問題。
等一個多時辰過去,才發現這煩躁得有些過了。
遠遠超出了他平日的反應。
“……!?”
越明珠杏眼圓睜,反應劇烈:“你不要污蔑我!”
裴晏遲摁住,擡起眼皮,緩緩興師問罪:“是嗎,剛剛那碗湯不是你。著我喝的?”
他每回用詞都如此鄙,越明珠氣呼呼地道:“你能不能不要講,那是娘給我的,說現在天寒,你喝點熱乎的暖暖子,我只是……”
不用想也知道這肯定不是越明珠的主意,若是有這樣的膽量,也不至于到現在還要跟他慢慢習慣彼此的。
不過這并不影響裴晏遲借題發揮。
在的注視中,他毫不留地問:“剛剛是誰端來讓我喝的?”
越明珠又被他問得啞口無言,半晌才憋出一句話:“這也不能怪我,那個,聖賢說,不知者無罪……”
裴晏遲:“我沒有怪你。”
“不過,”男人瞇了瞇眸子,在充滿希冀的弱注視之中,緩慢地吐出字眼,“誰挑起的,是不是應該誰解決?”
這個解決聽上去好像不是普通的解決,越明珠腦子嗡嗡的,囁嚅道:“這應該不是我們今晚應該習慣的容吧……”
裴晏遲:“提前習慣也不會有很大區別。”
Advertisement
越明珠不大相信,當即想要起坐到對面去,但剛一,屁。就被他警告似的扇了一下。
力道不重,恥比疼痛更明顯,越明珠覺自己的臉瞬間要被燙化了:“你怎麽還打我!”
裴晏遲并未回答,他陡然發現這裏手很好,比的前更為彈潤,于是便順手了一,又對上那張紅得跟番茄似的臉蛋,不不慢地道:
“免得你再。”
越明珠拍開他的手。人一惱就容易口不擇言,控訴道:“你變了,我以前在你上你都不會這麽不耐煩的!”
本以為裴晏遲會反駁,沒想到這男人一頓,幹脆地頷首應道:“確實變了。”
越明珠一愣。
裴晏遲凝視著神的變化。
湯藥帶來的谷欠念并非完全無法忍跟消解。
越明珠若是還沒有準備好,他其實并不介意再跟其他的地方習慣習慣。
現在膽量雖然比之前大了不,但距離最後一步,總是還需要一些時間。
裴晏遲很清楚。
他窺視著越明珠太久,比越明珠想象中還要更了解的。
越明珠子溫吞慢熱,對人對事都喜歡細水長流,要非常悉才會主起來。
那并不是他曾經擁有的特權。
因此他貪得無厭,想要從頭到尾慢慢變得主的過程。
哪怕比他想象中慢很多都可以。
哪怕只有一個月的時間,他也可以等。
……然而那樁措手不及的案子實在很讓人煩躁。
僞裝下某些惡劣的又開始蠢蠢。
“所以,明珠,”男人開口,嗓音似乎比平時都要低啞,“我們已經準備得差不多了,應該重新地、徹底地習慣一下彼此。”
猜你喜歡
-
完結480 章

穿書之沒人能比我更懂囂張
––伏?熬夜追劇看小說猝死了,她還記得她臨死前正在看一本小說〖廢材之逆天女戰神〗。––然后她就成了小說里和男女主作對的女反派百里伏?。––這女反派不一樣,她不嫉妒女主也不喜歡男主。她單純的就是看不慣男女主比她囂張,在她面前出風頭。––這個身世背景強大的女反派就這麼和男女主杠上了,劇情發展到中期被看不慣她的女主追隨者害死,在宗門試煉里被推進獸潮死在魔獸口中。––典型的出場華麗結局草率。––然而她穿成了百里伏?,大結局都沒有活到的百里伏?,所以葬身魔獸口腹的是她?噠咩!––系統告訴她,完成任務可以許諾...
86.1萬字8 11706 -
完結28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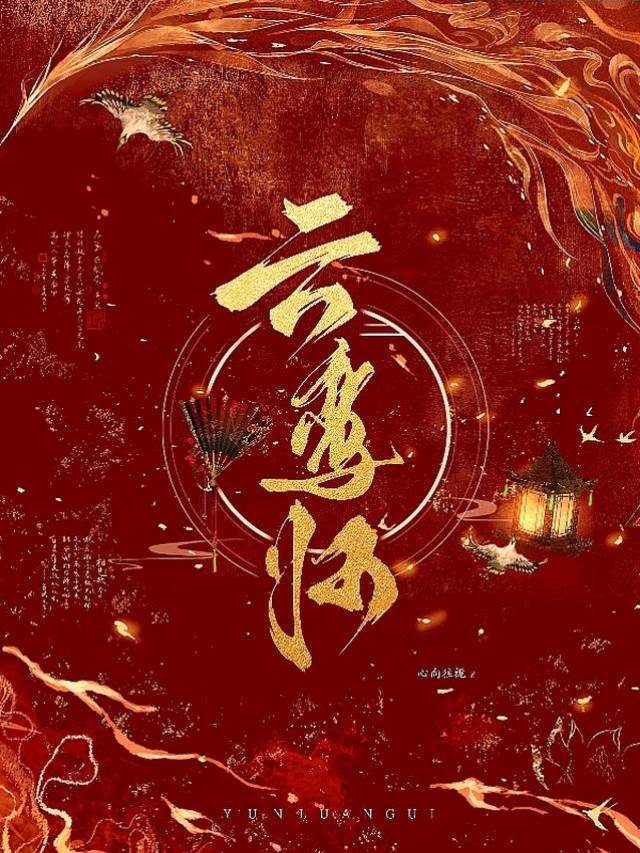
雲鸞歸
【黑蓮花美人郡主&陰鷙狠厲攝政王】[雙強+甜撩+雙潔+虐渣]知弦是南詔國三皇子身邊最鋒利的刀刃,為他除盡奪嫡路上的絆腳石,卻在他被立太子的那日,命喪黃泉。“知弦,要怪就怪你知道的太多了。”軒轅珩擦了擦匕首上的鮮血,漫不經心地冷笑著。——天公作美,她竟重生為北堯國清儀郡主薑雲曦,身份尊貴,才貌雙絕,更有父母兄長無微不至的關愛。隻是,她雖武功還在,但是外人看來卻隻是一個病弱美人,要想複仇,必須找一個位高權重的幫手。中秋盛宴,薑雲曦美眸輕抬,那位手段狠厲的攝政王殿下手握虎符,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倒是不錯的人選。不近女色,陰鷙暴戾又如何?美人計一用,他照樣上鉤了。——某夜,傳言中清心寡欲的攝政王殿下悄然闖入薑雲曦閨閣,扣著她的腰肢將人抵在床間,溫熱的呼吸鋪灑開來。“你很怕我?”“是殿下太兇了。”薑雲曦醞釀好淚水,聲音嬌得緊。“哪兒兇了,嗯?”蕭瑾熠咬牙切齒地開口。他明明對她溫柔得要死!
42.5萬字8 2182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