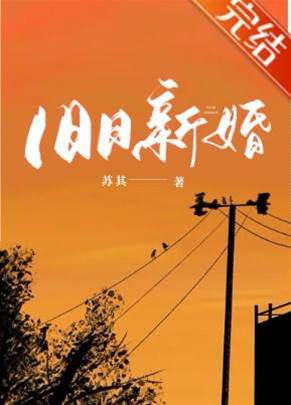《在前夫他心口上撒鹽》 第1卷 第67章 腫瘤醫生在誑我
他一把奪走菜刀,“當啷”一聲甩到了墻角,厲聲呵道:“你又干什麼!”
“我……”我著他震怒的臉,吞了吞口水,竭力讓自己的聲音不要發抖,“做、做菜……”
五分鐘后。
我坐在椅子上,繁華打開藥箱,拿出創可。
我手說:“我自己來就好了。”
他舉起手,避開我的手,睖了我一眼道:“出來。”
我只好把手給他,說:“謝謝了。”
“……”
“你為什麼突然這麼著急?”我問,“是以為家里來壞人了嗎?”
“……”
還是不說話。
罷了,我也不說了。
可能只是做噩夢了吧……
因為只有一只手,他的作有點慢,但還是順利地包好了。
我看了看手指,說:“謝謝。”
繁華臉稍緩,靠到椅背上,瞧著我問:“你做飯就做飯,給我塞個枕頭干什麼?”
“就……撐著你的手。”我說:“怕著它。”
繁華又瞪了我一眼:“多此一舉。”
“……你到底是誤會了什麼呀?”
我塞的是枕頭,又不是什麼危險品。
繁華兇狠地睕了我一眼,說:“出去。”
我說:“我還要做飯呢。”
“出去等著。”他站起,說,“看到你就來氣。”
說完,他走過去把刀撿了回來,放到水龍頭下沖洗。
我知道現在最聰明的舉就是出去,但我還是站在了原地,說:“你不會是覺得我想自殺吧?”
果然,繁華洗菜的作一停,微微側頭,睖了過來。
他的目好危險,我小聲說:“算了,我還是出去……”
“過來。”
他還握著菜刀呢。
Advertisement
我說:“不要了,我到外面去。”
“過來打蛋。”
我小心翼翼地走過去,充滿警惕地從他邊經過,打開冰箱,拿出了蛋。
沉默……
繁華練地切菜,果然大小都一樣,是個仔細的人。
我也仔細地打著蛋,并聰明地站在他的左邊,且跟他保持一米以上的距離,這樣就能在他突然發飆時爭取一點時間。
正想著,忽然,繁華開了口:“過來。”
我瞅瞅他手里的刀:“做什麼?”
“讓你過來。”他抬起眼,似笑非笑地瞟過來,“有話跟你說。”
我說:“你在這里說就好了,我聽得到。”
繁華咬了咬。
我警惕地退了一步。
對峙。
忽然,繁華丟開刀,朝我走了過來。
我趕轉跑,他卻一把就把我按到了流理臺上,說了一句:“趴著。”
然后,伴隨著一聲悶響,子左邊傳來一陣冷氣。
不用抬頭我就知道,是他打開了冰箱門。
我現在在流理臺的角落,而冰箱在我的子左邊。所以他打開門時,冰箱門的下沿幾乎是著我的后背。
所以我徹底起不來了,只能趴在這里干等。
老半天,繁華才重新關上了門,在我上拍了一把:“起來吧。”
我看了一眼,說:“沒事我就走了。”
他卻沒說話,在我的后,手把我圈在了里面,一邊拉出案板,將手里那塊通脊沖了沖,放上去,說:“摁著。”
遂出了切刀。
我按住,問:“這樣行……等等!不是這里,這是我的手……”
怎麼一直在我的手指上比劃!
“加點筍更鮮。”他說著,刀鋒下,按上了我指尖的創可。
Advertisement
我這會兒已經不走了,只好低聲說:“你不要……”
“就兩。”
語氣一本正經。
我只能搖頭。
我本就吃不準他會不會切下去,畢竟他已經不是第一次擊穿我的底線了!
“那就一。”繁華聲說著,按住了我的手,“別,瞄好位置,從關節上下刀比較快,不然在骨頭上拉來拉去的,容易苦。”
我頓時泛起了一的皮疙瘩:“你別說了,太恐怖了……”
一邊用力甩開他的手。
“嘶——”后傳來吸氣的聲音。
我不由得一僵,抬眼見繁華正白著臉咬著牙,遂低頭,見剛剛被我甩開的那只手,正是他傷的左手。
一時間我也不知該說什麼。
雖然我到了他的傷口,但這不是我的錯,是他要切我手指在先。
而且雖然左手放開了,但左邊本來就是角落,他拿著刀的右手還擋著呢。
良久,繁華放下了切刀。
我放松了幾分,這時,他又摟住了我的腰。
脖頸上傳來的覺,是他的鼻尖在我的脖子上,深深地吸氣,喑聲道:“我懷疑腫瘤專家在誑我。”
“……”
我不敢說話,生怕自己一句話就激活了他。
“其實你平時也冷淡的。”他說著,手住我的臉,轉過來面對他。他則微微瞇起了眼,端詳著我道:“滋味兒倒也不壞。”
“……”
好害怕。
“自己決定吧。”他忽然松開手,拿起了切刀,“吃筍還是吃你。”
我說:“吃吧。”
“不如你。”他說著往下,我只能再次趴下,勉強用手肘撐在作臺,看著他拿起了磨刀石,聲音在磨刀的霍霍聲中顯得有些含糊,“自己選吧,我不強迫你。”
Advertisement
唉……
這還有什麼可想的?
我把手放到案板上,說:“吃筍吧。”
“好。”繁華說著,舉起了刀。
我連忙閉起眼。
安靜……
難道沒有切?
我睜開了眼。
正好看到,刀鋒停在我的手指上。
他往下一,我不由得驚了一聲,下意識地攥起手指。
與此同時,刀鋒往下,片下了薄薄的一片通脊。
我的后背都被冷汗浸了……
繁華把那片通脊在案板上擺好,低頭咬了咬我的耳朵,“嚇得都了。”
我呼吸不暢,說不出話,索趴到作臺上,把臉埋到了手臂里。
過了好一會兒,忽然聽到刀放到案板上的聲音,臉頰邊傳來溫熱:“哭了?”
“……”
“好了。”他的手掌在我的肚子上了,哄小孩似的說,“逗逗你罷了,我還能真切麼?”
我說:“你把手拿開……”
“……”
他不沒拿開,還探了進去。
我捉住他的手,抬起頭說:“你剛過生,有細菌,不要我。”
猜你喜歡
-
完結582 章

BOSS主人,幫我充充電
一次失敗的手術,她意外變成了暗戀男神的私人機械人,且,還是情趣型的……顧安寶覺得她整個人生都要崩潰了!——天啊……我變成充氣娃娃了???主人在遠處沖她...
104.5萬字8 10421 -
完結523 章

可不可以爱上你
相愛三年,她曾許願能同他白頭偕老,相愛一生。卻不想,到頭來都隻是自己的一廂情願。直到後來,她重新擁有了他,卻不明白,為什麼心卻更痛了。
90.5萬字8 26921 -
完結134 章

離婚後,前妻頂級豪門身份曝光
【爽文 追妻火葬場 虐渣 萌寶 雙潔】 協議到期,慕冉甩下離婚協議瀟灑跑路。 誰知,剛離婚就不小心跟前夫哥擦槍走火。 轉眼前妻露出絕美容顏,馬甲掉不停。 鋼琴大師,金牌編劇,知名集團幕後老板……更是頂級豪門真千金,多重身份驚豔全球。 前夫哥纏上身,捏著慕冉下巴威脅:“你敢動肚子裏的寶寶,我打斷你的腿!” 然而白月光出現,他一張機票將懷有身孕的她送走。 飛機失事的新聞和真相同時傳來。 “戰總,夫人才是您找尋多年的白月光!” 戰景承徹底慌了。 再相遇,他卑微如泥自帶鍵盤跪在慕冉麵前,“老婆,我錯了!跟我回家複婚好不好?” 慕冉幹脆拒絕:“想複婚?不好意思,你不配!” 男人死皮賴臉,“孩子不能沒有爸爸。” 慕冉指了指身後大把的追求者,“這些都是我孩子爸爸的候選人,你連號都排不上。” 最後,戰景承站在臥室門口眼尾泛紅:“老婆,今晚能不能別讓我睡書房了?” “我要哄娃,別來沾邊!” “我也需要老婆哄睡。” 慕冉一個枕頭扔過去,“不要臉,滾!” 戰景承強勢擠進慕冉懷裏,化身粘人精,“要滾也是和老婆一起滾
23.7萬字8 68589 -
完結17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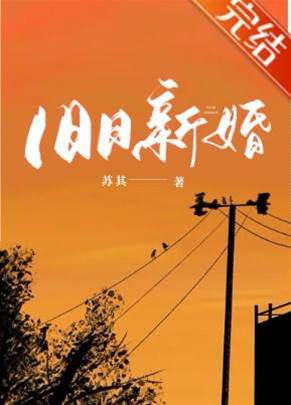
限定婚約/舊日新婚
秦南山是聞依最不喜歡的男人類型之一,刻板嚴肅,沒有喜好,沒有激情,像密林深處一潭死水,石頭扔進去,波瀾不驚。 一夜混亂,聞依更新認知,不全無可取之處。 一個月後,聞依看着試紙上兩道鮮明的紅槓,陷入沉思。 從懂事起,她從未想過結婚生子。 - 秦南山二十八歲,A大數學系副教授,完美主義,討厭意外,包括數學公式和人生。 聞依找上門時他一夜沒睡,逼着自己接受這個意外。 領證、辦婚禮、同居,他們被迫進入一段婚姻。 某個冬日深夜,聞依忽然想吃點酸的,換好衣服準備出門。 客廳裏穿着整齊加班的秦南山看向玄關被她踢亂的鞋子,眉心緊擰,耐着性子問:“去哪?” “想吃酸的。” “非吃不可?” “嗯。” 男人垂眸看錶,十二點零七分。 他心底輕嘆一聲,站起來,無奈道:“我去給你買。”
31萬字8.18 19943 -
完結78 章

救命!我家總裁又瘋又粘人
出獄第二天,云初強吻陌生帥大叔,成功脫險。出獄第三天,云初被送到慕家繼承人床上,為妹妹替嫁。 她一覺睡醒,竟成陌生帥大叔未婚妻! “你腿部有疾,還雙目失明?”她視線逐漸往下。 慕澤坐著輪椅,“陪我演,這件事你不準——” “退婚!我不嫁第三條腿不行的男人!” “......” 領證后,慕澤掐住云初的腰肢抵到墻角,不停逼問: “寶寶,滿意嗎?還不夠?” 云初欲哭無淚,“我錯了,大叔,你行你很行...” 兩人一起斗渣男,撕綠茶,破陰謀,一言不合送反派進局子,主打一個爽。 【一部女主出獄后升級打怪的救贖成長文,男主寵妻無下限。】
14.1萬字8 111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