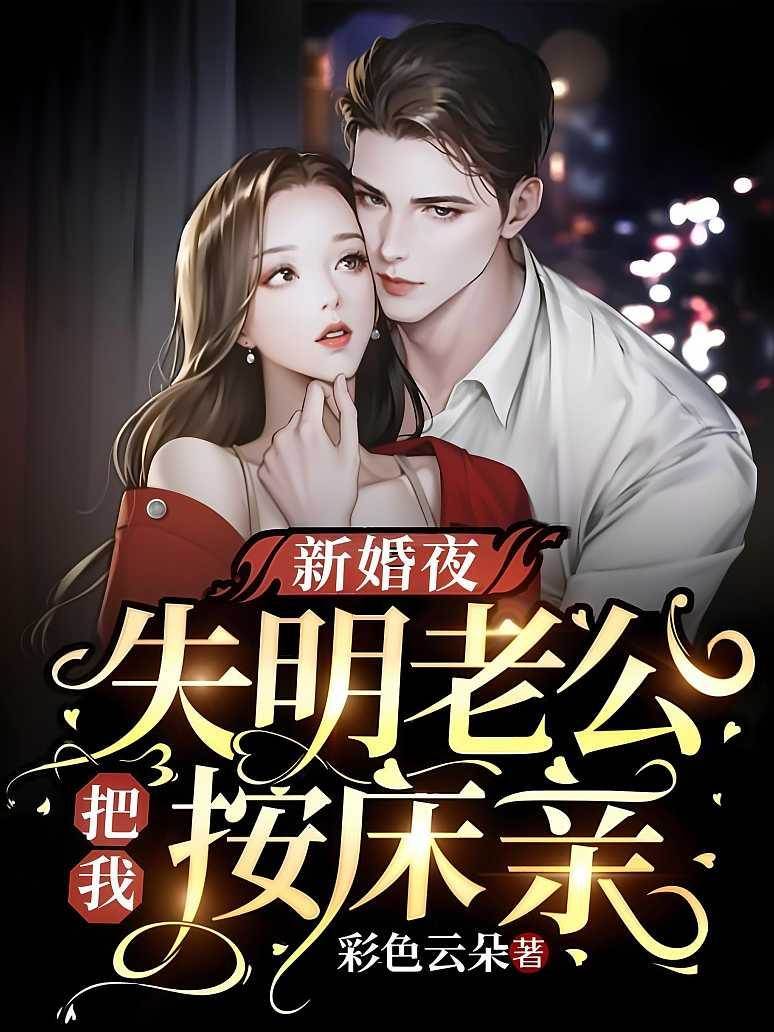《溫小姐獨美后,偏執靳總悔紅了眼》 第1卷 第50章 溫棠,這才是你的真面目吧!
溫棠的目在他臉上緩緩游走,仿佛第一次真正認識這個人一般,曾經讓無數次心、無數次沉醉的面龐。
此刻,每一都充滿了陌生與厭惡。
靳嶼年被這樣的眼神看得心頭一,閃過一不易察覺的慌。
“你到底走不走?”靳嶼年下心底的不安,盯著溫棠。
“憑什麼?”
“憑什麼?”靳嶼年咬著牙,手中用力一扯,直接把人扯到了面前。
靳嶼年以高優勢,俯盯著溫棠的眼睛,一字一句地說著:“就憑現在你踩的是靳家的地盤!”
溫棠別過腦袋悶聲悶氣說道:“這里是嶼城哥家!”
“你——”靳嶼年聞聲,氣得一梗。
靳嶼年手緩緩地落在了溫棠的臉上,用力一!
咬著牙說道:“溫棠,要乖!”
溫棠被迫仰頭與靳嶼年對視,卻死死咬著貝齒一聲不吭。
靳嶼年見溫棠不說話,手指緩緩收,用力地住的臉頰,力度大得幾乎要將臉上的掐出印來。
Advertisement
溫棠痛得倒吸一口涼氣,秀眉蹙,眼眶中迅速凝聚起一層水霧。
隨著靳嶼年力度再次加大,溫棠再也忍不住,用盡全力氣,對著靳嶼年的臉大吼了起來:“靳嶼年,你這個瘋子!”
靳嶼年著溫棠殘忍一笑:“你說的沒錯,我,就是瘋子!”
“你——”
靳嶼年氣急敗壞,雙眼圓睜,額頭上的青筋跳,他猛地近溫棠,聲音低沉而充滿憤怒:“溫棠,這才是你的真面目吧?這兩年的溫與順從,都是你心編織的謊言,用來騙我?”
溫棠迎上他的目,角勾起一抹冷笑,那笑容里滿是冷漠與嘲諷。
用力掙開靳嶼年,眼神中沒有毫留:“是,又怎樣?你以為你是誰,值得我真心相待?這兩年的戲,我演夠了,也看夠了你的自私與虛偽!”說著,轉走。
Advertisement
靳嶼年整個人都瘋了,他猛地向前一撲,幾乎要將溫棠撲倒在地。
雙手如鐵鉗般扣住的肩膀,臉上滿是猙獰與不甘,每一個字都像是從牙中出來的,“溫棠,你休想走!你是我的,永遠都是!”
溫棠目驚恐地著靳嶼年,眼底閃過一抹難以言喻的恐懼,聲音抖著問:“你要做什麼?”
靳嶼年的臉龐在昏暗的燈下顯得格外森,他角勾起一抹令人心悸的冷笑,一步步近溫棠,仿佛一頭被激怒的野。
“你說呢?”靳嶼年手猛地拽住溫棠的手腕,力度大得幾乎要將的骨頭碎,眼神中滿是占有與瘋狂。
溫棠拼命掙扎,卻如同蚍蜉撼樹,的眼中漸漸泛起了淚,恐懼如同寒冰般蔓延至全,每一個細胞都在尖著抗拒。
“靳嶼年,痛!你快松手!”
靳嶼年的眼神鷙如深淵,角勾起一抹令人心悸的笑意:“跟我走。”
“不,不要——”溫棠猛地搖搖頭,膽戰心驚地著眼前瘋狂的靳嶼年。
猜你喜歡
-
完結990 章

女扮男裝出逃后,我被薄爺通緝了
游離是薄爺養在家里的小廢物,打架不行,罵人不會,軟軟慫慫慣會撒嬌。薄爺對游小少爺就兩個要求,一,八點門禁,二,談戀愛可以,但不能越線。薄爺只顧防著女孩子,卻沒想到真正該防的是男人。游離——懷孕了!薄爺承認自己瞎了眼,這些年,竟沒看出游離女扮男裝。那日,聯盟直播間里千萬人在線,薄爺沉臉誤入。“游離,你肚子里的孩子是哪個狗男人的?我非扒了他的皮。”眾人皆驚,他們的老大竟然是女的?電競同盟:“老大,別玩游戲,安心養胎。”賽車基地:“多生幾個,別浪費了老大的好基因。”黑客組織:“把我們老大睡了的男人,...
166.1萬字8 38654 -
完結74 章

失控
向嘉事業受挫回鄉靜養,陰差陽錯事業開了第二春,還養了個天菜男友。事業漸入佳境,平步青云,她要回到曾經所在的富貴圈了。離開的前一晚,向嘉點了一支事后煙,跟林清和道
29.7萬字8 18957 -
完結13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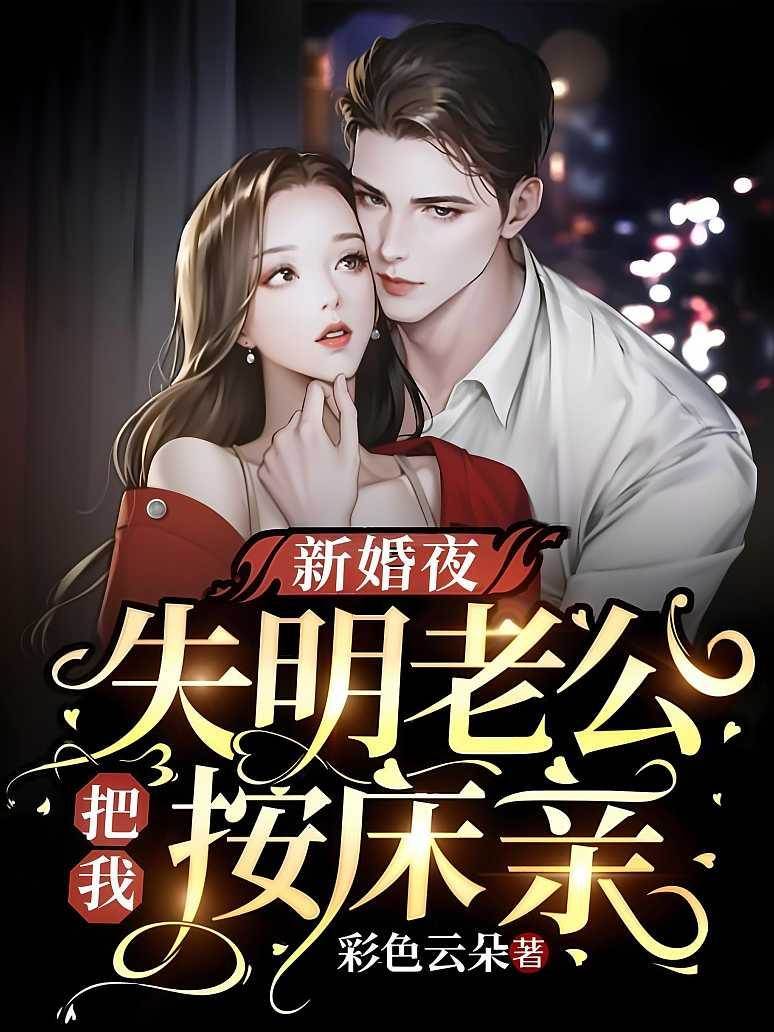
新婚夜,失明老公把我按床親
鄉下的她剛被接回來,就被繼母威脅替嫁。 替嫁對象還是一個瞎了眼的廢材?! 村姑配瞎子,兩人成了豪門眾人笑柄。 她沒想到,那個眼瞎廢材老公不僅不瞎,還是個行走的提款機。 她前腳剛搞垮娘家,后腳婆家也跟著倒閉了,連小馬甲也被扒了精光。 她被霸總老公抵在墻上,“夫人,你還有什麼秘密是我不知道的?” 她搖了搖頭,“沒了,真的沒了!” 隨即老公柔弱的倒在她懷中,“夫人,公司倒閉了,求包養!” 她:“……”
24.7萬字8 144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