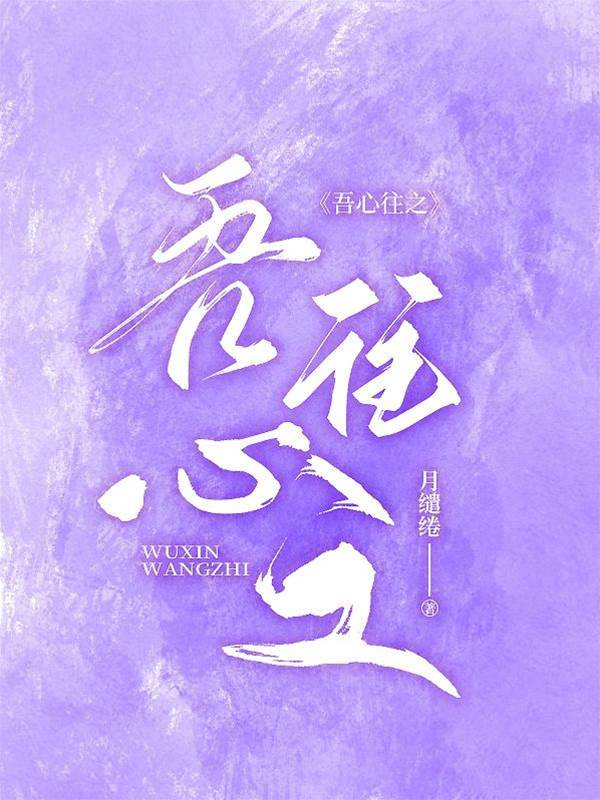《陷入溫柔暮色里》 第1卷 第195章 宴會
帝都
比賽回來后,舒將那枚獎牌送給了裴祁安,他接過的那一刻,舒好像看到了小時候看到爸爸回家時,將那枚泛著的獎牌當禮送給媽媽,直到男人親在的上,才回神,兩人相視一笑。
*
夜幽深,月穿黑暗,將一切都染銀,如詩如畫,令人心。
一輛加長的林肯停在別墅門口,男人高大的影站在門口,看清楚來朝他緩緩駛過來的車,提步向前。
待車停穩后,裴祁安紳士的打開車門,微微彎腰,將手了進去。
一只纖細白皙的手搭了上來,舒一席銀晚禮服,妝容比以往的任何一次都驚艷,冷艷又不失,頭發挽起來,耳邊垂下一小縷,一只小巧的手包抓在掌心。
站穩后,將手輕輕搭在男人的臂彎,小聲詢問道,“來晚了嗎?”
晚上原是計算好了時間,卻不想路上有點堵車,本想簡單裝造,直接赴宴,但是化妝師益求,所以現在才到。
Advertisement
“剛好。”男人低嗓音。
裴祁安幫理了理長,將臂彎的手拿下來,“我幫你提著子。”
帶著場。
宴會廳里籌錯,以高貴典雅的金為主調,大廳中間的水晶吊燈如同鉆石般閃耀,將整個大廳照的彩奪目。
見到門口的響,所有人都安靜下來,目凝在一。
門口有一排玫瑰花一直到大廳中央,像是一條小路。
舒愣了一下,這樣心布置地宴會,是求婚嗎?
張了張,還沒問出聲,大廳地燈突然暗下來。
“祁安?”邊的男人沒了聲響,舒手,卻只抓了一把空氣。
突然,門口的玫瑰花圍的小路突然亮起來,花路的盡頭,“啪”地一聲,天花板上打下來一束,而里是拿著小提琴的裴祁安。
所有的都凝聚在男人的上,隨著燈亮起得那一刻,流暢的旋律從他指間流淌出來,宴會里仿佛醉在里面。
Advertisement
舒聽出來了,是那首《的致意》,愣愣的看著站在里的男人。
曲子很快就拉完了,場上響起來雷鳴般的掌聲。
男人朝很手,舒還沒反應過來就走進了那條玫瑰花圍起來的小路,每走一步,玫瑰里面放得燈束就亮起來一支,一直走到他面前。
直到男人在手背紳士的落下一吻,舒才回神,沒等問出來。
底下寧然的聲音就響了起來,“親一個。”
大家也被帶,紛紛喊道,“親一個。”
“親一個。”
“親一個。”
男人眼底溫,握著的手,“可以嗎?”
舒還是懵懵的狀態,卻還是仰起臉,男人單手著的下吻了上去。
這一刻,燈璀璨,如同萬頃星傾瀉下來。
兩個人相的那一刻,大廳中央的燈亮了起來,整個宴會廳再次被照亮,接著,輕的音樂響了起來。
裴祁安這才放開,舒余瞥到什麼,猛地瞪大了雙眼,愣愣的朝他背后看去。
猜你喜歡
-
完結1250 章
強勢纏愛:總裁,你好棒(林語嫣 冷爵梟)
結婚一年,老公寧可找小三也不願碰她。理由竟是報復她,誰讓她拒絕婚前性行為!盛怒之下,她花五百萬找了男公關,一夜纏綿,卻怎麼也甩不掉了!他日再見,男公關搖身一變成了她的頂頭上司…一邊是拿床照做要挾的總裁上司,一邊是滿心求復合的難纏前夫,還有每次碰到她一身狼狽的高富帥,究竟誰纔是她的此生良人……
264萬字8 56104 -
完結1446 章

借住後,小黏人精被傅二爺寵翻了
傅二爺朋友家的“小孩兒”要來家借住壹段時間,冷漠無情的傅二爺煩躁的吩咐傭人去處理。 壹天後,所謂的“小孩兒”看著客房中的寶寶公主床、安撫奶嘴、小豬佩奇貼畫和玩偶等陷入沈思。 傅二爺盯著面前這壹米六五、要啥有啥的“小孩兒”,也陷入了沈思。 幾年後,傅家幾個小豆丁壹起跟小朋友吹牛:我爸爸可愛我了呢,我爸爸還是個老光棍的時候,就給我准備好了寶寶床、安撫奶嘴、紙尿褲和奶酪棒呢! 小朋友們:妳們確定嗎?我們聽說的版本明明是妳爸拿妳媽當娃娃養哎。 小豆丁:裝x失敗……
261.7萬字8.18 126691 -
完結596 章

新婚夜植物人老公親哭我
她愛上霍時深的時候,霍時深說我們離婚吧。后來,顧南嬌死心了。霍時深卻說:“可不可以不離婚?”顧南嬌發現懷孕那天,他的白月光回來了。霍時深將離婚協議書擺在她面前說:“嬌嬌,我不能拋棄她。”再后來,顧南嬌死于湍急的河水中,連尸骨都撈不到。霍時深在婚禮上拋下白月光,在前妻的宅子里守了她七天七夜。傳聞霍時深瘋了。直到某一天,溫婉美麗的前妻拍了拍他的背,“嗨!霍總,好久不見。”
105.6萬字7.77 95117 -
完結12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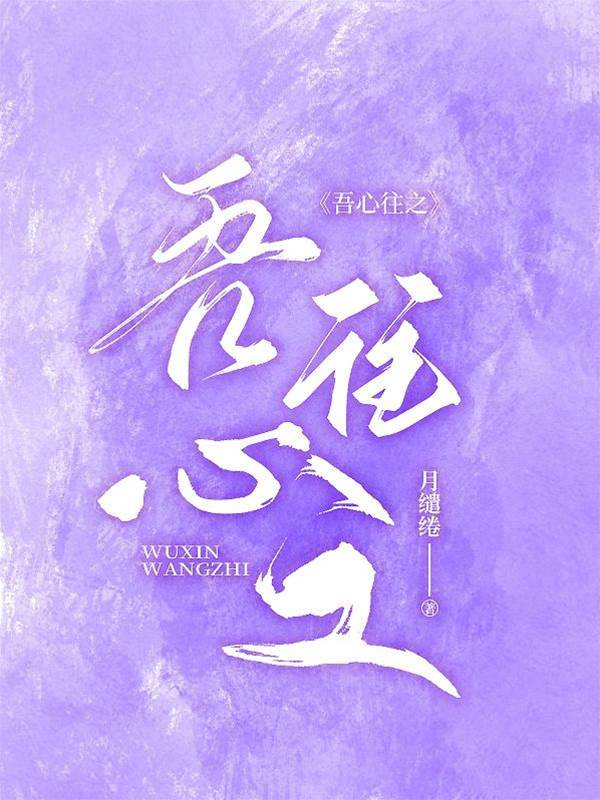
吾心往之
【久別重逢,破鏡重圓,嘴硬心軟,有甜有虐he 】【獨立敏感的高冷美人??死心塌地口是心非的男人】【廣告公司創意總監??京圈權貴、商界霸總】——————阮想再次見到周景維的時候,那一天剛好是燕城的初雪。她抱著朋友的孩子與他在電梯間不期而遇。周景維見她懷裏的混血女孩兒和旁邊的外國男人,一言不發。走出電梯關閉的那一刻,她聽見他對旁邊的人說,眼不見為淨。——————春節,倫敦。阮想抱著兒子阮叢安看中華姓氏展。兒子指著她身後懸掛的字問:媽媽,那是什麼字?阮想沉默後回答:周,周而複始的周。
22.3萬字8 3350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