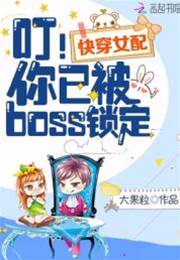《誘她入懷,聞少放肆寵》 第1卷 第98章 你最好祈禱她平安回來
常燈不知道自己被帶到哪里。
雙眼被遮擋,手被束縛,就連腳上也套了鐐銬。
這個屋子安靜過頭,約能聽見海浪拍岸的聲音。
是海邊嗎。
心里琢磨著,知道綁的這些人已經不是阮惠帶來的人了,昨晚被阮惠帶走,路上遭遇車禍,接著,另一撥人就趁劫走了,把困在這里。
整整一夜,彈不得。
額頭上磕出道口子,有跡滲出,后來不流了,應該已經干涸。
輕蹙眉,覺得事變得棘手。
如果只是在阮惠手里,起碼暫時安全,可以利用配型這段時間做掩護,將戰線拉長,等到聞柏崇發現來救,就算沒找到,也能找機會溜走。畢竟,在配型結果出來前,阮惠不會。
但是現在,一切都說不準了。
連這是什麼地方都不清楚,被看守得死死的,更別提逃走。況且二次綁架,中間隔了阮惠,聞柏崇即使發現了,調查起來也麻煩。
綁的人不知名姓、不知意圖,一切都是未知數,無端增加了難度。
常燈蜷在破草堆上,只覺得額頭一陣陣發疼,嗓子干得快冒煙,只好忍著痛喊:“有沒有人。”
“我要喝水。”
“你們總得給點水吧。”
皺眉,房間里回著自己的聲音,沒有其他靜。
哐的一聲,門被打開。
腳步聲停在邊,接著一個礦泉水瓶堵在邊,來人毫沒客氣,半豎著瓶子灌。
常燈被嗆得咳嗽,水大半灑在領里,涼得皺眉。
“真他爹的磨嘰。”是個嗓音狂的男人,嗤笑道,“還喝嗎?”
常燈察覺到危險,默默了腳,往后挪。
“膽子真小。”男人跟同伴調侃,“費這麼大勁干什麼?還以為是個不好惹的,沒想到是個綿羊羔子。”
Advertisement
“六子。”另一道聲音揷進來,音冷漠多了,裹著一警告意味,“別惹事。”
“嘖,就你正經。”被喚作六子的男人拍了拍常燈的小,看猛回去,破口大笑,“到這鬼地方,不找點樂子怎麼行。”
“不想找死就老實點。”同伴警告。
六子冷哼一聲,著掉在地上的瓶子扔到一邊。
房間又恢復平靜,但常燈知道他們沒走,邊有呼吸聲,還有六子偶爾臭罵的呵斥。
這個姿勢維持了一整夜,和腰都僵極了,稍微一就疼得厲害,咬牙忍下,躊躇了很久,才試探著問:“為什麼抓我?”
沒人理。
但知道,兩人都還在。
又問:“總得給個理由吧?抓我干什麼?誰讓你們來的?”
“呦,還冷靜。”六子先開口說話,“別的人被綁架,要麼哭天喊地,要麼就是一副默默掉眼淚的可憐樣,你倒是不怕,還敢問東問西。”
常燈抿了抿,沒吱聲。
六子調侃一句,似乎沒將人放在心上,又忙活自己的事。
常燈沒再問他,循著聲音將腦袋轉到另一邊:“為什麼綁我?”
另一個人沒說話,六子首先不耐煩了,冷笑:“我說你這人怎麼這麼啰嗦?”
常燈輕聲回:“我只是想死得明白一點。”
“呵,還有自知之明。”六子來了興趣,“你說說,為什麼覺得自己會死?我們看起來像殺人犯?”
“我沒看到樣貌,不好評價。”常燈掐了掐掌心,心里砰砰直跳。
“別耍小聰明。”六子斂了笑,“老實待著。”
他們比想象中更謹慎。
常燈繃著的弦斷了,知道套不出話來,也不再做無用功,仰靠在草堆上,保存力。
*
醫院。
聞柏崇著那枚戒指出神,眸底冰冷刺骨,面前站著幾道影,最中間是位士,額頭綁了繃帶,盯著男人手邊病床上的男孩,垂泫泣。
Advertisement
“常燈要是有任何意外,你和你兒子就給陪葬。”聞柏崇手上韓棕的側臉,指尖的涼意渡到男孩皮上,驚得他哭出聲。
阮惠心揪著,不敢剛,只得小心安:“我真沒想傷害小燈,誰知道半路被人劫走,不關我的事啊,你別我兒子。”
“不關你事?”男人臉冷,“你最好祈禱平安回來,不然,我一定要你們生不如死。”
“程木。”聞柏崇喊人。
程木心領神會,示意保鏢將阮惠扔出去,人撕心裂肺的哀嚎在走廊回著,苦于被阻攔,無法近,只能在病房外威脅。
“我告訴你,你敢我兒子試試,別以為聞家在泉城一手遮天,韓家也不是吃素的!”
程木見自家老板臉越來越郁,及時開門示意保鏢將人扔得更遠些,轉時,被冷臉老板住,他說:“全城搜,加大力度,繼續加人,讓沈祁川和秦時夜那邊也仔細點。”
常燈已經消失了一夜,事發路段是監控死角。
呵,還真是心積慮。
聞柏崇指尖著戒指,凌冽的目從最上面那顆鉆石上掠過,無形中蘊藏著風暴。
這是昨晚在商場找到的,除了這個,常燈沒留下任何東西,消失了一整晚,也不知道沒傷,冷不冷,綁的人給不給飯吃。
本來就是個膽小鬼,這下估計要嚇哭了。
想到這,聞柏崇掌心收,額角青筋跳了又跳,閉眼下腔里的郁氣。
程木聽完保鏢的匯報,對聞柏崇耳語幾句。
“他簡直找死。”聞柏崇低斥。
下一刻,男人凜眉,闊步往門外走,程木吩咐人看好病房,跟上自家老板。
聞氏集團的門廳被暴力拆開,前臺工作人員被嚇得不輕,剛想撥打線,就被人摁在工位上,健壯保鏢一左一右摁著的肩膀。
Advertisement
領頭的那位年輕男人,認識。
是聞家的小爺,說起來,還是們老板的小兒子。
但對方這尋仇的架勢著實不容小覷。
小前臺瑟瑟發抖,嚇得說不出話來。
拆家似的靜還沒停止,大廳玻璃被敲碎,沙發擺設被砸毀,一群材魁梧的漢子像來報復的黑社會,悶頭苦干。
一片混中,面容冷峻的男人只斜靠在前臺桌子前,薄繃一道直線,眸犀利戾,裹著十足的殘暴氣息。
他指節曲起,敲了敲桌面,低沉的聲音在此時宛如魔鬼的詛咒,他說:“讓何澤朗滾下來。”
猜你喜歡
-
完結574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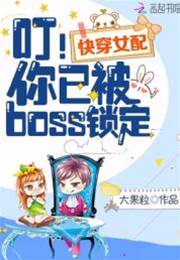
快穿女配之你已被boss鎖定
阮綿綿隻想安安分分地做個女配。 她不想逆襲,也不想搶戲,她甘願做一片綠葉,襯托男女主之間的純純愛情! 可是為什麼,總有個男人來攪局?! 阮綿綿瑟瑟發抖:求求你,彆再纏著我了,我隻想做個普通的女配。 男人步步逼近:你在彆人的世界裡是女配,可在我的世界裡,卻是唯一的女主角。 …… (輕鬆可愛的小甜文,1v1,男主都是同一個人)
103萬字7.83 14294 -
完結476 章

億萬首席,萌寶來啦
一紙契約,她淪落代孕工具,生產后當天,便被扔在雨夜里自生自滅。奄奄一息時,林念初握緊拳頭,發誓今后獨立自強,努力賺錢,不再任人欺辱。可是為什麼,那個冷漠男人又纏上了她,還百般寵愛?直到某天……“先生,請你自重!”“你是我兩個孩子的媽,還自重什麼?”男人將她步步緊逼至墻角,并掏出一枚鉆石戒指,深情款款地半跪下來。“寶貝,跟我回家,好嗎?” 男主是謝以深女主是林念初的小說《億萬首席,萌寶來啦》又名《萌寶來襲:媽咪是男神》。
87萬字8 81307 -
完結89 章

久婚必合
舒妤跟傅西辭能結婚,完全是家里的原因。在婚禮之前,兩個人只見過一面,還是車禍現場級別。舒妤跟傅西辭婚后一年,朋友問起她怎麼形容自己的婚后生活。她想了想,說了八個字:“沒有感情,全是技巧。”
28.4萬字8.18 37015 -
完結231 章

閃婚孕吐小嬌妻,禁欲傅總日日親
(年齡差9歲+雙潔+一見鐘情+懷孕閃婚+甜寵+有嘴的矜貴深情霸總*軟糯乖巧羞澀的小白兔)快節奏! —— “你懷孕了,是我的孩子。” 林初低眸,“我其實可以解釋,那晚之后,我吃避孕藥了,只是......” 傅南琛摸了摸她的頭,“初初乖,不用解釋,懷孕是喜事,把寶寶生下來。” 林初瞳孔瞪大。 她竟然在他的表情上看到了欣喜。 “生下來?” 傅南琛十分堅定的再次回答,“嗯,生下來。” “所以,你有很多孩子嗎?” 他干咳幾聲,掩飾尷尬,“咳咳咳,你是我唯一的一個女人。” 唯一一個?他的表現可不像...... “傅先生,我知道你很有錢,但是我還沒有給陌生男人生孩子的打算。” “你管親過睡過的男人叫陌生男人?” 轟—— 這是什麼虎狼之詞? 林初的耳根迅速躥紅,仿佛能滴出血來。 “求你別說了,傅先生。” “那我們熟嗎,初初?” “熟,很熟。” “所以可以給我一個照顧你和寶寶的機會嗎?” “可以。” “不對,不可以......” 【婚后商圈紂王傅總跌下神壇當忠犬】 “初初愛我好不好?” “老婆求你愛愛我。” “老婆,親我好不好?”
37.5萬字8 19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