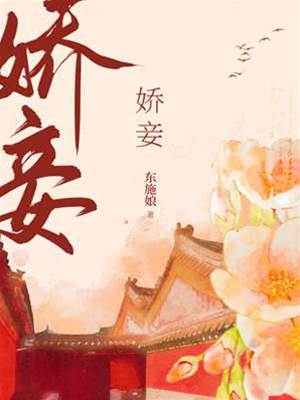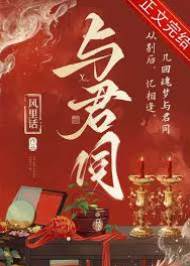《重生在龍塌,寵妃抱著陛下哭》 第1卷 第192章 番外:假如裴琰重生(1)接第一世
裴琰睜開眼,看見了悉的東宮帳頂。
“哎呦,殿下可算醒了。”
耳邊傳來程守忠如釋重負的聲音,他皺了皺眉,這是人死前的幻象嗎?
他分明已經服下鴆酒,在棺中陪伴著姜姝儀了。
“太傅還在文華殿等著,今日要講尚書,可不能遲了,否則有些小人只怕會借機生事,向陛下讒言告狀......”
程守忠絮絮叨叨的聲音逐漸把一切拉的真實,清晰。
裴琰緩坐起,眸定定落在他的臉上。
程守忠被盯的一驚,連忙跪下,有些忐忑不安地問:“殿,殿下,是奴才說錯什麼了嗎?”
一模一樣的神態,可人卻比裴琰印象中年輕了一二十歲。
他環顧周遭,這里顯然是自己在東宮的寢殿,而程守忠說太傅要講尚書。
從十五歲后,裴琰就開始在父皇的授意下涉及朝政,不再去文華殿聽講了。
他冷聲問:“程守忠,你多大年歲了。”
程守忠雖不知殿下怎麼忽然關懷起他的年紀,但還是連忙回答:“奴才十八了。”
十八。
那就是嘉和二十六年,自己將將十五歲,初被立為太子。
難道果真如那老道士所說,他是天上神君,因為沒有繼續造殺孽,所以有了重頭來過,和姜姝儀再續前緣的機會?
裴琰閉了閉眼,幾乎是立刻想去姜府,可十五歲的自己還有許多掣肘,只能勉強按捺住子,先去文華殿聽講。
散課后,裴琰去乾清宮求見父皇。
嘉和帝坐在案后,待他進來,便招手喚道:“太子過來,看看這封奏。”
裴琰恭敬應“是”。
那是一封揭發大皇兄私自豢養暗衛的奏。
這自然是大罪,可哪個奪嫡的皇子暗地里都有培植。
“太子之意,該如何置?”
上輩子也有此一問。
Advertisement
裴琰那時為了維持溫和謙仁的形象,為大皇兄求了,希父皇從輕置。
父皇未置可否,只笑著“嗯”了聲,讓他退下,事后也確實沒有置大皇兄。
裴琰一直以為父皇對這個回答是滿意的,直到父皇死前吐言,裴琰才知,父皇之所以把他立為太子后還屢次試探,在他和大皇兄之間猶疑,就是不喜他太過仁懦。
外有強將,有權相,朝廷上下還滿是貪蠹,這個局面如何是一個寬仁守之君能鎮下來的?
在沉片刻后,裴琰著父皇,一字一頓道:“當殺。”
嘉和帝的眸微亮了一下,似是意外之喜。
但他臉上卻不見喜,甚至更為嚴沉:“太子這是要殘殺手足嗎?”
換做前世,裴琰即便知道父皇不喜他過于仁懦,也會慢慢更改,不會頃刻間轉變的如此之快,畢竟太過野心,可能也會招惹父皇忌憚。
但如今他等不了那麼久了。
裴琰一叩到地,聲線平穩:“若父皇喚兒臣琰兒,兒臣會求父皇從輕置大皇兄,可父皇喚的是太子,為儲君,便當摒棄私,只要是為家國計,天下之人盡可誅殺。”
即便沒有抬頭,裴琰也能覺到父皇那道審視的目在自己上逡巡。
良久,在程守忠嚇得快溺了時,臉冷沉的嘉和帝忽短促的笑了聲。
“看來朕還真是選了一位好儲君。”
裴琰聽出父皇沒有怒的意思。
但同時,父皇冷靜下來后也沒有覺得多欣喜。
他明白父皇對自己最大的顧慮在哪里。
裴琰沒有起,而是懇請:“求父皇屏退左右,兒臣有話稟告。”
嘉和帝覺得今日的太子有些異樣。
他在太子上掃視了個來回,確認沒有利,才下令宮人退到門外去。
Advertisement
“太子有什麼話?”
裴琰直起,進父皇那雙銳利如鷹的眼里,低聲沉道:“父皇,溫寰功大欺君,兒臣除之。”
嘉和帝整個人猛地一震。
“你?”
他顯然是不信,神狐疑又震驚。
一則裴琰初為儲君,勢力微弱,本不可能功,二則裴琰的儲君之位都是溫寰著他立下的,兩人本是同黨,又怎麼可能反目?
但無疑,除掉溫寰這個連他寵幸誰都要管的強將,對嘉和帝來說是一件無比有吸引力的事。
裴琰眼中滿是認真和決絕:“父皇有所不知,溫寰曾在不日前潛東宮,暗示勒令兒臣娶他的次為太子妃,否則便要向父皇進言,廢除兒臣的太子之位,選應允的皇子立為太子。”
這簡直是把自己當皇帝了,立誰是太子難道是他說了算的?
可偏偏還真的是。
嘉和帝氣的郁悶,但面上不顯,仍是死死地盯著裴琰:“這對你而言不是好事嗎,太子是否已經應允了?”
裴琰搖頭:“兒臣沒有如此糊涂,若果真如此,那麼太子妃以后誕下的孩子,定然會被溫寰扶持為下一任儲君,屆時溫寰再以國丈的份輔政,架空兒臣,等到水到渠之日,便是我大淵江山萬劫不復之時。”
嘉和帝郁氣稍緩。
還好,這個太子還不算愚昧。
“太子說得容易,西闐虎視眈眈,朕若置了溫寰,再起戰時,誰去領兵抵抗呢。”
嘉和帝不是沒想過收攏溫寰手上的兵權,可西闐難纏,那邊的仗只有溫寰去才能打贏,旁人領兵總是一敗涂地。
裴琰聲音溫和,卻一語中的:“勝敗乃兵家常事,可溫將軍屢戰屢勝,旁人屢戰屢敗,父皇便不曾疑心嗎?”
嘉和帝也并非是個糊涂的君主,自然知道里面有些關竅。
Advertisement
可裴琰小小年紀能看出來,著實讓他吃驚。
他好整以暇地看著裴琰,態度和緩了不。
“就算是溫寰里通外敵,養寇自重,太子又有什麼辦法呢,”
裴琰仰起頭:“不只是養寇自重,西闐并不難攻打,難在西北的士兵吃著朝廷的俸祿,私下卻自稱溫家軍,旁人率領,他們奉違不肯奉令,如此這般,哪個將軍去都打不了勝仗,父皇若要除,便當不吝一時之得失,先斬殺溫寰,涼州必定會大,西闐貪得無厭,免不了趁機而,和溫家在涼州的駐軍反目,互相爭奪涼州,父皇只需坐山觀虎斗,無論勝出的是哪方,都損耗了一定的兵力,到那時,朝廷的大軍再悄然境,奪回涼州,父皇定會名垂青史。”
猜你喜歡
-
完結9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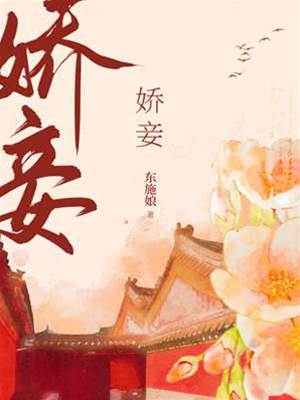
嬌妾
她生來命賤,覺得能成為駙馬爺的小妾,衣食無憂,還有人伺候,已經是她命最好的時候,哪知道那個不茍言笑的主母說她偷了人,叫人把她活活打死了。 死了的芝芝當了三年阿飄,整天飄來飄去,無所事事,所以發現她那位美貌的主母一個大秘密。 原來她的主母是個男人,后面還當了皇帝! 芝芝:??? 然后她重生了,重生回她十五歲,還沒有被一抬軟轎從側門抬進公主府的時候。 又軟又慫的女主角,大開殺戒的畫面是沒有的,但又軟又慫人生也是可能逆襲的。
25.9萬字8.63 38594 -
完結144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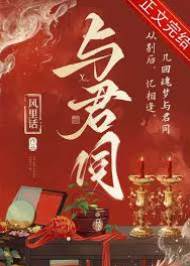
與君同
朔康五年,齊皇室式微,諸侯四起。 爲籠絡權傾朝野的大司空藺稷,天子接回遠在封地的胞姐隋棠長公主,賜婚下降。 大婚當日,隋棠獨守空房。 直到七日後,月上中天時分才迎來新郎。卻被他一把捏起下顎,將藏於牙中的毒藥摳了出來。 彼時隋棠因在婚儀路上被撞,雙目暫且失明,正惶惶不安時,昏暗中卻聞男人道,“今日天色已晚,先歇下吧。” 這夜隋棠做了個夢。 夢中她看見自己,難產誕下一子,後不到兩炷香的時辰,便毒發身死。 死前一刻,她抓着藺稷的手,平靜道,“不必喚醫官,不必累旁人,無人害孤。是皇弟,曾讓太醫令鑿空了孤半顆牙齒,在你我二人大婚之日將一枚毒藥埋入其間,用來毒死你。” “非孤仁心下不了手,實乃天要留你。送親儀仗在銅駝大街爲賊人驚馬,孤被撞於轎輦瘀血堵腦,致雙目失明,至今難尋機會。所以,司空府數年,原都無人害孤,是孤自備之毒,漸入五臟。” “大齊氣數盡,孤認輸,君自取之。” 她緩了緩,似還有話要說,譬如她幫扶的皇弟,她家搖搖欲墜的江山,她才生下的孩子……然到底再未吐出一個字。 所有念想化作一聲嘆息,來生不要再見了。 隋棠在大汗淋漓中醒來,捂着餘痛未止的牙口,百感交集。不知該爲毒藥被除去而慶幸,還是該爲毒藥被發現而害怕…… 卻覺身後一隻寬厚手掌撫上自己背脊。 男人嗓音暗啞,“別怕,臣明日便傳醫官來府中,給殿下治眼睛!” * 藺稷攏緊榻上人,他記得前世。 前世,隋棠死後,他收拾她遺物。 被常年監控的長公主寢屋中,幾乎沒有完全屬於她自己的東西。他整理了很久,纔在一方妝奩最底處,尋到一份她的手書。 久病的盲眼婦人,筆跡歪扭凌亂。 此生三恨: 一恨生如浮萍,半世飄零久; 二恨手足聚首,卻做了他手中棋; 三恨雙目失明,從未見過我郎君。 世人道,藺氏三郎,霸道專權,欺主竊國。 但他是第一個待我好的人,我想看一看他。 #從別後,憶相逢,幾回魂夢與君同#
37萬字8 126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