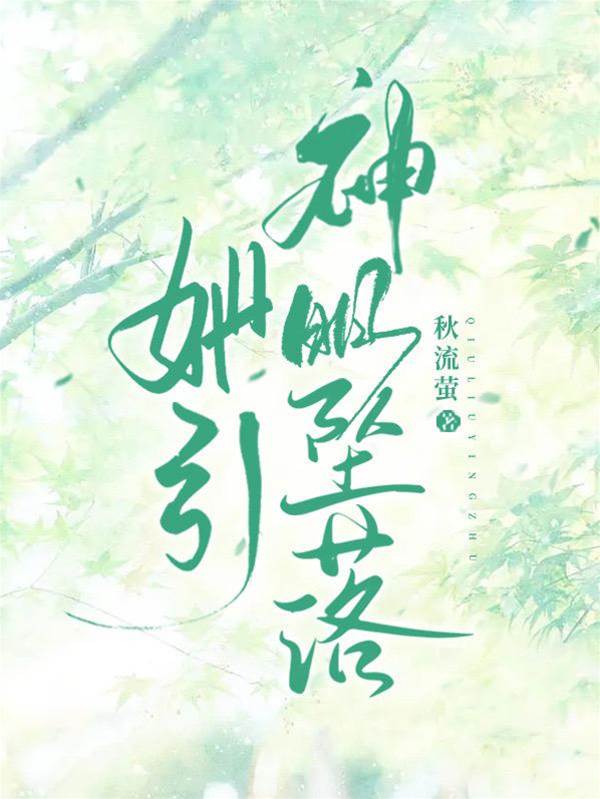《暗燒》 第 89 章
店員見生意來了, 也顧不上吃狗糧,臉上堆滿笑容向他們推銷。
南夏不想那麽容易被溫聿秋吊住,故意說:“二婚買什麽戒指。”
店員:“……?”
溫聿秋:“……?”
出來時溫聿秋開車, 看上去似乎并不計較這件事,還同打趣:“我怎麽不知道你還有個前夫?”
南夏說了個家喻戶曉的明星名字, 說你來晚了, 我小時候就把自己許配給他了。
溫聿秋見過那位明星,甚至知道他的一些私事兒。娛樂圈是個大染缸,大多只是表面鮮罷了。
只是為了不打破友的幻想, 溫聿秋沒有說話。
事後再想,他總覺得哪兒不對,怎麽就默認那位“前夫”的存在了。
溫聿秋沒說話, 手臂隨地搭在方向盤上, 南夏看向前方的車輛,過了會兒又悄悄地看他,觀察他有沒有生氣。
畢竟從上次他吃醋的那件事就可以看出來,某人是真的小心眼。
下車前,南夏說安全帶卡住了,要他過來幫忙。溫聿秋未曾察覺出什麽, 側過按開安全帶的卡扣。
溫聿秋正疑安全帶沒什麽問題時, 上落下輕的吻, 瓣分開時,男人才反應過來, 手扣在腦後加深了這個吻。
末了他才問做什麽。
“哄這個世界最小氣的人。”
溫聿秋笑了笑, 發現自己在心裏的形象總算是徹底毀了, 他再小氣也不可能因為一句玩笑話吃一個算得上是虛擬人的醋。
心裏這樣想,溫聿秋卻著的腰, 不輕不重地說:“這樣就夠了嗎,我莫名了你二婚對象。”
南夏也沒想到他這樣難哄,回憶了一下渣男語錄:“你要這麽想我也沒辦法。”
溫聿秋能說什麽。
他眼底泛著輕浮,笑著問怎麽好的不學專門學壞的。南夏說是跟他學的,畢竟他是見過最壞的人。
Advertisement
“我怎麽對你壞了?”
從他的眼裏窺出輕佻的意味,發覺他在耍流氓,認真地說:“就比如現在扣著我不放,完全不管我是不是了。”
溫聿秋拿沒辦法,松開了放在腰上的手。
重新在一起久了,同居是理所當然的事兒。溫聿秋和南夏搬到了一塊兒,之前也不是沒有同居過,只是這次比較新鮮,竟然開始學著做飯。
他到廚房的時候就看見南夏圍著圍,聽著紀士的教導一步步作。
但是不得不承認這個世界上做任何事兒都是需要一定天賦的,就這樣認真做出來的東西仍舊看上去像是在投毒。
溫聿秋垂眸看了眼,覺得自己太有些疼。等掛了電話,他問怎麽好好地要學做飯。
“你以為我想嗎?我媽一直跟我念叨,我這不是想應付一下嗎?”南夏說紀士也是覺得不能一直指溫聿秋,總是要獨立一點兒的。
別看紀士之前對溫聿秋不滿意,這會兒接了人家之後又怕什麽都不會,兩個人過得不長久。
南夏實在是不想聽嘮叨,這才勉強應付一下。
記得前幾年有個自我催眠,孩子犯錯了告訴自己是親生的。這會兒也告訴自己,親生的,親生的。
算了,紀士年紀大了順著點兒,也不是什麽原則的問題。
溫聿秋出纖長的手指解開上的圍,將人帶到沙發上坐下:“等我會兒。”
他走到臺上給紀士打了個電話。
南夏不知道他要做什麽,湊過去聽見他說:“您別為難我了,這要是吃了做的東西得進醫院。”
南夏:“……”這人怎麽這麽過分呢。
心裏盤算著待會兒要怎麽跟他算賬,溫聿秋手搭在欄桿上“嗯”了一聲:“您放心,今後有我照顧,不需要樣樣都會。我既然喜歡自然接的全部。”
Advertisement
南夏怔了怔,聽著他悅耳的嗓音耳廓不住地發,他又說:“請您放心把托付給我,我會履行好這份責任……”
解決了這事兒,溫聿秋將電話掛了,腰上突然多了一雙手。
南夏從後抱著他,想到那時遇到父親時,他也不知道說了多話才說服對方。可是卻沒能得到他家人的認可,多心裏是有些憾的。
只是那份憾不是對而言的,是希他能更幸福。
問溫聿秋真的不需要做飯了嗎,其實也可以學習學習,溫聿秋說很喜歡恩將仇報。
“哪兒來的恩?”南夏問。
溫聿秋笑:“平日裏哪兒都喂了,到你就對我投毒,我跟誰說理兒去”
南夏聽出他在耍流氓,松開手掐了一下他的腰。溫聿秋也習慣了,總喜歡跟他使用“暴力”,只是每次都很輕。
有次咬他咬狠了,溫聿秋假裝很疼,又在那兒心疼悔恨半天。
也不知道格怎麽那麽多變。
溫聿秋進廚房收拾幹淨的“犯罪現場”,作幹淨利落。倚在門口的南夏不得不承認學做飯確實是給他創造了麻煩。
看著他這副模樣,不知道為什麽在他上到了幾分“人夫”的氣息。
南夏有些想非非,看他的眼神跟著不太純粹。
“了?”
“嗯”了一聲,小聲說:“你什麽時候能再在這兒一次服?”
溫聿秋笑了,眼尾泛著淡淡的紅,敢的不是上面那張。
他把人抱過來,讓自己,南夏這才認輸:“錯了,我想先吃飯。”
飯確實做了,只不過是黏糊著做的,南夏在後面抱著他讓他沒什麽發揮空間,于是隨意做了一些。
他把餐擺放到桌子上,見這樣黏糊,幫弄好要喂吃。
Advertisement
“溫聿秋,我又不是小孩。”說這話時尾調上揚,倒帶著點兒孩子氣。
讓人無端想到某日他們去游樂場無意間撞見一對父,那個兒也是這樣跟他爸爸說的。
溫聿秋沒收回手,只好吃了一口,然後自己也拿起勺子喂他。
兩人膩歪地對視,南夏忍不住笑出聲:“你覺得這樣吃比較好嗎?我不用你喂。”
溫聿秋想這時候覺得膩歪了,剛剛在廚房裏抱著他的時候又不覺得。
吃了兩口,拿出手機拍了一張自己跟食的圖片發給紀士。
“小溫做的?”
“嗯,做得比你老公好吃。”
紀士沒想到還炫耀上了,不知道的還以為對面這人被盜號了。
好像們很這樣相過,明明是親人卻一直有隔閡。紀士有些慌神,好像跟溫聿秋在一起後,確實開心了很多。
剛好南父湊了過來,剛好撞到槍口上,紀士把東西扔到他懷裏:“你做飯。”
“……”
很快臨城迎來了漫長的梅雨季節,每到這個時候溫聿秋就尤為不適應。別說溫聿秋,有時候南夏也有些不了,下雨一久什麽東西都是噠噠的,還容易發黴。
他想到那時候待在陌生的城市會不會不適應,說京市太幹了,幹得難。
但這時候梅雨季節剛到,還是喜歡雨的,問他想不想出門,溫聿秋不理解下雨天氣為什麽還要出門。
下雨的時候似乎只要不出門一切還都是好的。
南夏知道他不想出去幹脆窩到他懷裏聽雨,雨下得越大,人就越是昏昏睡。
倒是喜歡在家裏這份安靜,只是一個人做得到,兩個人卻做不到。抱著抱著兩個人就有些槍走火,曖昧的聲音和著雨聲,組最聽的調子。
Advertisement
人坐在他懷裏,沒吃得下去,往常會幫的人今天倒是不了,眼底帶著點兒壞:“不是不要我喂嗎?”
這人……記還能更好一點兒嗎?
南夏瞪他一眼,小心翼翼地扶著做下去,眼尾泛起紅,起伏間腰上留下明顯的掌印。
盡興後抱他抱得那樣,夢裏還他的名字。那時候溫聿秋覺得這樣的季節也并不是那麽難以忍了。
那段時間總上工作還是忙,南夏升職溫聿秋事業進展得相對順利,都有自己要做的事兒。
出差後跟溫聿秋的聯系又變了,跟住一起的同事不了解溫聿秋,開玩笑說著他不是時間管理大師吧。
南夏說不是,下次你見過就知道了。
當然了解他,只是那段時間聯系變,也沒空視頻,總讓覺得發生了什麽。
就像是之前溫聿秋不聯系卻一個人躺在醫院裏,孤零零的。如果再發生一次,不知道會心疼什麽樣兒。
擔心他仍舊不聽的話。
南夏也沒問溫聿秋,提前結束了工作回了臨城,如果沒什麽事兒的話,也可以給溫聿秋一個驚喜。
等到溫聿秋公司找人的時候,溫聿秋的助理卻說:“您怎麽在這兒?”
南夏有些不明所以,以為真發生了什麽,問助理怎麽了,助理卻不知道該不該說,吞吞吐吐:“您給溫總打個電話問問吧。”
這態度弄得反而張起來。
電話接通前,都已經準備好要說他兩句了,然而說了自己已經回來之後就聽見那頭有些無奈的笑聲。
“怎麽了?”
“喃喃,我現在在星城。”
張了張,再傻也知道溫聿秋是特意瞞著去了出差的城市去找。
南夏那天給溫聿秋發過定位,所以他知道在哪個酒店,結果來了之後卻撲了個空。
回了臨城,他卻去了星城,兩個人就這樣錯過了。
溫聿秋想到這有些無奈,他原本打算過來陪南夏過生日,花都買好了。
這會兒仍舊豔的花束在他手裏,配它的佳人卻不在,未免有些憾。
只是南夏哪兒能想到玩的這出,這段時間太忙自己都快忘記自己的生日。加上不太重視這些,覺得既然兩個人不在一塊兒生日不需要認真過,之後補也沒什麽大不了。
讓他開視頻,就看見他坐在酒店大堂裏,那矜貴的姿態不知道的還以為什麽領導去視察呢。
一大束海洋之歌放在旁邊的桌子上。
一想到本來溫聿秋是過來陪過生日,結果差錯的兩個人在兩個城市,南夏就有些想笑。
有些憾,笑夠了以後不知道想到了什麽,又有些溫地隔著屏幕看他。
溫聿秋起,拿著那束花準備臨時趕回來,大概是值出衆的原因,旁邊的路人忍不住看他。
南夏說:“我知道你想回來陪我過生日,但是跑來跑去不累嗎?你先找個酒店休息。”
“在家等著我。”他臉上的表很淡,顯然不在意這樣的小事兒。
可是南夏卻知道旅途的勞累的,即便是坐車什麽都不做也會覺得疲憊。
“溫聿秋,你不在我邊也沒關系。”
他不會知道,此刻的心裏裝滿了他給的,比任何時候都要滿。
溫聿秋指尖頓了頓,聽到這話難免有些不滿,只是表面不顯,話裏還帶了點兒笑意:“怎麽,這麽快就不需要我了?”
“不是不需要,是你一直在我心裏。”南夏忍不住笑,因為說了這樣的話讓覺得煽,即便這樣還是忍不住說他,“笨蛋。”
“……”他學生時代永遠是斷層的年級第一,這會兒倒是被人罵是笨蛋了。
“你找個酒店休息,明天生日打電話陪我。”
南夏說完,溫聿秋自然是沒準備聽的,他站在人之中,剛準備過馬路的時候聽見著嗓音說:“阿聿,好不好?”
只是簡單的一句話,讓他的心輕易就了。
南夏以前在家很過生日,的生日和南昔的很近,兩個人總是一起過,最後不知道怎麽回事兒總會變南昔的慶祝日。
因為是姐姐,需要承擔更多責任,需要更加地獨立,可是從來沒有說過也害怕孤獨,也想做個不懂事的小孩兒。
有時候別人不知道心口的裂痕,甚至自己也是麻木的。
直到今日那塊隙被填滿。
兩個人隔著電話久久未言語。
溫聿秋抱著那束鮮花站在十字路口,頎長的形惹人注目。他的眼前是車水馬龍,有那麽一瞬間他幾乎要淹沒在人中,失去與世界的連接。
直到他重新聽到電話那頭人的聲音。
說——
“溫聿秋,無論你在或不在,你已經是我收到的最好的禮。”
猜你喜歡
-
完結1091 章

失憶后我成了法醫大佬
十三年前全家慘遭滅門,蘇槿患上怪病,懼光、恐男癥,皮膚慘白近乎透明,她成了「吸血鬼」,選擇在深夜工作,與屍體為伴;他背景神秘,是現實版神探夏洛克,刑偵界之星,外形豐神俊朗,愛慕者無數,卻不近女色。第一次見面,他碰了她,女人當場窒息暈厥,揚言要把他送上解剖臺。第二次碰面,她手拿解剖刀對著他,看他的眼神像看一具屍體。一個只對屍體感興趣,一個只對查案情有獨鍾,直到未來的某天——單宸勛:你喜歡屍體,我可以每天躺在解剖臺任你處置。蘇槿:我對「活的」沒興趣……
196.7萬字8.18 22956 -
完結1233 章
七零年有點甜
何甜甜一直以感恩的心,對待身邊的人。人到中年,卻發現一直生活充滿謊言的騙局里。重回七零年,何甜甜在小銀蛇的幫助下,開始新的人生。換一個角度,原來真相是這樣!這輩子,再也不做睜眼瞎了。這輩子,再也不要錯過辜負真心相待的青梅竹馬了,好好待他,信任他,有一個溫暖的家。******
215.3萬字8 54157 -
完結877 章

失憶后,偏執總裁寵我成癮
生日那天,深愛的丈夫和其他女人共進燭光晚餐,卻給她發來了一紙離婚協議。 原來,三年婚姻卻是一場復仇。 意外發生車禍,夏初薇失去了記憶,再也不是從前了深愛霍雲霆,死活不離婚軟包子了! 霍先生:“夏初薇,別以為裝失憶我就會心軟,這個婚離定了!” 夏初薇:“離婚?好,明天就去,誰不離誰是小狗。”第二天,夏初薇敲開霍雲霆的門。“霍先生,該去離婚了。” 霍先生:“汪!”所有人都知道她愛他至深,但唯有他,他愛她多次病入膏肓。
157.9萬字8 60448 -
完結10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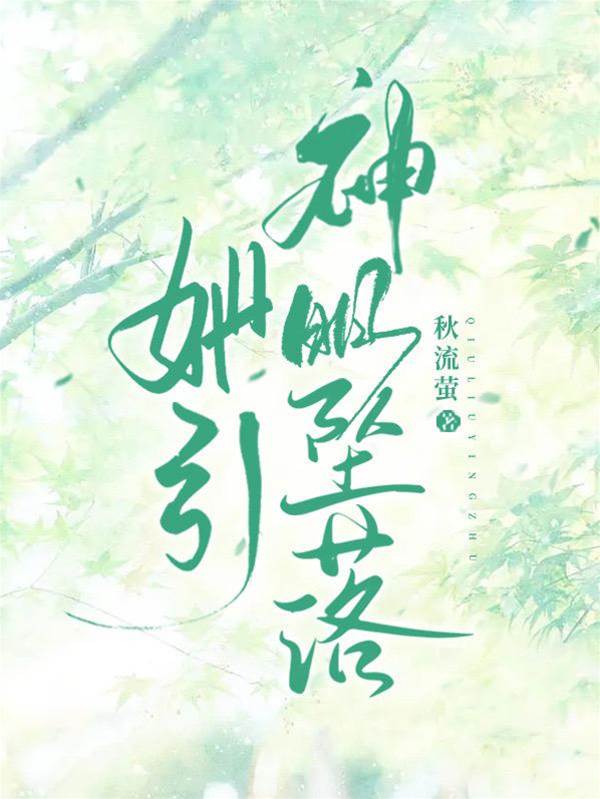
她引神明墜落
沈黛怡出身京北醫學世家,這年,低調的母親生日突然舉辦宴席,各大名門紛紛前來祝福,她喜提相親。相親那天,下著紛飛小雪。年少時曾喜歡過的人就坐在她相親對象隔壁宛若高山白雪,天上神子的男人,一如當年,矜貴脫俗,高不可攀,叫人不敢染指。沈黛怡想起當年纏著他的英勇事蹟,恨不得扭頭就走。“你這些年性情變化挺大的。”“有沒有可能是我們現在不熟。”宋清衍想起沈黛怡當年追在自己身邊,聲音嬌嗲慣會撒嬌,宛若妖女,勾他纏他。小妖女不告而別,時隔多年再相遇,對他疏離避而不及。不管如何,神子要收妖,豈是她能跑得掉。某天,宋清衍手上多出一枚婚戒,他結婚了。眾人驚呼,詫異不已。他們都以為,宋清衍結婚,不過只是為了家族傳宗接代,那位宋太太,名副其實工具人。直到有人看見,高貴在上的男人摟著一個女人親的難以自控。視頻一發出去,薄情寡欲的神子人設崩了!眾人皆說宋清衍高不可攀,無人能染指,可沈黛怡一笑,便潦倒萬物眾生,引他墜落。誰說神明不入凡塵,在沈黛怡面前,他不過一介凡夫俗 子。
20.2萬字8 45509 -
完結80 章

幸福不脫靶
他連吵架時擲出的話都如發口令般短促而有力:“不許大喊大叫!給你十秒時間調整自己,現在倒計時,十,九……” 她氣憤:“有沒有點兒時間觀念?需要調整十秒鐘那麼久?” 他是個很霸道的男人,對她裙子長度引來的較高回頭率頗有微詞:“你可真給我長臉!”見她呲牙笑得沒心沒肺,他板起來臉訓她:“下次再穿這麼短看我不關你禁閉。” 她撇嘴:“我是滿足你的虛榮心,搞得像是有損安定團結一樣。” 我們的小心願,幸福永不脫靶。
24.6萬字8 90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