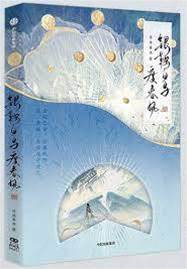《世子他為何如此黏人/世子清冷但纏人》 第29章
柳箏看向不知何時打翻在床的針線籃,繡繃上那團醜花真是越看越醜。看著看著就笑了。
宋硯抱著,忍不住左右來回地輕輕晃。
柳箏了宋硯的肚子:“你吃飯沒有?”
一被主,宋硯渾的溫度都要往上升好幾分。他腹上幾度收,更黏糊地蹭了:“……還沒有。”
“中午吃的什麽?”
“忘記了。”
柳箏挑眉:“這也能忘記?”
問完就把手拿開了,宋硯不依,又拿了的手放肚子上,難耐地趴在肩膀上:“馮策弄的,黑糊糊一碗,認不出來。”
柳箏“嘁嘁”地笑起來,笑得眼睛都彎了月牙。
宋硯看笑,自己也笑起來:“我們太笨了。”
柳箏拉他起來,笑問他:“黑糊糊一碗,認都認不出來,你也吃完了嗎?”
“吃完了,馮策做得很努力。”
柳箏笑得肚子要發痛了,又坐回了床上:“你就不怕吃了會沒命?”
“不會的,馮策不會害我。”
柳箏忍不住手他的臉:“你怎麽有點可啊。”
宋硯眨眼:“嗯?”
柳箏又他的臉:“真不能總把你一個人留在家裏了,估計不是死就是毒死。”
宋硯又笑了:“以後你去哪裏就把我帶到哪裏嘛,我太笨了,學東西太慢。”
柳箏再次起拉他起來:“走吧,我給你弄面條吃。先生送了我好些點心,你也嘗嘗。”
到了廚房一看,馮策已經在竈臺前生火了,正目不轉睛地盯著王初翠切面條。
見他們來了,王初翠笑道:“哎呦呦,馮策一見著我就說得不行了,爺,你也沒吃飯吧?”
“沒有,好。”
柳箏舀了兩碗面,挑了幾只蛋打進盆裏,又掐幾蔥切碎放進去,和了鹽攪拌,然後讓馮策順便把另一只竈臺也點起火。拿鍋鏟弄了點兒豬油在鍋面上化開,溫度差不多了才把面糊倒進去,一連烙出了四五張蛋面餅。香氣一陣一陣地飄了出來。
Advertisement
柳箏把烙好的蛋餅擱進盤子裏遞給宋硯和馮策:“吃吧,馬上面條也做好了。”
馮策心急,等宋硯拿筷子夾走了一張就手卷了兩張狼吞虎咽起來,被燙得“斯哈斯哈”個不停。宋硯顯然也得厲害,但吃相比他強多了,夾在碗裏等涼些了才一口一口地咬。
餅還沒吃完,王初翠就已把鍋裏的面條撈出來了,兩碗各碼了兩排香煎臘臘腸。馮策吸溜吸溜一碗下肚,著肚子舒舒服服地打了個飽隔。
等都吃完飯洗過澡了,宋硯和柳箏一起到院子裏坐著吹風。柳箏披散著半幹的發著滿天繁星和草叢中的螢火蟲發呆。宋硯擡手幫把頰畔的碎發捋到耳後,眼睛裏盛著笑意:“箏箏好。”
柳箏回頭看他:“你也好看。”
“有多好看?”
“那我有多?”
“比什麽都,有你在我面前,我看不進去花,看不進去月亮,看不進去星星,什麽都看不進去,只想一直看著你。”
柳箏瞥他,他眼睛裏倒映著星,倒比星星本更奪目了。多麻的話,他說著竟也不覺得尷尬。
宋硯悄悄地把手向的手,輕放在的手背上,指腹下是潔的指甲。他覺得這樣的夜晚好幸福好幸福,原來能和喜歡的人閑坐在一起是這樣一種好的。
怪不得娘親說人是不能沒有的。沒有和行走有什麽區別?他好像直到這兩日才真正地開始活著。
可是幸福之下,他仍有不滿足。
他和箏箏遠沒有到心意相通的地步。很主對他說起有關自己的事,而他不敢主對說起自己的那點事。心意未通,那不論他們得有多近,所隔還是好遠好遠。
柳箏想捋一捋自己的頭發,手指剛要,被上面那只大手握住了。柳箏看向他,宋硯眸瑩瑩:“箏箏,你是如何知道賞花宴的事的?”
Advertisement
終于還是問到這個問題了。柳箏移開視線:“你先前沒讓人查過我嗎?”
宋硯睫了兩下,似乎難以置信:“……箏箏以為我是那樣的人?”
柳箏心有詫異。以他這種份,難道不會探查自己邊出現的所有人嗎?雖說是他自己主招惹上的,但他難道查也未查就來招惹嗎?
柳箏頭一次無比懷疑他在說謊。
顧師丈派去吳江縣理當年舊事首尾的人還沒有回來,也不知是不是真有人去查了。不過退一萬步說,就算宋硯沒查,國公府也會有人查的吧。事都過去十一二年了,應該沒那麽容易被人發現……
宋硯從的沉默裏知道了答案,前一刻還充盈了整顆心的好與幸福好像一下子都了一層薄薄的、一就破的。先前的傷心與難過和他此刻的心相較都不算什麽了。比起箏箏對他生氣、漠視、不在意,對他的誤解更像是在剜他的心。
柳箏再次手,宋硯攥了攥的指尖,還是松開了。
柳箏撥弄長發,翻出底下那層發繼續晾著,宋硯聞到了上好聞的味道。他貪,不舍,卻也留不住。
他迫切想解釋,但頭在犯痛,哽咽讓他一個字都說不出口。宋硯不認為自己是多脆弱的人,至沒脆弱到輕易就要流淚的地步,可是在箏箏面前,他時常發現自己就是個很沒用的人,所有緒都被的一舉一、一言一語牽著,傷心了、難過了,就是會想伏在上流淚。
箏箏會那樣想他,那他這幾日數次與接,把自己最脆弱、最無助的一面暴給看時,又是如何想他的呢?
是否覺得他心機頗重,覺得他虛僞矯,覺得他可笑?
宋硯怔怔想了許久。
Advertisement
柳箏覺得頭發晾得差不多了,忙了一天有點兒累,想上樓睡覺去。正要起,偏頭發現宋硯正愣愣盯著院牆看,不甚明朗的月星之下,他眼睛裏有兩團閃著的霧氣。
柳箏在他眼前揮揮手:“發什麽呆呢?睡覺吧,驅蚊香快燃完了,小心被蚊子叮。”
宋硯看著的手,那些話還是憋在心裏難以出口。
柳箏不知道他怎麽了,也不管了,提步就想離開。未走半步,的手被他拽住了。柳箏蹙眉看他:“到底怎麽了?”
剛才不還好好的嗎?
“……我沒有查你。”宋硯輕聲道。
柳箏沉默,過會兒道:“知道了。”
“你不知道。”
宋硯不知道還能怎麽解釋,可他沒辦法帶著這一肚子委屈結束今晚。他得讓明白他不是那樣卑劣的人,至在面前他絕不是。他的是拿得出手的。
柳箏再次沉默,但已明白他在為了什麽而傷心了。這又不是什麽大事……他查也好,不查也罷,沒什麽怕的。
“你怎麽一點都不明白我……”宋硯的聲線在幾不可察地抖著,他擡眼,眼睛裏是點點碎。
柳箏確實不明白,不懂這有什麽好傷心的。的確不在意他查不查。
宋硯不了的懵懂和長久的沉默了。箏箏明明是那麽聰明的一個孩子,為什麽總是不能明白他的心意?
他心裏發了狠,把拽到了自己懷裏。
柳箏沒設防,一下坐到了他上,肩膀被他用手臂圈著,臉被他用手輕地著,眼睛被迫與他對視。
離得太近了,近得柳箏能清晰地看見他眸中自己的倒影。他制著渾的力氣,腹與大上的都繃著,甚至有點發燙,柳箏整個人都被他錮住了,偏偏他眼神還是溫的,指尖的也是無比小心珍視的。
猜你喜歡
-
完結121 章

攻心毒女:翻身王妃
可憐的李大小姐覺得自己上輩子一定做錯了什麼,這輩子才會遇到這麼多衰事。好在美人總是有英雄相救,她還遇到了一個面如冠玉的男子相救,這麼看來也不是衰到了極點哦? 不過偽善繼母是什麼情況?白蓮花一樣處心積慮想害死她的妹妹又是什麼情況?想害她?李大小姐露出一絲人獸無害的笑容,誰害誰還不一定呢!
46.5萬字8.18 19134 -
完結337 章

成為人生贏家的對照組[快穿]
她不是人生贏家,卻比人生贏家過的還好,你敢信?人生贏家歷經磨難,一生奮斗不息,終于成了別人羨慕的樣子。可她,吃吃喝喝,瀟灑又愜意,卻讓人生贏家羨慕嫉妒恨。在紅樓世界,她從備受忽視的庶女,成為眾人艷羨的貴夫人,作為人生贏家的嫡姐,也嫉妒她的人…
212.4萬字8 11147 -
完結686 章

神機毒妃只想寵反派
穿成狗血文女主,黎清玥開局就把三觀炸裂的狗男主丟進了池塘。為了遠離狗男主,轉頭她就跟大反派湊CP去了。原書中說大反派白髮血瞳,面貌醜陋,還不能人道,用來當擋箭牌就很完美。然而大反派畫風似乎不太對…… 她逼他吃噬心蠱,某人卻撒起嬌: “玥兒餵……” 她缺錢,某人指著一倉庫的財寶: “都是你的。” 她怕拿人手短,大反派笑得妖孽: “保護好本王,不僅這些,連本王的身子都歸你,如何?” 【1V1雙強,將互寵進行到底】
130.7萬字8.18 178083 -
完結224 章

吾妹千秋
照微隨母改嫁入祁家,祁家一對兄妹曾很不待見她。 她因性子頑劣桀驁,捱過兄長祁令瞻不少戒尺。 新婚不久天子暴斃,她成爲衆矢之的。 祁令瞻終於肯對她好一些,擁四歲太子即位,挾之以令諸侯;扶她做太后,跪呼娘娘千秋。 他們這對兄妹,權攝廟堂內外,位極無冕之王。 春時已至,擺脫了生死困境、日子越過越舒暢的照微,想起自己蹉跎二十歲,竟還是個姑娘。 曾經的竹馬今爲定北將軍,侍奉的宦官亦清秀可人,更有新科狀元賞心悅目,個個口恭體順。 照微心中起意,宣人夤夜入宮,對席長談。 宮燈熠熠,花影搖搖,照微手提金縷鞋,輕輕推開門。 卻見室內之人端坐太師椅間,旁邊擱着一把檀木戒尺。 她那已爲太傅、日理萬機的兄長,如幼時逮她偷偷出府一樣,在這裏守株待兔。 祁令瞻緩緩起身,握着戒尺朝她走來,似笑非笑。 “娘娘該不會以爲,臣這麼多年,都是在爲他人作嫁衣裳吧?”
34.6萬字8 3662 -
完結370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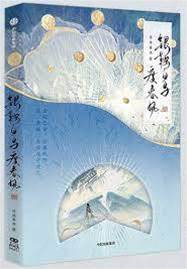
銀鞍白馬度春風
君主剛愎自用,昏庸無能,掩蓋在長安錦繡繁華之下的,是外戚當權,蟻蛀堤穴。 賢仁的太子備受猜忌,腐蠹之輩禍亂朝綱。身爲一國公主,受萬民奉養,亦可濟世救民,也當整頓朝綱。 世人只掃門前雪,我顧他人瓦上霜。這是一個公主奮鬥的故事,也是一羣少年奮鬥的故事。 ** 你該知道,她若掌皇權,與你便再無可能。 我知道。 你就不會,心有不甘嗎? 無妨,待我助她成一世功業,他日史書之上,我們的名字必相去不遠。如此,也算相守了。
55.4萬字8 191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