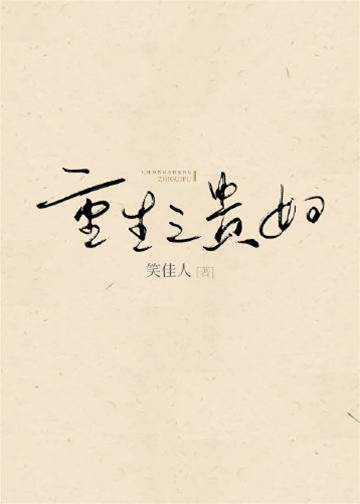《被渣后和前夫破鏡重圓了》 第 37 章
溫禾安早就在等溫流叩開第二道第八的時機。
那是最能要命的時候。
“我今日來,有件事想問問你。”溫禾安看著,神鄭重,沉後啓:“你這可有關于的文獻記載,有多算多,我都買下來。”
提到,修士莫不變。
無他,能被稱作的,手段之損可怖,非常人所能想象,偶然冒出一件,就足以讓幾個州城做一團。
林十鳶倒是不怕溫禾安沾染,的氣息純正溫和,決計和這兩個字沾不上任何關系,只是很好奇:“若是我沒記錯,這是你第二次我替你留意了,你究竟在查什麽。”
溫禾安點了點眉心,并未否認:“一樁陳年舊事。”
“你也知道,有能力編纂的家族門派,閉著眼睛都能數出來,有關的記載又半個字都不能流市面,我們不做這等虧本買賣,這一時半會的——”林十鳶看著格外專注的眼睛,婉拒的話一時拐了彎,嘆息著松口:“我只能盡量給你留意。”
竟覺得,溫禾安對這事的態度很不尋常,比對付溫流和江召都來得上心。
談完事,過半開的窗牖往下看,暮四合,落日熔金,再過一會,估計天就黑了。
林十鳶還是留下來用膳,溫禾安搖搖頭,道:“我得回去。”
眼前浮現出陸嶼然的眼睛。
他生了雙睡眼,眼皮冷薄,線條狹長,瞳仁會在燭下泛出清冷之,靜下來與人對視時,不免給人種深邃專注之,好像有掌控人心的本事,人無從拒絕。
溫禾安鬼使神差,每次都會遲疑著答應他,然後為了騰出時間苦惱半天。
如果言而無信,這雙眼睛就會盛滿倨傲漠然和一層七八糟的風雨,旋即水靜江寒,眼下斂得鋒銳,能看出明顯的不開心。
Advertisement
就。
怪可惜的。
大多數時候,能順著他,溫禾安都會順著他。
==
巫山酒樓臨時開鑿出的地牢裏,腥之地融進冷的空氣中,兩難聞的氣味撲面而來,人作嘔。
那名被生擒的九境被關在地牢裏,他叩開了第八,于是關押的陣仗格外大。
系在他上的大鎖鏈有足足十二,貫穿前後肋骨,白骨森森,流如注,鎖鏈上弧的雷一刻不停地流,只要他有所異,立刻就會毫不留地轟下來,這是陸嶼然親自出手布控的。
因此。
那名九境沒死在傀線上,但差點代在這該死的巫山雷上。
陸嶼然枯寂一夜,今早起來,得了溫禾安兩句應承後,眼裏淡漠的懨鷙倒是散去一些,然一進地牢,眉骨攀附起淩然之,難以抗拒,只人臣服的氣勢悉數回到他上。
聽命固守地牢的執事們紛紛行禮,不敢直視他的眉眼,餘裏只能看見一片由銀線織就的麒麟寬袖,其上圖案張牙舞爪,清貴人。
商淮原本是要“嘖”的取笑陸嶼然幾聲的,但想到要見自己父親,也沒了心,難得愁眉苦臉,在心中一個勁唉聲嘆氣。
陸嶼然腳步停在那名九境跟前,仄狹小的囚室裏聊勝有無地鋪了層稻草,此刻都被沁了,經過幾天,發出一種腐爛的腥臭氣,腳踏上去,會踩出一層猩紅。
他睨著這位被吊起來的九境,眼中如深潭,看不出任何一瀾漣漪。
審了幾天,能審的基本都審出來了。
人肖諳,年歲不小,倒是有一修為,又走了天大的好運在境中覺醒了第八“萬象”,這等噱頭唬住了不高門顯貴,每年開出天價酬金,讓他效力。可他渾沒個正行,吊兒郎當不腦子,往往想一出是一出,喜歡挑戰刺激,但做任何事都是三分鐘熱度,遇到危險甭管什麽使命任務,先跑為上,混不管同伴的死活。
Advertisement
往往是沒到一年,就被好言好語地辭退請出來。
他這次為王庭效力,圖的也是個刺激。
破壞神殿,暗害帝嗣,瓦解巫山。
多麽宏大的理想,是一聽,就人熱沸騰,這深深吸引住了他。為此,他不惜飛蛾撲火,甚至主接了傀陣師的那傀線,在那幫孫子的蠱下,有一段不短的時間都覺得自己是找到了畢生的理想。
但他骨子裏就是那種格,急功近利,說白了,就是沒有耐,只能接功,失敗好幾次後,興趣就消減了。
就算是條狗,你也得拿骨頭在前面吊著他,讓他聞到點香吧。
這個計劃可以說是只有失敗,沒有功的時候。
每次失敗,都要損失許多東西,無數通宵達旦,燒燈續晝的力白費砸進去如泥牛海,有去無回,還得做好隨時犧牲的準備。
而且肖諳深信自己被騙了。
蓋因他發現,除了以上三條,這個計劃中還有另一組人分心去做別的事去了,什麽外島計劃,你都不知道它究竟是在做什麽,誰也不會給個解釋,但可以肯定的是,和巫山,帝嗣,沒有半錢的關系。
出事之前,他已經想跑路了,正在揪著頭發思索如何解除傀線,山高路遠,再尋別的刺激。
誰知道會發生後面的事。
肖諳腸子都悔青了。
陸嶼然手掌微一握鎖鏈,就聽叮當悶響,雷芒大盛,半死不活的肖諳陡然悶哼,像被看不見的線提著,猛的揚起了腦袋,供三寸之外氣質無雙的男子打量審視。
“公子。”幕一踏進來,低聲稟報:“商大人到了。”
陸嶼然微一垂眼,聲線清至極:“讓他進來。”
商淮了頭上的玉冠,又整整裳袖口,最後不自在地過自己的鼻脊。
Advertisement
商譽是天懸家現任家主,亦是天懸家唯一一個叩開了第八的人,他們這樣懷絕技,天賦異稟的種族,在修行之路上,總是比尋常人難上許多。
商大人格古板,嚴于律己,到了如今這個年紀,家族和睦,子大多還算爭氣,家族不溫不火,沒有下墜之勢,能他夜裏翻來覆去,長籲短嘆的,唯有離經叛道的逆子商淮。
自家本事都沒學好,非要去學什麽擺渡之法。
而今一見面,他便先翹了翹胡子,以眼神剜了他一刀。
接著對陸嶼然行禮:“臣見過公子。”
陸嶼然長袖一,靈力托起他的臂膀,冷聲道:“此人拜托商大人了。”
商譽哪裏敢當他這聲拜托和大人,他常見一些輩分遠還在自己之上的老者在陸嶼然跟前依舊畢恭畢敬,莫敢不從,自己卻因為商淮的緣故,不免得到陸嶼然一些另眼看待,這他又喜又愁。
他不敢分神,記得自己長途跋涉而來是有要事在,當即站到肖諳跟前,渾濁的眼睛盯著他看,是那種格外細致,要將他臉上每個表,每塊骨骼位置都記住的看。
肖諳被看得頭皮發麻,氣若游地看著陸嶼然:“……我知道的,都說了。”
只唯獨瞞了一件事。
一件他唯一覺得搭上半條命進去也算值得的事,這曾他小有就,可以說,那麽多件事都是瞎忙活,唯有這件,才真正朝著目標邁近了微小的一步。
商譽要看的,就是這一件事。
第八探心悄然發,朝著肖諳一人籠罩而去。
片刻後,商譽陡然睜開眼,連著退了兩步,被商淮扶住了。
陸嶼然看過來,眉頭鎖,問:“看到什麽了?”
商譽膛裏的冷氣攪著,渾濁的眼中尚有驚懼之未曾下去,因為二月末的寒意,他從鼻腔裏深深吐出一團白霧,聲音無比凝重:“公子,他們在神殿中了手腳。”
Advertisement
神殿對巫山來說意味著什麽,無人不知,那是帝主留給巫山的東西,是一種無可取代的象征,同時也是巫山最大的。
商淮都驚住了。
陸嶼然臉被冰霜覆蓋,但不至于和他們一樣就此了陣腳。世人鮮知曉,神殿分為殿與外殿,作為被神殿選中的人,舉世之,唯他一人可踏殿,那些人要做手腳,只能在外殿。
不會出很大的問題。
但就此留著終究是個不小的禍患。
他不能拿巫山冒險。
“做了怎樣的手腳,大人可看見了?”陸嶼然問。
商譽搖頭,看著有些疲憊,這一下好似耗盡了一天的力氣,連渾的重量都搭了一半在商淮上:“不曾,只窺得很短的一點片段。此事事關重大,臣明日再來一趟,再看一場。”
陸嶼然下心中翻騰而起的戾氣和煩倦,深深一闔眼,朝幕一擺擺手,示意他們看好此地,自己轉出了地牢。
商淮被商譽揪著好一頓說教,好容易找了個借口,此刻跟上陸嶼然,眉頭皺“川”字,搖著玉扇嘆息,似是自言自語:“現在這個意思是——這個塘沽計劃,咱們是不查也得查了。”
陸嶼然不答,擰著眉去了趟巫山酒樓,消息當即從諸位長老裏傳回了主家,巫山數不盡的銳暗衛出,在神殿外逐一排查,剎那間風雲湧,局勢變幻莫千。
他看著窗外逐次亮起的燈火,算著晚膳的時間,將自己的麒麟腰牌甩給商淮,垂著眼吩咐:“傳我的命令,去奪永,芮,淩三州,同時南上,去占天都寒山的靈礦。”
商淮呼吸一窒,覺得自己懷裏捧著塊燙手山芋,接不是,丟也不是。
永,芮,淩三州是富庶之地,在王庭的庇佑下,市集繁盛,産富,每年産的糧可供給王庭軍隊無度揮霍,至于寒山的靈礦,那就是座寶庫,天都去年一的進項都出自這條礦。
這一計猛藥下下去,是要現在開戰嗎。
陸嶼然這是自己不開心,也擺明了要從對手上一層皮下來。
說話間,陸嶼然的四方鏡亮了下,撈起來一看,發現是溫禾安。
【晚上還有飯吃嗎?】
心平氣和地陳述:【我已經在魚塘裏喂了一個時辰的魚了。】
陸嶼然拍了拍商淮的肩,將椅背上搭著的鶴氅撈到臂彎裏,眉目凝霜一片,起往外走,商淮手忙腳著那塊腰牌,在四方鏡上急布署,見狀連著誒了幾聲,追上來,問:“你現在上哪去?”
“回去吃飯。”
“……”
商淮納悶了,怕他把另一件正事忘了似的,揚聲提醒:“你不去觀測臺啊?”
陸嶼然眉間煩躁之更深一點:“吃了再去。”
商淮這次是真嘖了聲。
猜你喜歡
-
完結730 章

太子殿下你被逮捕了
世人皆讚,寧安侯府的四小姐溫婉寧人,聰慧雅正,知書達理,堪稱京城第一貴女,唯有太子殿下知曉她的真麵目,隻想說,那丫頭愛吃醋,愛吃醋,愛吃醋,然後,寵溺他。
134.7萬字8 8508 -
完結20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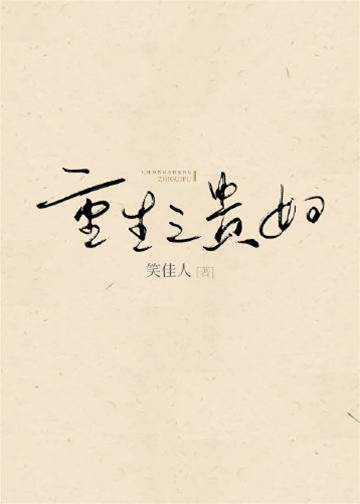
重生之貴婦
人人都夸殷蕙是貴婦命,殷蕙也的確嫁進燕王府,成了一位皇孫媳。只是她的夫君早出晚歸,很少會與她說句貼心話。殷蕙使出渾身解數想焐熱他的心,最后他帶回一個寡婦表妹,想照顧人家。殷蕙:沒門!夫君:先睡吧,明早再說。…
66.6萬字8.72 195765 -
完結387 章

掌上齊眉
謝雲宴手段雷霆,無情無義,滿朝之人皆是驚懼。他眼裡沒有天子,沒有權貴,而這世上唯有一人能讓他低頭的,就只有蘇家沅娘。 “我家阿沅才色無雙。” “我家阿沅蕙質蘭心。” “我家阿沅是府中珍寶,無人能欺。” …… 蘇錦沅重生時蕭家滿門落罪,未婚夫戰死沙場,將軍府只剩養子謝雲宴。她踩著荊棘護著蕭家,原是想等蕭家重上凌霄那日就安靜離開,卻不想被紅了眼的男人抵在牆頭。 “阿沅,愛給你,命給你,天下都給你,我只要你。”
84.8萬字8 45840 -
完結322 章

啟稟將軍,夫人又跑了
蘇沉央一遭穿越成了別人的新娘,不知道對方長啥樣就算了,據說那死鬼將軍還是個克妻的!這種時候不跑還留著干嘛?被克死嗎?“啟稟將軍,夫人跑了!”“抓回來。”過了數月。“啟稟將軍,夫人又跑了!”“抓回來。算了,還是我去吧!”…
86.3萬字8 86025 -
完結257 章

春水搖
赫崢厭惡雲映是一件自然而然的事。 她是雲家失而復得的唯一嫡女,是這顯赫世家裏說一不二的掌上明珠。 她一回來便處處纏着他,後來又因爲一場精心設計的“意外”,雲赫兩家就這樣草率的結了親。 她貌美,溫柔,配合他的所有的惡趣味,不管他說出怎樣的羞辱之言,她都會溫和應下,然後仰頭吻他,輕聲道:“小玉哥哥,別生氣。” 赫崢表字祈玉,她未經允許,從一開始就這樣叫他,讓赫崢不滿了很久。 他以爲他跟雲映會互相折磨到底。 直到一日宮宴,不久前一舉成名的新科進士立於臺下,吸引了所有人的目光。 包括雲映,她脊背挺直,定定的看他,連赫崢叫她她都沒聽見。 赫崢看向那位新晉榜首。 與他七分相似。 聽說他姓寧,單名一個遇。
38.5萬字8.18 548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