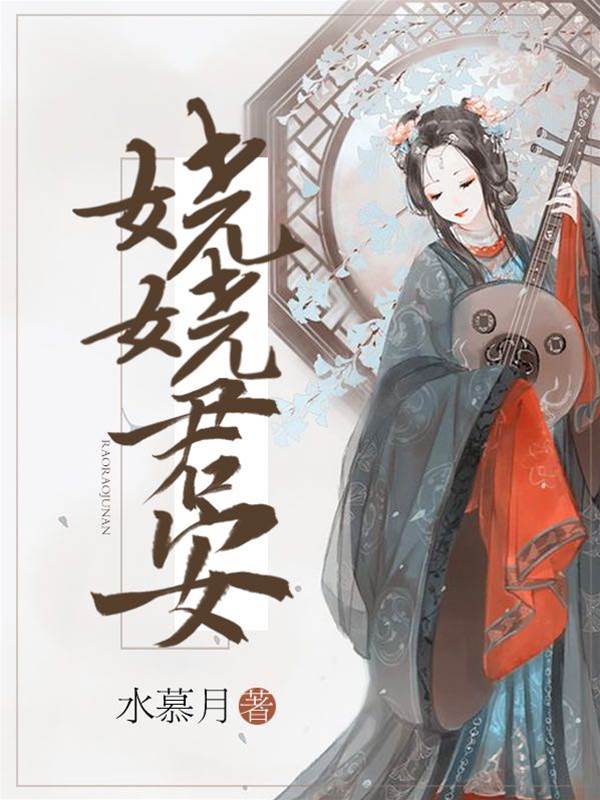《被渣后和前夫破鏡重圓了》 第 87 章
江無雙也只是笑,然而笑眼之下,長劍離手,劍氣淩然直過去,威懾的意味很是明顯,素瑤卻上前一步,接下了這道邀戰。
手之前,朝江無雙遞了個眼神。
他若是出手,溫流也不會坐視不管,兩人何必無謂膠著,這種場面,應付得過來。
江無雙權衡半晌,最終掌將劍下。
場中有人起手來,分為幾片戰局,素瑤戰勝溫流心腹之後,又接著打敗了巫久,最後與聞人悅僵持了會後勝出,自此之後才算在場中站穩了腳跟。
沒有松一口氣,反而隨著時間的推移而越發繃了心神。
有幾個早該出現的人,到現在都沒現。
人群中倏的有聲音抑地道:“九十窟有人出來了,那是李逾吧?”
“看不太清楚,他怎麽戴面了?”另有聲音回:“……他不是一向無法無天,得罪了這邊又得罪那邊嘛,誰家通緝令上沒他的名字?仗著有聖者護著,恨不能橫著走,從沒見他有戴面的時候。”
“這時候能從九十窟走出來的,除了他,也沒別人了。”
來的確實是李逾。
然而他才踏出來,江無雙就握住了劍,劍毫不避諱遙指他眉心,無視一切喧然,眼梢笑意如冰凝凍,專門等了他許久似的:“九十窟李逾,門主之一,是吧?在瑯州帶走徐遠思的人是你?”
他朝前踏出一步,劍意如山呼海嘯,所過之,存存碎盡,兩個呼吸間就斬到了李逾眼前。這等存在,起真格來,本不給人反應時間,須臾間便是懸崖峭壁,生死難料。
“知道自己在做什麽嗎?”
劍尖幾刺進李逾眉心中,他急退十數步,擡手對抗,聽著這話,心裏是真想罵人。他也不是第一次被這三家的狗追殺,從未有一次覺得自己這麽冤。
Advertisement
徐遠思、如果不是溫禾安提起,他都不知道這是哪號人。
“在做什麽?”
一道脆生生的聲音響起,替李逾發問。一個梳著長長蠍子辮的姑娘雙手負于後,閑庭散步般踱進來,長得俏,穿得也俏,喇叭袖與擺一起隨風擺,上面的花紋似乎活了過來。
就在此時,周數米的一切都陷詭異的淤塞中,唯一能震著掙的只有江無雙的劍,淩枝這時才從後出只手,手指敲在劍尖上,頓時寒芒迸發千丈,那柄吞吐鋒芒的寸劍倒飛回江無雙手中。
淩枝邊的“領域”也碎了。
“好熱鬧啊。”也不跟前頭的兩位搶位置,徑直站到了溫流後,要了右邊第二座傳承,慢吞吞地一擡眼睛,自顧自道:“我最喜歡看熱鬧了。”
江無雙和溫流同時看,皺起了眉,心中有猜測,但看這裝扮,這年齡,又無論如何跟想象中的人對不上。
淩枝不看江無雙,仔仔細細觀察起了溫流,像在研究一樣好奇已久的,倒要近距離看看虛實深淺,看著看著,就出了一點殺意。溫流對這東西太敏了,霎時間握了手掌,強大的靈流波蜿蜒流淌。
第八被破壞後,不得不接了這個事實,從前難以制的脾氣也有所緩和,但依舊十分討厭那些以為在溫禾安手裏吃了兩次虧就可以肆意挑釁的蠢貨。
冷然一掀眼:“閣下這樣喜歡熱鬧,怎麽從前那麽多熱鬧都不見出來過。”
淩枝卻朝笑了下,眼睛沒有笑意,黑白分明,靜得像兩點暈開的料:“你也不認識我嗎。”
手點了點自己,直起好心好意自我介紹:“誰說我沒來看過熱鬧。上次溫禾安對你出手,將你第八破掉的時候我就在啊,諾,就站在那邊看的,你用以挽救的秋水還是我的呢。”
Advertisement
“記起來了麽。”
這樣一說,誰都明白了的份。
這說的話,可謂是字字嗆人,滿帶嘲諷,得了,這樣看來,又是一個與溫流結了仇的。
“是麽。”溫流忍了會,歇了和打鬥的心思,冷傲地回:“那真是可惜,家主的東西,竟會有親自到我手中。”
淩枝這回真笑了。
氣笑的。
另一邊,江無雙緩緩道:“家主既然喜歡看熱鬧,站著好好看就是,王庭與這人之間的恩怨,你應當不會想管。”
說的是方才為李逾攔了那一劍。
淩枝一擡下,表現出一副冷眼旁觀做壁上觀的神,李逾和亦是老相識,但關系不好不壞,本沒什麽話說。
李逾回想起溫禾安說話,點點頭,耐人尋味地開口:“你這是失了瑯州要跟我算賬,還是失了永,芮,淩,瑯四州,惱怒將爛賬都堆我頭上?前者還勉強與我有點關系,若論後者,我豈不是冤得很。現在控擁永,芮,淩三州的是誰,你找他奪回來不就是了,也不必這樣大肝火。”
江無雙噙著笑,道他找死。
李逾掌心中亦有華漫出,打江無雙他確實是打不過,可不至于連跟他正兒八經過個幾招的本事都沒有,除非江無雙上來就用第八生機之箭,可他敢嗎。
他賭江無雙不敢。
他這第一座傳承守得岌岌可危,溫禾安沒出現,他最大的宿敵陸嶼然也沒出現,他敢將底招都了?
江無雙手掌往劍鋒上一抹,流湛湛,千萬道劍意虛影橫亙在半空中,不的時候像天空中下了牛般細的春雨,這些虛影很快有序糾纏起來,又織兩道斜斬而上的劍勢。
這得是在劍道上走得十分深的人才能參悟的本領,鬼神難測。
Advertisement
就在這時,又有人走了進來。
戴著金邊面,穿長長,走時曲線利索流暢,帶著風雨將至的颯爽力量。很這樣裝束,然而的眼睛,溫的聲線,在場諸位都悉。
“別蓄力了,收回去吧。”
溫禾安看向江無雙這道攻勢,平靜地道。
見到,溫流覺自己渾汗都豎了起來,就像遇見了天敵,膛裏既有無邊憤怒,又有無邊忌憚,心知這不是個好時候,也不是個好的戰場,淩枝還在一邊看好戲,隨時準備給自己迎頭痛擊。
索冷冷撇開視線,眼不見為淨。
“你要保他?”
江無雙沉沉看了溫禾安一會,說實話,他很不願意這樣一個難纏的對手攪合進王庭大局裏,天都與巫山就夠讓人頭疼的了——但如果溫禾安真要順著徐遠思知道些什麽,不論付出怎樣的代價,他必定得除了。
如此想著,面上卻不顯,嗤然道:“還是說二主現在另謀高就,上了九十窟的船。”
“我不想保什麽人,但更不想被扣帽子。”說著,溫禾安隨意一站,站了最後一個空位,道:“傳承快開了,你要真那麽想打,就帶著他去外邊打,把你的位置讓出來,別耽擱別人的事。”
話音落下,周圍靜了一瞬。
眼見江無雙的攻勢往回收,李逾走到淩枝後面那座傳承站定,或許是真看不慣這等做派,聽了溫禾安的話,非還要嘲諷江無雙兩句:“讓不讓的,也得他守得住。這不是,還有人沒到呢麽。”
確實。
現在場上的站位太過讓人匪夷所思了。一共六道傳承,右邊三道分別為溫流,淩枝和李逾,左邊三道是江無雙,素瑤和溫禾安。
溫禾安排在了素瑤的後面,還站得那樣自然,連爭一爭的念頭好像都不強烈?
Advertisement
這是怎麽了……誰能看不出來,傳承的位置明顯決定著收獲的多,這種東西,還能不爭?就算不跟江無雙和溫流奪第一,第二,總不該拱手讓給素瑤吧?
而且,正如李逾說的。
現在六座傳承全滿了。
但有人還沒到呢。
屆時,誰下場?又是誰能奪得第一,真不好說。
暗湧。
江無雙冷冷地掃視天地之間,劍吞吐浮沉,溫流默不作聲開始蓄力,繃了心神,被溫禾安襲擊過兩次,不用細想,就知道溫禾安只要有作,必定是奔著來的。
來都來了,說不在乎位置,那是假的。
很快,幾位都覺到了來自空氣中的晦之意,有人調了天地間大部分靈力,換句話來說,有人在暗中布置磅礴的招式。
江無雙和溫流對視,都皺著眉,旋即錯開視線,溫禾安一直沒擡頭,真跟專心致志等待傳承開啓將他們卷進去的那一刻一樣。
過了一會,淩枝看向溫禾安,快速眨了下眼。
溫禾安這才如夢初醒般搖了搖手腕,察覺到前面的人已經晦朝投來好幾眼,不由得擡眼,迎上素瑤的視線。
沒人比素瑤更忐忑。
自己後面這個肯定要出手,夾在和江無雙中間,這個位置太糟糕了。
溫禾安知道在想什麽,主問:“要跟我換換嗎?”
素瑤反而松了口氣,手掌心半舒開,毫不遲疑地回:“換。”
兩人換了位置。
就在此時,六道境同時發出“啵”的一聲,像花開的聲響在耳邊放大了數倍,朦朧的白霧一點點過來,綿地纏繞手腳,六個人恍若踩著白雲騰空而起。
也就是在那時候,溫禾安了。
依舊是十二神錄的招式,悄然攤開掌心,裏面躺著三朵花苞。花苞呈深紅,形狀像牡丹,但比牡丹小,因為太過鮮,豔得像。作迅疾縹緲,將其中兩朵拍在江無雙雙肩上,像兩顆釘子進了骨中。
江無雙的騰空而起,轉瞬落在了溫流跟前,右側第一道傳承旁邊。
他很快發出抑的怒吼聲。
沒想到,真沒想到。江無雙一直在防半空中蟄伏的陸嶼然,他想的也是,就算溫禾安要出手,也是對溫流出手。
又沒有生機之箭,要這座傳承做什麽。
跟天都的關系已經是板上釘釘的惡劣,何必再得罪王庭。
他不是沒防,但他防的都是大殺招,不是兩朵使他騰挪的花。
但現實沒給他太多思考的時間。
兜頭朝江無雙襲來的,是溫流的殺招,這是為了對付溫禾安準備的,可謂是毒辣至極,沒有半分留手。
在察覺到異的第一時間,溫流就祭出了這招,現在收也來不及收,兩人的攻勢撼天震地,崩碎雲霧,重重撞擊在一起。
江無雙是想過第一時間回去的,可朝自己原先站著的位置看過去時,發現它已經被溫禾安占據了。李逾作更快,一走,他便閃到了原來的位置。
由右側第三,為了左側第二。
溫禾安清清靜靜看過來,將手中剩下的那朵花踩在腳下。
一個巨大的防護靈罩出現在視線中。
攻守兼,好手段!
時間有限,白霧越來越濃,範圍越擴越大,江無雙沒法再轉回去破開溫禾安的防,并且很快分出勝負。
他拿定主意,不再糾結,轉而和溫流戰到一起。
兩邊第一座,對他來說都是好東西,既然如此,那就看形勢來。
即便此時他心中窩著團驟烈的火。
算著最後的時限,一直在他們後正兒八經就差搬張椅子來看戲的淩枝走進戰局中,擡手拍了拍兩人的肩頭,笑地道:“我說,不然你們去後面打吧。”
格何等睚眥必報,惦記著先前溫流嗆的那句,此時好心地彎腰在耳邊問:“我師兄有沒有和你說過,我最擅長的招式是什麽啊?”
跟分好朋友之間新奇的一樣。
溫流直覺不好,眼瞳微,卻見淩枝五指攏起,在眼前直接控下。
收斂所有小孩的笑意,變得沉穩,端重,一字一句道:“——空間。”
此片狹小空間了聽話的奴隸,其中的兩人本沒見過這種,只不過是一眨眼,真是一眨眼,他們便被丟到了後面。
江無雙突然想起,那日溫禾安打完穆勒,聽說有個小姑娘在找待的小世界,用的法出神莫測,能將小世界悉數召喚出來。
下一刻。
六道境都開了,濃霧彌漫,難以抵的眩暈朝每個境側的那道人影席卷而去……
此時此刻,這六人的順序與最開始,變了個天翻地覆。
左側三座變為溫禾安,李逾,素瑤,右側三座則是淩枝,溫流,江無雙。
意識完全墜落消散之前,江無雙暴怒,腦子裏閃過兩個念頭。
——陸嶼然本沒來。他狂妄至極,一意只要最好的,未雨綢繆不在他的考慮範疇之。
——溫禾安,淩枝,李逾都是一夥的,他們事先就商量好了。他們不費吹灰之力贏了個徹底,得到了所有能得到的好。
猜你喜歡
-
完結182 章
屠戶家的小娘子
胡嬌彪悍,許清嘉文雅。 他們的婚後生活是這樣的: 胡嬌:「相公你說什麼?」 許清嘉:「……身為婦人就應恪守婦德……」 胡嬌:「相公我耳背,你近前來說……」緩緩舉起手中刀…… 許清嘉……許清嘉強擠出一抹笑來,「娘子……娘子言之有理!」 原本是馴婦記,最後變成了馴夫記。 胡嬌:「……」我啥都沒幹! 許清嘉:……娘子言之有理!」內心默默流淚:誰能告訴我,當大官還要附贈個怕老婆的屬性?這不是真的!
73.4萬字8 8602 -
連載439 章

夫人她每天都想和離
為報恩所娶的夫人沈聽瀾膽小無趣,白遠濯很不喜。 可最近他發現事情有些不對勁。 先是傾慕他的沈聽瀾提出要和離。再是同僚/下屬/上司們奇奇怪怪的言行: “白大人,貴夫人刻得一手好印章,您愛好印章,與您的夫人琴瑟和鳴,定得了不少好印章,不如與我們分享分享?” “白大人,下官一想到您每日都能享用您夫人做的美味佳肴,便好生羨慕。” “白愛卿,想不到你夫人繡藝如此精妙,那一副《南山僧佛會》太后很喜歡,病已大好!” 白遠濯:“……” 拿不出印章、沒吃過美食,更不知道沈聽瀾繡藝精妙的白遠濯決定去找沈聽瀾談談。 正好聽見沈聽瀾在與人唏噓白府虛度的那幾年:“辣雞愛情,毀我青春。” 白遠濯眉心狠狠的跳了一下。
80.1萬字8 16020 -
完結10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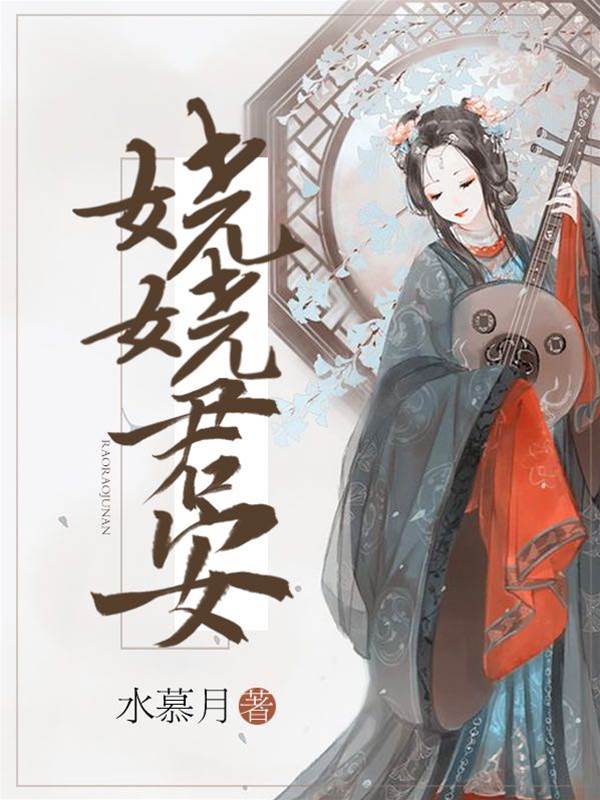
嬈嬈君安
原想著今生再無瓜葛,可那驚馬的剎那芳華間,一切又回到了起點,今生他耍了點小心機,在守護她的道路上,先插了隊,江山要,她也絕不放棄。說好的太子斷袖呢!怎麼動不動就要把自己撲倒?說好的太子殘暴呢!這整天獻溫情的又是誰?誰說東宮的鏡臺不好,那些美男子可賞心悅目了,什麼?東宮還可以在外麵開府,殿下求你了,臣妾可舍不得鏡臺了。
16.6萬字8 14823 -
完結69 章

暴君獨寵小宮女
帝王魏傾陰險狡詐,經常假扮成宮中各個角色暗訪民情。有一天他假扮太監,被浣衣局一個小宮女纏上了。 小宮女身嬌體軟,總對他撒嬌賣萌:小太監你長得真好看,我能抱抱你嗎? 魏傾黑臉:敢?胳膊給你卸下來。然後小宮女親了他一口,魏傾:太監你都下得去嘴? 小宮女安慰他:沒事呀你不要自卑,我不嫌棄。讓我做你的對食吧,我要讓整個浣衣局知道,你的衣服被我承包了。 小宮女可可愛愛,魏傾原本只是看上人家的腦袋,後來迷戀她的吻,再後來,他想要這個人。 有一天霜落髮現了魏傾的祕密,抱着全部身家來找他:快跑吧,被人知道你是假太監要強行淨身的。 魏傾:淨身之前,你再讓我親一下吧! 霜落闖了禍,必須找個太監消災。遇見魏傾後,霜落心想:小太監脾氣好,長得好,我一定要拿下這個男人! 後來,霜落髮現魏傾是個假太監。比起生氣,她更害怕,於是連夜讓情郎跑路。她被親了一口,三個月後肚子大了。 衆人幸災樂禍等着看霜落笑話,可是笑話沒看到,卻見帝王將霜落擁入懷中冷冷威脅:找死麼?妄議朕的皇后! 帝王魏傾陰險狡詐,經常假扮成宮中各個角色暗訪民情。有一天他假扮太監,被浣衣局一個小宮女纏上了。小宮女身嬌體軟,總對他撒嬌賣萌。小太監你長得真好看,我能抱抱你嗎?魏傾黑臉:敢?胳膊給你卸下來。然後小宮女親了他一口,魏傾:太監你都下得去嘴?小宮女安慰他:沒事呀你不要自卑,我不嫌棄。讓我做你的對食吧,我要讓整個浣衣局知道,你的衣服被我承包了。小宮女可可愛愛,魏傾原本只是看上人家的腦袋,後來迷戀她的吻,再後來,他想要這個人。有一天霜落發現了魏傾的秘密,抱著全部身家來找他:快跑吧,被人知道你是假太監要強行淨身的。魏傾:淨身之前,你再讓我親一下吧!霜落闖了禍,必須找個太監消災。遇見魏傾後,霜落心想:小太監脾氣好,長得好,我一定要拿下這個男人!後來,霜落發現魏傾是個假太監。比起生氣,她更害怕,于是連夜讓情郎跑路。她被親了一口,三個月後肚子大了。衆人幸災樂禍等著看霜落笑話,可是笑話沒看到,卻見帝王將霜落擁入懷中冷冷威脅:找死麽?妄議朕的皇後!備注:雙c,he,1v1治愈系沙雕小宮女x戲精有病狗皇帝文案已截圖存wb。原名《狗皇帝當太監的那些事》,只換文名其他沒變哦內容標簽: 宮廷侯爵 情有獨鐘 甜文 爽文搜索關鍵字:主角:霜落,魏傾 ┃ 配角:預收《殘疾大佬的續命丹》 ┃ 其它:預收《兩個病弱長命百歲了》一句話簡介:這個皇帝有點東西立意:保持勇敢,熱忱的心,終能收獲幸福
27.4萬字8 3237 -
完結320 章

我的惡犬我的馬,我想咋耍就咋耍
【大女主、女強、重生女將、女扮男裝、家國大義、架空正劇、亂世群像,感情線弱介意勿入】 她死在封候拜將,榮耀加身的那一年。 原來毫無怨恨,終登高位也會重生。 前世,她因為母親的一句話,肩負起家族重擔,女扮男裝成為宗延氏長子,隨父從軍。 卻因自己的年輕氣盛感情用事,以至阿妹慘死,叔伯累戰而亡。 皇權爭斗儲位紛爭,她愚昧無知錯信旁人令父親受挾,困戰致死。 她以親族血淚筑堤得以成長,攬兵奪權,殺伐一生,終得封候拜將榮耀加身!卻也留下終生遺憾。 一朝重生,重回十五歲初入軍營之時。 這一次她再無不甘,心甘情愿女扮男裝,為父,為家,為國而戰! 至此引無數賢才謀臣為其折腰,得萬千猛將部卒誓死追隨。 橫刀立馬,南征北戰,定江山,安天下! - 若說有什麼不同,大抵便是她的身邊始終站著一人,如那任由她驅使的惡犬,所向披靡忠心耿耿。 他從無奢求,追隨他的將軍戎馬一生,無名無分,不訴情愛,唯有忠誠二字。 很多年后將軍墓中,他肉身筑鐵立于棺前,生死相伴。 【殺伐果決的女將軍vs嗜殺瘋批的惡犬】
88.3萬字8 121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