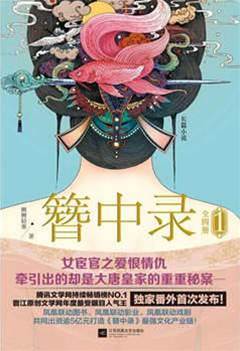《不辭春山》 暴雨
眼下形似乎也與那時差不多。
他滾的結著,啞著聲音道:“那公主現在要不要無恥之徒……”
他下兩個字,低了在耳邊喃喃道。衛蓁雪白的耳廓頃刻泛紅,偏偏他聲音本就好聽,此刻帶上了蠱人的意味,得人七魂六魄都麻。
他故伎重施,用方才一樣的法子問,衛蓁也無可躲,靨含,貝齒暗咬不肯出聲。
盛夏暴雨來勢洶洶,仿佛能席卷天地間一切。王宮上下都是氤氳的水汽,花叢中的花被雨水得奄奄一息,花瓣隨風飄落,楚楚可憐。
外頭忽然傳來敲門聲,衛蓁的頭皮一麻,轉過頭去張地看著門外。
“公主,您歇了嗎?”
衛蓁沒敢回話,耳畔的耳珰仍上下打在臉上。
空氣中濃彌漫,祁宴額上細汗有一滴落在的鼻梁上,衛蓁攥了下的床單,聽到外頭人道:“奴婢睡前想起來,殿中大鼎中冰塊沒換,公主若是直接睡了,夜裏怕是會熱醒,不知奴婢是否可以進來送冰?”
Advertisement
衛蓁不住,拍了拍上祁宴的肩膀,讓他到裏頭躺著去。
心頭一片窘迫,也不知涼蟬何時來的,方才自己有沒有發出不該發出的聲音,外頭暴雨雖然大,但未必能掩蓋住殿的響。
且這會地上散著袍,涼蟬若是闖進來,定然能發覺一切。
衛蓁也不知哪裏來的力氣,一把推開祁宴,撈起被子蓋在祁宴上。祁宴正是心激之時,被一下推開,那被子便蒙住了他的臉。
接著衛蓁的聲音響起:“涼、涼蟬,你先、先莫要進來……”竟然是連話都說得支離破碎。
“公主怎麽了?”外頭人疑道。
“我無事……你先走吧。”
可這嫵的聲線聽在外人耳中便是蓋彌彰。
許久之後,涼蟬應了一聲。那腳步聲逐漸遠去,衛蓁撥開被褥,面紅耳赤,“涼蟬會不會被發覺你?”
祁宴結滾了一下,長緩幾口氣:“明日一早,你問一問便知。是你侍不會多說什麽。”
Advertisement
眼睫上還沾著被他弄哭的淚珠,祁宴再次傾吻住。
次日天微亮,衛蓁聽到邊人的靜,微微睜開眼眸,窗外天還沉著,祁宴已經下榻撈起袍穿好。
昨夜蠟燭一直燒到極晚,衛蓁也才歇息沒一會,有氣無力道:“你要走了?”
祁宴嗯了一聲,走到床邊,了披在後的長發,“等會宮與侍衛該起了,那時我若想走便沒那麽容易,你先睡吧,屋裏我收拾一二。午後我去王殿找你,我們再見面。”
衛蓁聽到這話,連忙強撐著子爬起來。
殿自然是要收拾的,不止是地上、桌上、甚至窗邊都是一片狼藉,本不能示人。抱著被褥坐起來,看著祁宴收拾,神實在不支,很快又昏睡過去。
這一覺昏昏沉沉,便是連祁宴何時走的都沒有察覺,等再醒來,簾帳外傳來涼蟬的聲音:“公主,該起了。”
衛蓁了子,腰酸,實在爬不起來。
Advertisement
那綢被褥從肩膀落,出一截耀目雪白的,肩上布滿斑駁的痕跡。涼蟬完全愣住。
衛蓁索趴在榻上,無力道:“你去向父王道一聲,說是我今日有些累,上午便不去王殿陪他了。”
涼蟬收回視線,紅著臉應了一聲:“那奴婢這便去見大王。”
猜你喜歡
-
完結26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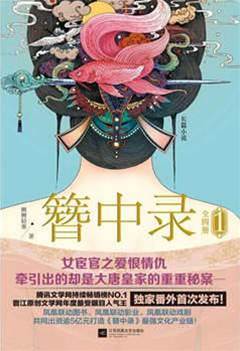
簪中錄
唐朝懿宗年間, 名聞天下的女探黃梓瑕,一夜之間從破案才女變為毒殺全家的兇手,成為海捕文書上各地捉拿的通緝犯。李舒白貴為皇子,卻身遭“鰥殘孤獨廢疾”的詛咒,難以脫身。皇帝指婚之時,準王妃卻形跡可疑,“鰥”的詛咒應驗在即。 黃梓瑕只身出逃到京城伸冤,途中陰錯陽差巧遇夔王李舒白。識破黃梓瑕身份的李舒白,答應幫黃梓瑕重新徹查家中血案,作為交換,則要她以王府小宦官的身份,去調查自己身邊的團團迷霧。 風起春燈暗,雨過流年傷。李舒白與黃梓瑕沿著斷斷續續的線索,走遍九州四海。江南塞北,宮廷荒村,在各種匪夷所思的懸案盡頭,真相足以傾覆整個大唐王朝……
79.6萬字8 18121 -
完結672 章

錦鯉王妃有空間
穿越后,蘇錦璃發現她全家都是反派,未來將不得善終。 父親是野蠻侯爺,兄長是未來權臣,未婚夫是克妻親王。 她就更厲害了,囂張跋扈,剛剛才打了女主親娘。 蘇錦璃默默檢查了自己的空間和異能,決定干票大的。 【甜寵】【蘇爽】【種田】【美食】【經商】【神醫】【基建】【打臉】
120.1萬字8 13350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