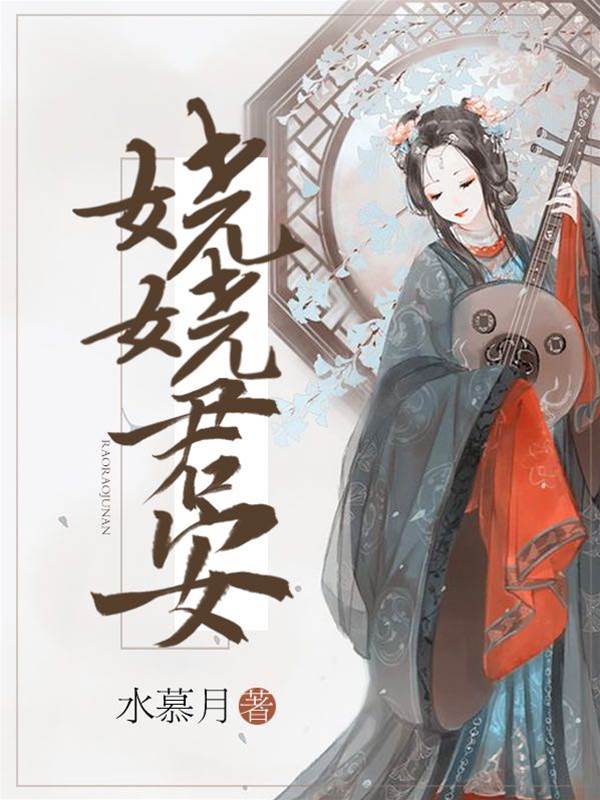《嫁給異族首領後》 第 54 章
第 54 章
母妃去世的時候,不過十二歲。這件事已經過了六年,但此時回想起,依然還記得母妃在一個夏季忽然變得孱弱。
楚妃的子雖然不算健壯,但也從來沒有那麽虛弱過,何況還懂得一些醫。
明明是夏季,正是溫暖炎熱的時候,卻經常患上風寒。
沈桑寧記得,那個溽熱的夏季,母妃竟前後染過三次風寒,幾乎一月一次。
皇宮的醫師來看,也看不出什麽原因,只道母妃第一次風寒便沒好全,才會反反複複。
那段時間,母妃反反複複閱讀醫書中的風寒一科,或許也非常迫切地想知道自己反複染的原因,只是秋季來的時候,便再也沒有力氣了。
秋季,一周的時間,玉京宮中樹木葉片盡黃,而楚妃也如同幹枯梢頭上搖搖墜的葉子,極快便只能躺在床上了。
往事歷歷在目,沈桑寧不覺將手握。這件事在今日由沈濯重新提起,顯然意指沈璟。
沈濯與沈桑寧是兄妹,看著沈桑寧的眼神,便知道已知道了答案,鄭重地點了點頭。
“是毒藥,來自西域的毒。所以,母妃翻遍大孟的醫書,也不可能知道生病的真實原因。”
“太後參與了這件事,沈璟同謀。”
沈桑寧形一晃,蘇勒連忙扶住了。
原本就消瘦的子,扶起來也是輕飄飄的,沈桑寧撐著旁邊的桌案站穩,又問:“為何?”
母妃是個溫和順的人,即便與太後有過齟齬,但這便能為太後殺人的原因麽?沈璟又為何要相幫?上一輩的恩怨,與他有什麽相幹?
種種錯綜複雜的線索出現在腦海,沈桑寧理了理,很快便得到了答案。
因為皇位。
沈濯年後一表人才,頗有人,楚妃醫出,并非世家大族,當年也差點躋貴妃之位,而沈桑寧,當年不到十二歲,便已獲封康樂公主,先帝的重視可見一斑。
Advertisement
太後可以容忍與楚妃的恩怨,但不能容忍自己正位中宮生下的兒子,被其他人謀奪了皇位。
即便後來沈璟已經繼承王位,這怨怒也從來沒有停止。
所以,先弒殺楚妃,再遣沈桑寧,而今沈璟對沈濯同樣虎視眈眈。
“阿寧。”沈濯道,“此次沈璟派我來,打算直接讓我死在河西。”
出征的時候被敵軍殺死,這個聲明太合合理,沒有人會懷疑。
更何況,沈濯先前已經來過一次河西洽談,此次出征再派他,太過正常。
“大孟說派駐大軍三萬,實則不到一萬。”蘇勒淡淡道,“他怕你真的贏了。”
“是啊。”沈濯攥拳頭,“我若死了,正合他意。我若沒死,無論是躊躇不前、帶兵抗旨、還是兵敗逃跑,我人在萬裏之外,自是由他隨意羅織罪名。”
這兩個男人說話間,沈桑寧看出來,他們早有聯絡。
恐怕這件事,他們也已經商量了許久了。
沈桑寧想起兄長每次寄過來的件,都經過蘇勒的手,或許,寄來的件裏還有給蘇勒的信,他留下了,其餘的原封不,給沈桑寧送去。
這兩個人,都沒和提起過這件事。
而此時,沈濯扶著的肩膀,盯著,表凝重認真:“阿寧,我的人已經圍住了玉京宮殿,只要我一聲令下,他們便會攻進去。”
他著沈桑寧,一字一句:“阿寧,你想我做皇帝嗎?”
一句話,他將世上最高的寶座,拖拽到沈桑寧的面前。
蘇勒也看著。
他表很平靜,又似乎帶著的鼓勵,似乎沈濯要去做皇帝這件事與他沒有半分關系,他在乎的只有沈桑寧一個人的意思。
沈桑寧看看沈濯,又看看蘇勒。
萬裏之外的玉京,最高的權力寶座,仿佛此刻就在一念之間。
Advertisement
“要。”最後點了點頭,“兄長,我要你做皇帝。”
那雙眸子裏竟也是相同的華彩,十分璀璨,沈濯憑空從向來單薄弱的妹妹上看到了掌權之人的氣魄,他怔愣了瞬間,隨後意識到,這氣魄來自蘇勒。
是蘇勒用這大半年的時間,一點點將沈桑寧上原本已經被深宮磨平的銳氣、氣度,重新養了出來。
沈濯還想說什麽,蘇勒將沈桑寧攬了過去,他連沈桑寧的兄長著肩膀的作都不大樂意,將人搶過來,只淡淡說了一句:“你該傳令了。”
-
命令從河西傳回,快馬加鞭,只需十日。
沈桑寧不知此時玉京宮中是怎樣一片兵荒馬,只知道在捷報傳來不久後,沈濯返回大孟,最要的關頭,沈濯必得親眼看著。
而這十日,沈桑寧和蘇勒一直在河西待著。
此不像西涼那麽冷,那麽偏,但沈桑寧已經習慣晚上抱著蘇勒睡,一晚不抱,便總覺得有些睡不著似的。
也從蘇勒的口中,知道了他們的計策原來始于上一次沈濯來河西,比沈桑寧想的更早。
最初,蘇勒并沒有相幫的意思,但逐漸他覺得沈濯比沈璟更適合做皇帝,更何況,沈濯還是沈桑寧的親兄長。
沈璟當面一套背地一套,虛與委蛇的做派,蘇勒早就厭煩不已。
幫沈濯奪走沈璟的王位,也是在向楚妃報恩。
蘇勒的手緩緩著沈桑寧的頭發,一邊親吻的耳垂,一邊問道:“我們何時回西涼?”
他迫不及待想帶回去。
沈桑寧卻不想,只說要在前線等著玉京傳來消息,才能放心返程。
蘇勒無法,只好在河西陪著。
除了河西駐紮軍之外,其餘的軍士們已經陸續返回了西涼,原本隨軍的烏烈、胡塞他們也都回去了,于是,西涼宮,竟然出現了一段時間的“君王不早朝”的況。
Advertisement
沈桑寧白日去看古麗他們練兵,與河西駐紮軍的其餘四名兵都了朋友,古麗還教箭,這下有充足的時間,古麗給了一把輕便些的弓,教沈桑寧慢慢學。
而晚間,則自然與蘇勒廝混在一,倒像是食髓知味,忽地明白了從前娜依在教時,冒出的那一句“或許王後日後也能會到其中妙”。
河西的春來得早。一日沈桑寧在看古麗他們拉練,閑來無事,竟注意到原本荒蕪的草地上似有約約的青。
驀然一驚,原來西域的青草依舊堅韌,不需要春雨,附近高山上融化的積雪依然能滋養它們。
玉京傳來的捷報也跟著河西的春天一起到達。
沈桑寧看過信,這才舒了一口氣。
政權疊,國家大事,很難傳到這樣一片西域的地界。實際上,這封信到沈桑寧手中的時候,沈濯已經在皇位上坐了十餘日。
蘇勒在不遠,冷著一張臉檢驗軍隊的訓練結果,大發慈悲地讓他們稍事休息,便去找沈桑寧。
一眼就看到沈桑寧手裏拿著信,表釋然。
蘇勒一直關注玉京向,前幾日便知道此事差不多了,卻只和沈桑寧旁敲側擊地暗示了兩句,想讓從一直掛念的兄長那裏得到第一手確定的消息。
“看到了?”他走過去,摟住的腰。
沈桑寧笑得很甜:“看到了。蘇勒,兄長讓我回玉京省親呢。”
沈濯登上皇位,理了一些掃尾之事,便想著讓沈桑寧回去省親。
蘇勒這個妹夫,沈濯已從一開始看他哪裏都不順眼,倒現在勉強能承認他是妹妹夫君的份。
“要去幾日?”蘇勒看似隨意地問。
他已經料到,沈璟被關押在天牢,朝堂上上下下都已被沈濯洗過一遍,再也沒有人會對沈桑寧省親這件事說一個不字,沈濯恐怕想讓沈桑寧在京中多留幾日。
Advertisement
“幾日不重要。”沈桑寧卻搖了搖頭,上前扶著他的手臂輕輕晃了晃,“夫君要陪我回去麽?”
這一聲夫君,得還有些害,似乎是沈桑寧第一次主這樣他。
盡管在床笫之間,他哄得沈桑寧滿面通紅地求饒時,偶爾 冒出過這兩個字,蘇勒聽見,眸暗了暗。
“我是西涼的王,如何能離開。”他還是堅定的。
沈桑寧想了想,忽然有了個主意,踮起腳,在蘇勒耳邊說了句話。
蘇勒也湊過去,俯下子,好讓不會太累。
只是那話還沒說完,沈桑寧的臉便已紅了起來,人一看便極為好奇那話的容。
極輕快地說完,沈桑寧捂住笑笑,往後退了一步。
蘇勒默了默,金的眸子似翻滾著,結也上下了:“使出這招也是沒用的,公主。”
沈桑寧看著他:“別忙著拒絕,我給你時間想一想。”
蘇勒的行力極強,當下沒有說話,在夜晚便提前把沈桑寧說的兌現了。
到後來,沈桑寧如同一尾被浪拍上岸的魚,氣不得,只能攀著男人的肩膀,承洶湧的一浪又一浪的沖擊。
帳中紅燭的搖晃直到半夜稍停。
沈桑寧已經累的不得了,偏蘇勒還神抖擻的樣子,眸子在黑暗中灼灼地盯著沈桑寧,出類似于野的本能的神。
最後,他理智回籠,還是依依不舍地放開了,幫理幹淨狼藉,躺在邊,手把小小的人都籠在懷裏。
或許是因為前線捷報頻傳,沈桑寧這段時間心事也了許多,吃飯更香了,蘇勒手了腰間,那裏的皮依然是瑩潤的,較之從前甚至還多了些。
只了一會兒,便被沈桑寧嗔著瞪了一眼,將他的手拿開。
沈桑寧正道:“蘇勒,你知道我為何想跟你一起回玉京嗎?”
猜你喜歡
-
完結182 章
屠戶家的小娘子
胡嬌彪悍,許清嘉文雅。 他們的婚後生活是這樣的: 胡嬌:「相公你說什麼?」 許清嘉:「……身為婦人就應恪守婦德……」 胡嬌:「相公我耳背,你近前來說……」緩緩舉起手中刀…… 許清嘉……許清嘉強擠出一抹笑來,「娘子……娘子言之有理!」 原本是馴婦記,最後變成了馴夫記。 胡嬌:「……」我啥都沒幹! 許清嘉:……娘子言之有理!」內心默默流淚:誰能告訴我,當大官還要附贈個怕老婆的屬性?這不是真的!
73.4萬字8 8602 -
連載439 章

夫人她每天都想和離
為報恩所娶的夫人沈聽瀾膽小無趣,白遠濯很不喜。 可最近他發現事情有些不對勁。 先是傾慕他的沈聽瀾提出要和離。再是同僚/下屬/上司們奇奇怪怪的言行: “白大人,貴夫人刻得一手好印章,您愛好印章,與您的夫人琴瑟和鳴,定得了不少好印章,不如與我們分享分享?” “白大人,下官一想到您每日都能享用您夫人做的美味佳肴,便好生羨慕。” “白愛卿,想不到你夫人繡藝如此精妙,那一副《南山僧佛會》太后很喜歡,病已大好!” 白遠濯:“……” 拿不出印章、沒吃過美食,更不知道沈聽瀾繡藝精妙的白遠濯決定去找沈聽瀾談談。 正好聽見沈聽瀾在與人唏噓白府虛度的那幾年:“辣雞愛情,毀我青春。” 白遠濯眉心狠狠的跳了一下。
80.1萬字8 16020 -
完結10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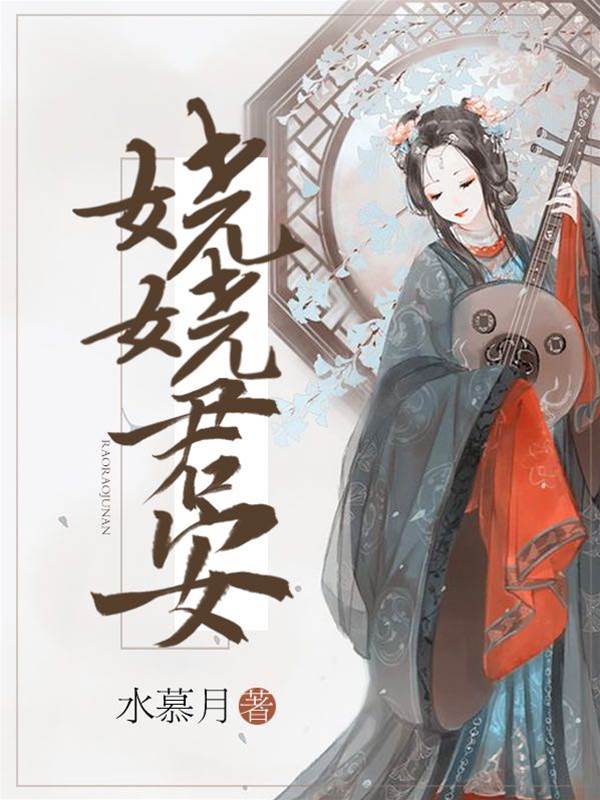
嬈嬈君安
原想著今生再無瓜葛,可那驚馬的剎那芳華間,一切又回到了起點,今生他耍了點小心機,在守護她的道路上,先插了隊,江山要,她也絕不放棄。說好的太子斷袖呢!怎麼動不動就要把自己撲倒?說好的太子殘暴呢!這整天獻溫情的又是誰?誰說東宮的鏡臺不好,那些美男子可賞心悅目了,什麼?東宮還可以在外麵開府,殿下求你了,臣妾可舍不得鏡臺了。
16.6萬字8 14823 -
完結69 章

暴君獨寵小宮女
帝王魏傾陰險狡詐,經常假扮成宮中各個角色暗訪民情。有一天他假扮太監,被浣衣局一個小宮女纏上了。 小宮女身嬌體軟,總對他撒嬌賣萌:小太監你長得真好看,我能抱抱你嗎? 魏傾黑臉:敢?胳膊給你卸下來。然後小宮女親了他一口,魏傾:太監你都下得去嘴? 小宮女安慰他:沒事呀你不要自卑,我不嫌棄。讓我做你的對食吧,我要讓整個浣衣局知道,你的衣服被我承包了。 小宮女可可愛愛,魏傾原本只是看上人家的腦袋,後來迷戀她的吻,再後來,他想要這個人。 有一天霜落髮現了魏傾的祕密,抱着全部身家來找他:快跑吧,被人知道你是假太監要強行淨身的。 魏傾:淨身之前,你再讓我親一下吧! 霜落闖了禍,必須找個太監消災。遇見魏傾後,霜落心想:小太監脾氣好,長得好,我一定要拿下這個男人! 後來,霜落髮現魏傾是個假太監。比起生氣,她更害怕,於是連夜讓情郎跑路。她被親了一口,三個月後肚子大了。 衆人幸災樂禍等着看霜落笑話,可是笑話沒看到,卻見帝王將霜落擁入懷中冷冷威脅:找死麼?妄議朕的皇后! 帝王魏傾陰險狡詐,經常假扮成宮中各個角色暗訪民情。有一天他假扮太監,被浣衣局一個小宮女纏上了。小宮女身嬌體軟,總對他撒嬌賣萌。小太監你長得真好看,我能抱抱你嗎?魏傾黑臉:敢?胳膊給你卸下來。然後小宮女親了他一口,魏傾:太監你都下得去嘴?小宮女安慰他:沒事呀你不要自卑,我不嫌棄。讓我做你的對食吧,我要讓整個浣衣局知道,你的衣服被我承包了。小宮女可可愛愛,魏傾原本只是看上人家的腦袋,後來迷戀她的吻,再後來,他想要這個人。有一天霜落發現了魏傾的秘密,抱著全部身家來找他:快跑吧,被人知道你是假太監要強行淨身的。魏傾:淨身之前,你再讓我親一下吧!霜落闖了禍,必須找個太監消災。遇見魏傾後,霜落心想:小太監脾氣好,長得好,我一定要拿下這個男人!後來,霜落發現魏傾是個假太監。比起生氣,她更害怕,于是連夜讓情郎跑路。她被親了一口,三個月後肚子大了。衆人幸災樂禍等著看霜落笑話,可是笑話沒看到,卻見帝王將霜落擁入懷中冷冷威脅:找死麽?妄議朕的皇後!備注:雙c,he,1v1治愈系沙雕小宮女x戲精有病狗皇帝文案已截圖存wb。原名《狗皇帝當太監的那些事》,只換文名其他沒變哦內容標簽: 宮廷侯爵 情有獨鐘 甜文 爽文搜索關鍵字:主角:霜落,魏傾 ┃ 配角:預收《殘疾大佬的續命丹》 ┃ 其它:預收《兩個病弱長命百歲了》一句話簡介:這個皇帝有點東西立意:保持勇敢,熱忱的心,終能收獲幸福
27.4萬字8 3237 -
完結320 章

我的惡犬我的馬,我想咋耍就咋耍
【大女主、女強、重生女將、女扮男裝、家國大義、架空正劇、亂世群像,感情線弱介意勿入】 她死在封候拜將,榮耀加身的那一年。 原來毫無怨恨,終登高位也會重生。 前世,她因為母親的一句話,肩負起家族重擔,女扮男裝成為宗延氏長子,隨父從軍。 卻因自己的年輕氣盛感情用事,以至阿妹慘死,叔伯累戰而亡。 皇權爭斗儲位紛爭,她愚昧無知錯信旁人令父親受挾,困戰致死。 她以親族血淚筑堤得以成長,攬兵奪權,殺伐一生,終得封候拜將榮耀加身!卻也留下終生遺憾。 一朝重生,重回十五歲初入軍營之時。 這一次她再無不甘,心甘情愿女扮男裝,為父,為家,為國而戰! 至此引無數賢才謀臣為其折腰,得萬千猛將部卒誓死追隨。 橫刀立馬,南征北戰,定江山,安天下! - 若說有什麼不同,大抵便是她的身邊始終站著一人,如那任由她驅使的惡犬,所向披靡忠心耿耿。 他從無奢求,追隨他的將軍戎馬一生,無名無分,不訴情愛,唯有忠誠二字。 很多年后將軍墓中,他肉身筑鐵立于棺前,生死相伴。 【殺伐果決的女將軍vs嗜殺瘋批的惡犬】
88.3萬字8 121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