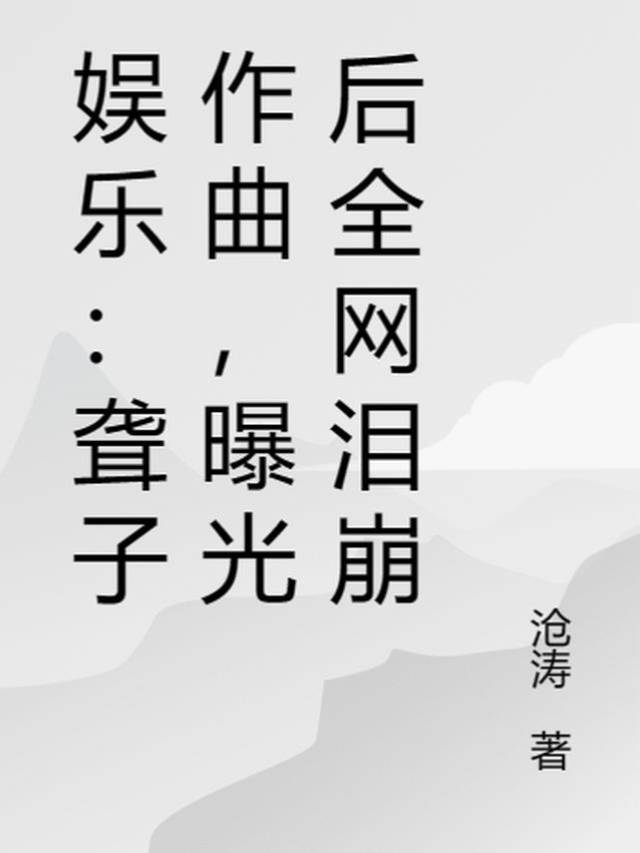《驚魂掠愛:夫君,很纏人》 第一百五十五章 陰墟邪局
“煤瓜,這個夢不好玩……我們回去了好不好?”
抱住伏在腰側的頸,手掌下面涌的暖流。
的腦袋驀然清醒過來,我手足無措地掂了掂手里的詭異武,惶恐得快要哭出來了。
剛才是被什麼鬼東西附了嗎?
黑睨了我一眼,獨自走上前幾步,然后躍上一座高臺又縱飛向八卦圖。
變大的煤瓜真是漂亮啊,像撕裂天幕的一道郁黑鮮亮的電弧,又流瀉漫天炫目的紫輝,從八卦暈的頂端傾泄而下。
我傻愣愣地著它,直至紫輝攏住四周又悄然地沒,本是巋然不的天地,突然鮮明地躍起來,就被誰松開了被摁停的時間之閥。
耳邊響起火把“噼啪”地乍響,冷寂的空氣里微微震起誦經的聲音,越來越宏亮,聲浪涌在四面八方無孔不。
空氣隨著這些唱變得灼熱起來,雙眼強烈地刺痛,煙霧就像變繩索地扼住了我的嚨。
擺在場地上的那些紅漆棺材在轟隆隆的巨響中劇烈地燃燒起來,然后持續潰塌,轟隆之聲不絕于耳,很快和綿綿不絕的誦化為一,像針尖穿刺進我脆弱的頭顱和心臟。
實在不了這般無休無盡的折磨,我抱著腦袋伏向地面,想躲避這場不知道什麼時候才能停休的炎火屠戮。
這夢真是太恐怖了,好想醒過來,繼續去找南城九傾那鬼家伙。
“起來好生看著!”頭上響起黑的命令。
它悄然降落在側,用刺刺的尾敲打著我的腦門。
“我不想看,煤瓜!”我揪住它的尾,苦的求,“你把我整得跟個蛇病似的也沒用。我跟百年前的南城家真的沒關系……我家世代姓柳,我爸媽是普通山民,我爺爺也是農民兼職幫人家挖墓,我太爺爺是看風水的假道士。我能把家里的十八代祖宗干嘛的都背給你聽。我柳妙正苗紅是柳家的親閨,從小到大沒有干過什麼傷天害理的事,更不要說什麼屠殺南城全家了!”
Advertisement
“愚笨不可救藥。”
黑從我手回回尾,不太爽地嘀咕了一句。
尼瑪,姐姐我不陪你玩了行不行?!扛起那把什麼幽剎鉤鐮,我想往后溜,卻被它暴地扯咬著擺往前扯。
“上來!吾須為你清除迷障!”
我氣悶,不過想想還是得指這畜生帶我回去,只得再次騎上背用手死攥住為它戴上的銀索。
那只晶亮的小表盤墜在健壯的前,有種萌萌的致。
黑抬足翹首,再一次縱騰躍而起,沖向煙云層迭塵起灰揚的暗空,懸停在八卦陣的另一側。
八卦陣懸下的線特別的溫暖潔凈,我迷地將手了過去,在指尖輕拂過。
“別靠近它!”黑怒斥,扭頸呲出雪亮的獠牙。
我只得尷尬地將目投向底下的沐火修羅場。
天地之間的烈火已將黑暗焚盡,留漫天漫地異樣的紅芒萬丈。
一焦骨從焚毀的棺木殘骸中掙扎破出,它們竭盡所能地長著自己油脂淋漓,黏連的手臂,向站在圓臺的蓑客發出尖銳的痛苦嘶鳴。
我渾止不住地戰栗,幾乎要扛不住肩頭的幽剎鉤鐮。
焦骨們在火中咆嘯,翻滾和蜷,將自己一點一點地損毀在蓑客毫不見憐憫的喃喃誦之中。
“這到底是什麼?”
我張地從攥著鏈索的舉下意識改為撕扯著頸上的。
黑煩躁地在空中掠出一圈暈,它梗扭起腦袋噴著氣,古怪地綻開一心滿意足的笑容。
“今朝能見識這至至邪的陣局,也算沒有白白被封印這百年。”
它如此說道,笑容愈見深沉,充滿著與我剛才一樣古怪的。
我到自己抖得厲害,抓在手心里的黑因汗而黏著一團。
底下的棺木里,有一焦骨正以扭曲的姿態趴在那里,驚慌失措的尖吼滾爬,與其他的沒什麼兩樣。
Advertisement
但我知道它有,它的骨上還懸掛著小半截還沒有被燒干凈的嫁,款式古樸花樣繁復,似乎比其他的更漂亮。
那些持鎬肅立的蓑客在火勢褪盡后,突然了。他們遵從著一種秩序拎起自己腳下的瓷罐,依次順著圓臺旁的木梯緩步而下,一直步火星紛舞的焚場,揮手里的鎬擊碎那些還在掙扎和嘶吼的焦骨們。
一下又一下,雪亮的鎬尖將其敲捶齏,又被小心翼翼地捧起裝那些瓷白的葬品。
作緩慢而細致,機械又規整,像已被重復過千萬次的嫻工序。
我看到一只圓潤的青花白瓷罐,已被慎重地放下。
鎬尖揮起直起直落,將那穿著繡花的焦骨鎬得碎屑飛濺,嘶吼剎那嘎然而止。
“你哭什麼?”
黑的問話像凜冽的臘月寒風拂面而過,干燥冰冷,潦草而暴地干了我面頰上的意。
在這烈焰焚炙的炎屠中,讓沸黏糊狀的神智又慢慢冷卻下來。
呃,估計鬼也不知道我這種時候為什麼要哭唧唧。
空氣中濃郁的焦味和腥持續裊裊蒸騰,像兩條正在糾合的蛇般不斷纏繞融匯,無聲無息地彌漫一詭異的香,沁進鼻腔侵心肺,又化為一方綿的絹,蒙附在將要被窒殺的五腑六臟上。
我扯手里攥著的銀鏈索,將伏倒在修長的頸背上,手臂展指向那一縷破碎,青煙迤邐的紅綢碎片。
“煤瓜,告訴我那是誰?!”
紅綢布片兒隨著鐵鎬不斷地砸落和揮起,被高高地勾掛在鎬尖,又隨揚起的力道遁而去,在火星和灰燼、焦骨與棺骸間曼妙地飛揚。
黑甩了甩頭頸,辟開煙灰流火踏穿熱霧煙燼,從空中如團云煙一樣輕盈降下,然后停駐在那被敲碎渣的焦骨旁。
Advertisement
所有揮鎬的蓑客正專心致志地把自己腳邊嘶吼掙扎的焦骨砸個碎,骨屑隨火星和灰燼散地彈濺。
沒有人朝我們瞥過一眼,盡管四周都是震破天際的囂鬧,悲嚎尖嘶中摻雜“呱咔呱咔”的焦骨破裂聲古怪而妖詭地震著這片修羅場。
我笨拙地躍下,站在火星紛飛的黑煙中窺著前方力不休的背影,在他掄起鐵鎬砸向焦黑的頭顱之時,我也忍不住高高揮起扛在肩上的幽剎鉤鐮,憤怒地砸向佝僂的背脊。
幽剎鉤鐮扎進有種微妙的黏滯,像將冰涼的雙手陷進溫暖的泥濘中,舒適得舍不得撤離。
我費勁地拔出武后,又忍不住揚起再砸落下去,帶著無比舒暢的和激昂。
黑不耐煩地踱著步,它的腳掌踏陷在細碎的骨屑堆之中,窸窸窣窣響得清脆悅耳。似乎在這種聽的節奏里,我的能更協調流暢地把控雙臂的力量,將手中的鎬一再揮出不可思議的暢快弧度,一次次重落擊下。
而這個承了數次鎬擊的始終沒有被擊趴伏地,他只是沉滯緩慢地轉過來。
幽剎鉤鐮又一次沉重落下時,不偏不移地擊向他寬大麻笠的中央,直直向下,一路拖曳出一條猩紅的裂。
我的手似乎已被癲狂的力量所控制,無法收力和停罷,只能任憑沉重的鐮尖順其而下,溜地扯裂笠沿蓑襟勾劃著皮筋直至肚臍之下,生生地卡在骨盆之上。
我聽見自己的里迸發出撕心裂肺的尖嚎,仿佛被鎬扯裂軀的人是自己,如同腳底下正繼續在被鎬碎的焦骨們。
幽剎鉤鐮終于從虛了力道的雙手中出,它牢牢地釘在綻裂的腹部,像只捕獲到獵的魚鉤。
寬笠和黑紗落,亮的黑發顯在躍的火中,連同那張帥破天際的俊。
Advertisement
南城九傾?!
他的臉使我更加不可抑制地繼續瘋狂嘶吼,并眼睜睜地瞪著他萎倒至雙膝跪地,淋漓的腹部頂著斜撐在地的鎬柄,像一塊頹敗的墳碑歪歪斜斜。
被驚駭到極致而迸發的尖嘶從頭源源不斷地噴涌而出,蓋過焦骨們的悲嘶和裂碎的合奏,在這片妖孽的場面里獨樹一幟的悠長嘹亮。
黑過腦袋呼出一口氣,萎倚在地的人和破碎的骸骨一起霎間碎崩為塵灰,飛揚進彌漫在天際的火星煙霧中。
我驀的頓住了哭吼,怔忡地看著一人一骨在眼前化灰而去。
好似半夜噩夢蘇醒后,轉頭見擺在床頭的水杯上還裊裊冒著熱氣,帶來濃重的彷徨和無力的虛。
這些,到底是真的還是假的?
“跟我來。”黑張叼起青花瓷罐,用尾端輕過我的擺。
我扛起武,愣愣地再次躍上它的脊背。
掌踩踏著咯咯作響的碎屑,緩步穿梭在一幕幕正在進行的某種儀式中。
焦骨們有條不紊地被鎬碎,然后被小心地捧起,倒罐中。這些青花白瓷罐宛如一朵朵盛開的睡蓮,在沖天的煉獄里平靜地綻放。
巡完整場,我終于發現不是所有的骸骨都會被鎬碎罐。
猜你喜歡
-
完結68 章

墜落于你
清初和職業選手顧祁澤在一起兩年。 他年少成名,萬人追捧,被譽為職業野神,清初當了他兩年的地下戀人,卻只是他無數曖昧的其中之一。 一切在無意撞見中破碎,朋友問他:“不是有清初了嗎,怎麼,這個也想收。” 彼時的顧祁澤靠在沙發里,眼瞼上挑,漫不經心:“談個女朋友而已,還真指望我要守身如玉?” 清初知道,他家里有錢,天之驕子看不上她;作為頂級海王,他魚塘里的妹妹數不勝數。 當頭一棒,清初徹底清醒。 她走了,顧祁澤和朋友輕嘲低笑:“她那樣的條件,找得到比我好的?” - S系列總決賽聯賽,清初作為空降播音到臺上大放異彩。 一夜之間,大家都在搜索那個叫清初的女孩,她爆紅了。 彼時的顧祁澤已然是全球總決賽TOP選手,面對臺上熟悉的女孩,他如遭重擊。 仿佛心臟瞬間被抓住,那是心動的感覺。 他知道,是他后悔了。 他徹底想挽回曾經的白月光。 然而來到她門口等兩小時抽了滿地煙頭后,門開了,一個溫柔少年渾身濕漉站在門口,剛洗完澡。 “你找誰?”少年聲線溫柔的問。 顧祁澤當頭一棒,渾身涼透。 此后,這位爺瘋了。他求饒,認錯,瘋狂彌補,決絕的時候甚至跪下求著她哭了一晚。 他說:“初初,我給你當備胎,你看我一眼好不好……” 追妻火葬場/浪子回頭/SC 排雷: 男主感情玩咖,非絕對1V1,有男二,文中所有男人潔,女主隨便。女主和男二后期在一起過會分手,不喜慎看。 注:游戲設定英雄聯盟,正文賽事非實際存在,游戲內所有戰隊等等設定含私設,勿與現實掛鉤,也非電競主線,啾咪。 一句話簡介:后悔嗎?后悔也沒用 立意:在逆境中前行,在逆境中成長
32.5萬字8 6534 -
完結1181 章

分手后,她藏起孕肚繼承億萬家產
葉芷萌當了五年替身,她藏起鋒芒,裝得溫柔乖順,極盡所能的滿足厲行淵所有的需求,卻不被珍惜。直到,厲行淵和財閥千金聯姻的消息傳來。乖順替身不演了,光速甩了渣男,藏起孕肚跑路。五年後,她搖身一變,成了千億財…
205.2萬字8.18 79263 -
連載12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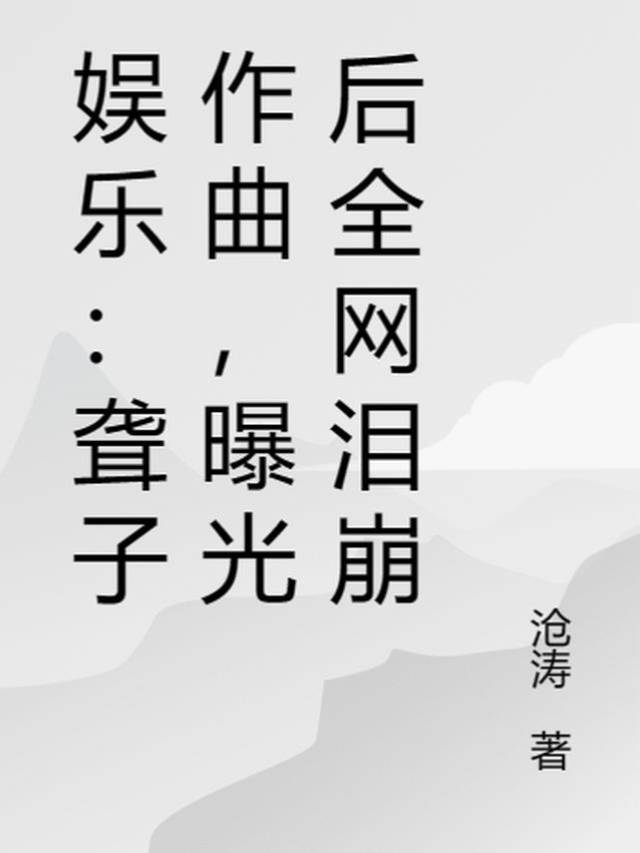
娛樂:聾子作曲,曝光後全網淚崩
微風小說網提供娛樂:聾子作曲,曝光後全網淚崩在線閱讀,娛樂:聾子作曲,曝光後全網淚崩由滄濤創作,娛樂:聾子作曲,曝光後全網淚崩最新章節及娛樂:聾子作曲,曝光後全網淚崩目錄在線無彈窗閱讀,看娛樂:聾子作曲,曝光後全網淚崩就上微風小說網。
23.8萬字8.18 5622 -
完結235 章

分手后,我渣頂流的事被全網曝光了
娛樂圈新晉小花姜云幼,被爆曾渣了頂流歌手宴涔,致其傷心退圈。分手視頻傳的沸沸揚揚。視頻中,曾紅極一時的天才歌手宴涔渾身濕透的站在雨里,拽著一個姜云幼的手,狼狽哀求:“幼幼,我們不分手好不好?”姜云幼只是冷漠的掰開他的手,決然轉身離去。一時間,全網嘩然。都在問她是不是渣了頂流。沒想到,姜云幼在社交平臺上公開回應:“是。”引得網友們罵聲一片。但下一秒,宴涔轉發了這條微博,還配文——“要不,再渣一次?”
40.8萬字8 1329 -
完結508 章

拋我殺我?蘇小姐腹黑歸來
前期小虐+重生+虐渣+爽文+女主超颯,復仇,手撕綠茶和渣男,仇家一個都不放過。爸爸媽媽不愛親生女兒(蘇鳳),卻對養女(蘇雪琳)視若己出。 綠茶+白蓮花妹妹怪會偽裝,搶走蘇鳳的家人和未婚夫. 蘇雪琳聯合未婚夫送她坐了13年的牢獄。 出獄歸來本想復仇,奈何再一次被蘇雪琳謀害,送入緬北,經歷一年半的地獄般折磨。 重生歸來,前世不堪的親情,這一世再也不奢望,她只有一件事,害她之人統統下地獄。
91.6萬字8 17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