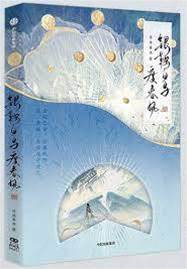《大周女官秦鳳藥,從棄兒到權利巔》 第993章 徐棠的心機
連翹沒回鄧家,假扮一個有錢的寡婦,住了京城最好的酒樓。
二樓一側全部包下來,廊道上鋪著羊地毯,不許閑人上樓,飯食可以送上來,還可以提前讓夥計給馬車。
一切都很愜意。
在這裏可以思考接下來自己的路要怎麽走。
對人生沒抱過奢,有什麽便會利用什麽,讓自己活得更自在些。
生在徐家,自小認得太多大家閨秀,觀察過許多人的生活。
待字閨中的一切都是虛幻的,那隻是人生中短短時,與自己最親的人在一起,算不得數。
出了閣和一個不相識的男人在一起度過餘生,那才是一個人真實生活的開始。
知道這關乎自己的將來,所以看得仔細。
之後,得出結論——
所有的人,下至出卑賤的養媳,上至高貴到皇後,都逃不開一種命運——
在男人的世界討生活。
不管們願意不願意,們都會或有形,或無形去討男子的歡心。
徐棠不願討任何人的歡心。
在看這一真相後,甚至討厭所有男人,包括自己家的親。
他們娶妻納妾生子,不管在外如何胡作非為,都可以被原諒。
而套在人上無形的繩索卻一直收得很。
就像現在,因為自家爺們胡來,已染上了病,隻是走出家門出來口氣,就要承外人的閑言碎語。
承來自不止男人,還有人的輕視,來自家人的迫。
“蠢貨。”靠窗而坐,眼睛看著酒樓後院的景,輕輕吐出兩個字。
Advertisement
這世道對人是殘酷的,人不得不躲在家庭的殼子裏求安穩,卻有人意識到這一點。
們對出一隻腳去試探“外麵”的同報著那麽大的惡意。
就像綺眉,徐棠挑挑眉,那個小丫頭鍾李嘉,可是男人,除了皮囊不同,在又有多大差別?
有一部分男人,心中本沒有,隻有算計。
人其實也好活。
徐棠早就看,坐在窗臺上,聽著自己的丫頭在外間為的熏香。
隻要像男人那樣思考、活著,人也能過得很好。
挑起角一笑,從行李中拿出自己的荷包,取出漂亮致的雕花小煙鍋,練地裝上草葉,推開窗,沐浴著微風與青草鮮香,愜意地吞雲吐霧。
對酒樓掌櫃暗示自己是寡婦,這雖是謊言,卻是的期待。
那個髒了的男人,不想要,可是不會自己離開的,要走他走。
不能付出這樣巨大的本,最後人財兩空。
徐棠,從來不吃虧。
沒天真過,嫁給姓鄧的是心思慮過的選擇。
經過打聽,得知鄧家雖是新貴,份差了點,比不得書香門第和老勳貴,但他家著實有錢!
富有的程度連國公徐家都能應了這門親事。
要知道徐家姑娘嫁人前,所選婿要經過徐家調查,人品、家世、家風、財富等。
鄧家別的短,能用財富來彌補,可想而知這財富得了徐家眼,是什麽樣的分量。
鄧家祖公很有智慧——鄧家有錢,知道的人卻不多。
他們將自己藏起來,才在一次又一次的災難中,將財富保住,越滾越大。
Advertisement
鄧家公子不敢覬覦徐家。這樣門第的姑娘幾乎不會正眼看他。
徐棠主選擇了他。
還打聽到,鄧公子早早沒了親娘,鄧家庶母當家,也就是說過去沒有親婆婆需要侍奉。
是這一點就贏了多嫁到別人家當媳婦的人。
有婆婆,進門就要做低伏小,低頭侍人。
其次,鄧公子兄弟雖多,嫡出就他一人。
商賈之家雖不那麽講究嫡出庶出,更看重個人能力手段。
但與國公府結親後就不一樣了。
會把大世家的規矩帶到鄧家去,好好約束鄧家人。
徐棠自認別的不會,但後宅爭鬥看得太多,早把醃味。
憑心而論,不想嫁人,並且知道這一點由不得,那不如先下手,自己為自己相看一門“合適”這個人的親事。
每個大家族,總會出一兩個紈絝,鄧家出了鄧公子。
他早早沒了母親,庶母教養得並不當心,父親因為思念妻子,對他頗為縱容。
不知是何緣故,養出一個沒心機的廢。
……
家家後宅都有爭鬥,鄧家也一樣。
隻是這種級別的爭鬥在徐棠看來有些孩子氣。
利用自己的份製鄧家後宅有著天然的優勢。
立的規矩、的風範、的儀態帶著國公府常年熏陶出“味道”。
鄧家是桿“秤”,徐棠就是鄧家的“秤砣”。
清楚僅憑自己國公小姐的份,管理鄧家,還會有人不服。
沒關係。本質上,人是在男人的世界中爭鬥——
隻需要鄧老爺站在背後。
Advertisement
他不是一直想貴族圈嗎?徐棠知道自己就是橋梁。
暗示過這一點後,甚至不需要徐家千金的份,也一樣製後宅。
有了鄧老爺的支持,徐棠很快就把後宅管理得有井井有條,服服帖帖。
可惜,太多人看不清這一點。
並非像旁人以為的,任、驚慌、逃回了娘家。
一切都在預料與策劃之。
隻有一個意外。
外房中夥計和丫頭小聲說話,片刻,丫頭來報——
李公子求見。
……
“連翹。”李嘉給徐棠行禮,對方隻是懶懶坐在寬大的窗臺上,擺垂落,斜著眼睛示意他不必多禮。
看上去很好,眼並沒在他上多停一下。
李嘉習慣了人的睹目,不管是千金小姐,還是市井子,誰見了他也會多看兩眼。
走在街上,他能到從轎廂中,商鋪裏投來的各種目。
無一不是欽慕與仰。
徐棠待他何止有些無禮,的眼神中已經告訴他,不拿他當回事。
他有瞬間分神再看徐棠,卻見眼中帶著水,悶聲道,“我是個被人嘲笑的出格之人,你何必過來瞧我,倒沾一閑話。”
所有頭發挽在一側前,瀑布似的,穿著家常,腳上穿著室底繡鞋,子灑在一邊,連羅都能看到。
李嘉心中突突直跳,不好奇羅向上的小是什麽樣的。
他轉過心思,心中罵自己不是君子。
猜你喜歡
-
完結121 章

攻心毒女:翻身王妃
可憐的李大小姐覺得自己上輩子一定做錯了什麼,這輩子才會遇到這麼多衰事。好在美人總是有英雄相救,她還遇到了一個面如冠玉的男子相救,這麼看來也不是衰到了極點哦? 不過偽善繼母是什麼情況?白蓮花一樣處心積慮想害死她的妹妹又是什麼情況?想害她?李大小姐露出一絲人獸無害的笑容,誰害誰還不一定呢!
46.5萬字8.18 19134 -
完結337 章

成為人生贏家的對照組[快穿]
她不是人生贏家,卻比人生贏家過的還好,你敢信?人生贏家歷經磨難,一生奮斗不息,終于成了別人羨慕的樣子。可她,吃吃喝喝,瀟灑又愜意,卻讓人生贏家羨慕嫉妒恨。在紅樓世界,她從備受忽視的庶女,成為眾人艷羨的貴夫人,作為人生贏家的嫡姐,也嫉妒她的人…
212.4萬字8 11147 -
完結686 章

神機毒妃只想寵反派
穿成狗血文女主,黎清玥開局就把三觀炸裂的狗男主丟進了池塘。為了遠離狗男主,轉頭她就跟大反派湊CP去了。原書中說大反派白髮血瞳,面貌醜陋,還不能人道,用來當擋箭牌就很完美。然而大反派畫風似乎不太對…… 她逼他吃噬心蠱,某人卻撒起嬌: “玥兒餵……” 她缺錢,某人指著一倉庫的財寶: “都是你的。” 她怕拿人手短,大反派笑得妖孽: “保護好本王,不僅這些,連本王的身子都歸你,如何?” 【1V1雙強,將互寵進行到底】
130.7萬字8.18 178083 -
完結224 章

吾妹千秋
照微隨母改嫁入祁家,祁家一對兄妹曾很不待見她。 她因性子頑劣桀驁,捱過兄長祁令瞻不少戒尺。 新婚不久天子暴斃,她成爲衆矢之的。 祁令瞻終於肯對她好一些,擁四歲太子即位,挾之以令諸侯;扶她做太后,跪呼娘娘千秋。 他們這對兄妹,權攝廟堂內外,位極無冕之王。 春時已至,擺脫了生死困境、日子越過越舒暢的照微,想起自己蹉跎二十歲,竟還是個姑娘。 曾經的竹馬今爲定北將軍,侍奉的宦官亦清秀可人,更有新科狀元賞心悅目,個個口恭體順。 照微心中起意,宣人夤夜入宮,對席長談。 宮燈熠熠,花影搖搖,照微手提金縷鞋,輕輕推開門。 卻見室內之人端坐太師椅間,旁邊擱着一把檀木戒尺。 她那已爲太傅、日理萬機的兄長,如幼時逮她偷偷出府一樣,在這裏守株待兔。 祁令瞻緩緩起身,握着戒尺朝她走來,似笑非笑。 “娘娘該不會以爲,臣這麼多年,都是在爲他人作嫁衣裳吧?”
34.6萬字8 3662 -
完結370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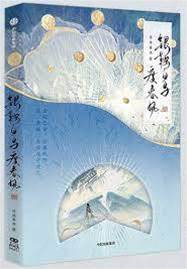
銀鞍白馬度春風
君主剛愎自用,昏庸無能,掩蓋在長安錦繡繁華之下的,是外戚當權,蟻蛀堤穴。 賢仁的太子備受猜忌,腐蠹之輩禍亂朝綱。身爲一國公主,受萬民奉養,亦可濟世救民,也當整頓朝綱。 世人只掃門前雪,我顧他人瓦上霜。這是一個公主奮鬥的故事,也是一羣少年奮鬥的故事。 ** 你該知道,她若掌皇權,與你便再無可能。 我知道。 你就不會,心有不甘嗎? 無妨,待我助她成一世功業,他日史書之上,我們的名字必相去不遠。如此,也算相守了。
55.4萬字8 191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