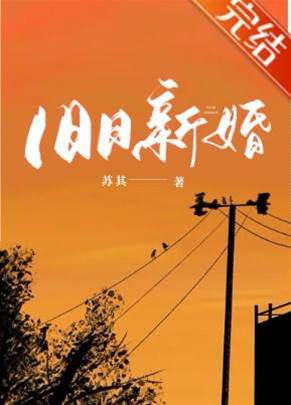《致小天使》 第97頁
加琳娜和阿納托利果然毫無保留地跟燕棠說起了宋郁小時候的事。
“他讓司機開車送他到莫斯科的公司樓下,要去找爸爸,結果前臺不認識他,把他攔了下來。”
加琳娜喝了一口紅酒:
“然后他在那里大哭著對那位前臺小姐說‘你知道我爸爸是誰嗎?’”
燕棠幾乎要笑岔氣。
“這是真的?”
宋郁無奈地說:“我不記得了。”
他聲稱沒有證據不能當真,阿納托利便在飯后拿出好幾本厚厚的相冊。
保姆將餐桌清理干凈,四個人圍坐在桌邊,老夫婦兩人戴上厚重的老花鏡,跟燕棠說起以前的事。
也許是宋郁在這里住得時間更久,相冊里他的照片更多,也有不兩兄弟的合照。
進青春期后,兩兄弟就越來越像了,但兒時期的差別還很大,尤其是宋郁將近一歲的時候,宋璟已經五歲了,由于父母都是高個子,他的個頭也比同齡人更高。
照片里,宋郁還在蹣跚學步階段,像個剛剛學會控制肢的小洋娃娃,宋璟站在弟弟邊,手里攥著跟一指寬的綁帶,另一頭纏繞在宋郁上。
“我媽媽讓他教我學走路,他就跟遛狗似地遛我。我要摔跤了,他就把繩子把我提起來……”
說起這件事,宋郁還是很無語。
除了孩子們的照片,也有年輕時的宋裕川和娜斯佳,包括兩個人訂婚到結婚,再到有了孩子之后合照。難怪兩個兒子長得好,這對夫妻年輕的時候也是男帥。
宋郁出其中一張照片,是他父母的訂婚照,看背景是在游上,娜斯佳的麗從來沒有變過,笑容活潑開朗,像手上的鉆石一樣耀眼。
這座鄉村別墅面積很大,二樓給他們休息的臥室已經清理出來。
Advertisement
當兩個人準備回臥室睡覺時,Маркиз跟在他們后,想要悄悄溜進臥室,然而在踏進房的前一秒被宋郁關在了門外。
他讓Маркиз去找它自己的朋友。
房間里的地面和墻壁是用不同的木材建,恍然像是回到了在西伯利亞度假的時候。
燕棠打開臺燈,用冷水沾巾給坐在床邊的宋郁冷敷膝蓋。
“還疼嗎?”將巾輕輕在他膝蓋上,“睡前記得把消炎藥吃了。”
“好多了。”
借著昏黃的燈,宋郁看著面前的人。
溫暖的線在室浮,將燕棠的眉眼染上一層朦朧的。
他忽然開口:“我媽媽對結婚的要求就是漂亮的大鉆石、熱鬧的派對、有趣的月。”
燕棠一愣,一抬頭就和他對上目。
“你呢?”宋郁問。
猝不及防被這個問題突襲,燕棠的大腦還沒轉過彎來:“我?我還沒想過。”
說到這里,聲音一頓,“現在說這個會不會——”
“我覺得你可以想一想。”宋郁接過手中的冰巾,將拉到邊坐下。
他轉而又問:“你喜歡Маркиз嗎?其實當年我外祖父很想直接養藪貓或者獰貓,甚至想過去收養小獅子,被我媽媽和外祖母強烈反對才作罷。我也很喜歡這類,之后如果有機會,我們可以去草原上看看……”
燕棠聽得很心,可惜兩個人的工作都十分繁忙,這個計劃在近期恐怕無法實現。
好在宋郁的左膝炎癥恢復很快,也許是外祖父母家靜養了兩天,遛遛貓逗逗狗,心放松,在周一的時候兩人就回到了家中,繼續投工作和生活。
日子一天天過去,在得到了文化基金的扶持投資之后,公司項目推進的效率高了許多,在年底時有兩個項目已經推進到上市階段。
Advertisement
而恰好是在這個時間,宋郁的訓練也卓有效,在和UFC方再次接洽后定下了復出賽安排,就在十二月中,地點在新加坡。
為了適應場地和提早進行賽前準備,宋郁提前兩周帶著團隊飛往新加坡,而燕棠恰好也回到北京跟進項目的最后階段。
兩人訂的是同一天的航班,一起坐車到機場才告別彼此。
“我一定盡早去陪你。”
燕棠拖著行李箱跟他保證。
按照項目時間表,可以在宋郁進行賽前水階段趕到,那時候也恰好是他最辛苦的時候。
這次是宋郁的復出賽,如果比賽順利,他需要連續打兩場top10排名賽,一場top5排名賽,接下來還有冠軍挑戰的資格賽,最后是冠軍賽。
由于傷病導致他在賽場上消失近兩年,這場比賽的熱度不算高,也并非主場,從某種程度上看,這反倒是一個很好的事,至在初期不會給宋郁太多的外界力。
——燕棠是這麼想的,所以對宋郁的比賽并不太擔心,經過這麼久的踏實訓練,加上以前的經驗,宋郁不可能不會功。
可沒想到這一年來,兩人幾乎形影不離,宋郁最大的問題在于分離焦慮。
兩個人在機場分開后不過半個小時,燕棠剛剛過完安檢,就收到了他發來的消息。
「我很想你。」
「小熊哭泣.jpg」
就連回到了北京,晚上在項目上和員工一起加班開會的時候,也會準時收到宋郁的消息。
“我接個電話。”
燕棠從會議室起,進單間辦公室,鎖好門后才打開手機,接通視頻請求。
新加坡和北京沒有時差,那邊也是晚上將近十二點。
屏幕一片漆黑,燕棠通過藍牙耳機聽見那邊響起窸窣的聲音,隨后見到那頭燈打開,宋郁放大的臉蛋填滿了整個屏幕,下睫都讓看得一清二楚。
Advertisement
“Kirill,我在辦公室。”
燕棠想到昨晚宋郁隔著屏幕對哼唧的樣子,臉頰還在發燙。
“現在不能做那種事。”嚴肅地說。
宋郁立刻反駁:“難道我找你只是為了那種事嗎?我很想你!”
這真的不能怪燕棠,他的力實在是太旺盛了,閑著無聊的時候需要發泄,太忙了神力大的時候也要發泄。
可還是好聲好氣地說:“是我錯怪你了,我可以陪你聊聊天。”
好在項目推進順利,第一天上市后的圖書銷售數據超乎預期,燕棠提早一天結束工作,飛新加坡的機票買在后天,中間一天便和恰好來北京出差的表姐程惠藝吃了個飯。
幾年過去了,表姐保養得當,借著來北京出差的時間,多停留一個周末在周邊旅游。
燕棠好奇問:“姐夫不會吵著要你回去嗎?”
“兩個人天天黏在一起會膩。”表姐喝了口茶,用過來人的語氣說,“小別勝新婚,距離產生。你跟你男朋友現在是同居狀態,也是一個道理。”
燕棠說:“還有這個說法呢?難道不是負距離產生嗎?”
表姐驚奇地看向,“你談個進步很大啊,小黃詞兒一套一套的。”
但表姐還是很誠懇地跟說,就算現在他們對彼此趣很強,為了可持續發展,平常還是要注意一點兒,比如不要經常在對方面前太多,保持神等等。
程惠藝比燕棠大好幾歲,燕棠每次覺得自己已經有許多BB囍TZ心得會了,拿到程惠藝面前總覺得不夠看。
所以信了表姐的話。
第二天,燕棠從樟宜機場出發,在下午三點時抵達宋郁住的酒店。
小譚已經等在酒店大堂,將宋郁的房卡給,用一種救世主來了的目看著,連連哀嘆:“明天開始賽前水,他已經好幾天沒吃碳水,從昨天開始就特別焦躁。”
Advertisement
新加坡的綠化程度非常高,生命力旺盛的隨可見,酒店主是白騎樓,充斥著濃濃的南洋氣息,讓燕棠有一種來度假的錯覺。
連續加班十天,累得暈頭轉向,到了房間后直接洗澡睡下。
這里環境好,空氣潤,四安靜,燕棠沉沉地睡到了晚上并開始做夢。
莫名其妙夢見Маркиз出現在房間里,跳上床,要爪子扇。
燕棠猛地睜眼,在漆黑對上一雙閃著澤的金棕瞳孔,下意識驚一聲。
床頭燈被打開,宋郁笑著說:“我又不會吃了你。”
他剛剛洗過澡,只在腰間圍了一層浴巾,上半沒穿服,頭發也是的。
由于臨近比賽期間重管理要求非常準,他的相較之前更加實,此刻在昏暗燈下別有一番的風味。
可現在是備賽期,不宜放縱,兩個人都清楚這一點。
燕棠在這時想到了臨行前表姐的告誡,忽然沉聲說:“把服穿上。”
話音剛落,就看見宋郁愣了。
“為什麼?”他聲音里有些不敢置信,“你怎麼會提出這種要求?”
燕棠把表姐那一套新鮮理論跟他轉述了一遍。
這還是宋郁第一次聽燕棠提起的表姐,他很不贊同那個觀點,甚至覺得這個想法很危險。
哦豁,小伙伴們如果覺得不錯,記得收藏網址 或推薦給朋友哦~拜托啦 (>.
猜你喜歡
-
完結582 章

BOSS主人,幫我充充電
一次失敗的手術,她意外變成了暗戀男神的私人機械人,且,還是情趣型的……顧安寶覺得她整個人生都要崩潰了!——天啊……我變成充氣娃娃了???主人在遠處沖她...
104.5萬字8 10421 -
完結523 章

可不可以爱上你
相愛三年,她曾許願能同他白頭偕老,相愛一生。卻不想,到頭來都隻是自己的一廂情願。直到後來,她重新擁有了他,卻不明白,為什麼心卻更痛了。
90.5萬字8 26921 -
完結134 章

離婚後,前妻頂級豪門身份曝光
【爽文 追妻火葬場 虐渣 萌寶 雙潔】 協議到期,慕冉甩下離婚協議瀟灑跑路。 誰知,剛離婚就不小心跟前夫哥擦槍走火。 轉眼前妻露出絕美容顏,馬甲掉不停。 鋼琴大師,金牌編劇,知名集團幕後老板……更是頂級豪門真千金,多重身份驚豔全球。 前夫哥纏上身,捏著慕冉下巴威脅:“你敢動肚子裏的寶寶,我打斷你的腿!” 然而白月光出現,他一張機票將懷有身孕的她送走。 飛機失事的新聞和真相同時傳來。 “戰總,夫人才是您找尋多年的白月光!” 戰景承徹底慌了。 再相遇,他卑微如泥自帶鍵盤跪在慕冉麵前,“老婆,我錯了!跟我回家複婚好不好?” 慕冉幹脆拒絕:“想複婚?不好意思,你不配!” 男人死皮賴臉,“孩子不能沒有爸爸。” 慕冉指了指身後大把的追求者,“這些都是我孩子爸爸的候選人,你連號都排不上。” 最後,戰景承站在臥室門口眼尾泛紅:“老婆,今晚能不能別讓我睡書房了?” “我要哄娃,別來沾邊!” “我也需要老婆哄睡。” 慕冉一個枕頭扔過去,“不要臉,滾!” 戰景承強勢擠進慕冉懷裏,化身粘人精,“要滾也是和老婆一起滾
23.7萬字8 68589 -
完結17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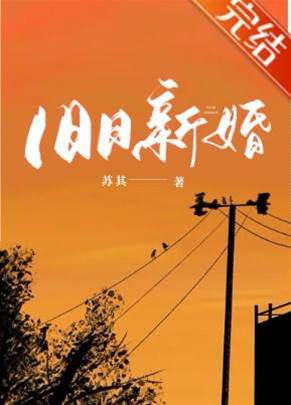
限定婚約/舊日新婚
秦南山是聞依最不喜歡的男人類型之一,刻板嚴肅,沒有喜好,沒有激情,像密林深處一潭死水,石頭扔進去,波瀾不驚。 一夜混亂,聞依更新認知,不全無可取之處。 一個月後,聞依看着試紙上兩道鮮明的紅槓,陷入沉思。 從懂事起,她從未想過結婚生子。 - 秦南山二十八歲,A大數學系副教授,完美主義,討厭意外,包括數學公式和人生。 聞依找上門時他一夜沒睡,逼着自己接受這個意外。 領證、辦婚禮、同居,他們被迫進入一段婚姻。 某個冬日深夜,聞依忽然想吃點酸的,換好衣服準備出門。 客廳裏穿着整齊加班的秦南山看向玄關被她踢亂的鞋子,眉心緊擰,耐着性子問:“去哪?” “想吃酸的。” “非吃不可?” “嗯。” 男人垂眸看錶,十二點零七分。 他心底輕嘆一聲,站起來,無奈道:“我去給你買。”
31萬字8.18 19943 -
完結78 章

救命!我家總裁又瘋又粘人
出獄第二天,云初強吻陌生帥大叔,成功脫險。出獄第三天,云初被送到慕家繼承人床上,為妹妹替嫁。 她一覺睡醒,竟成陌生帥大叔未婚妻! “你腿部有疾,還雙目失明?”她視線逐漸往下。 慕澤坐著輪椅,“陪我演,這件事你不準——” “退婚!我不嫁第三條腿不行的男人!” “......” 領證后,慕澤掐住云初的腰肢抵到墻角,不停逼問: “寶寶,滿意嗎?還不夠?” 云初欲哭無淚,“我錯了,大叔,你行你很行...” 兩人一起斗渣男,撕綠茶,破陰謀,一言不合送反派進局子,主打一個爽。 【一部女主出獄后升級打怪的救贖成長文,男主寵妻無下限。】
14.1萬字8 1117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