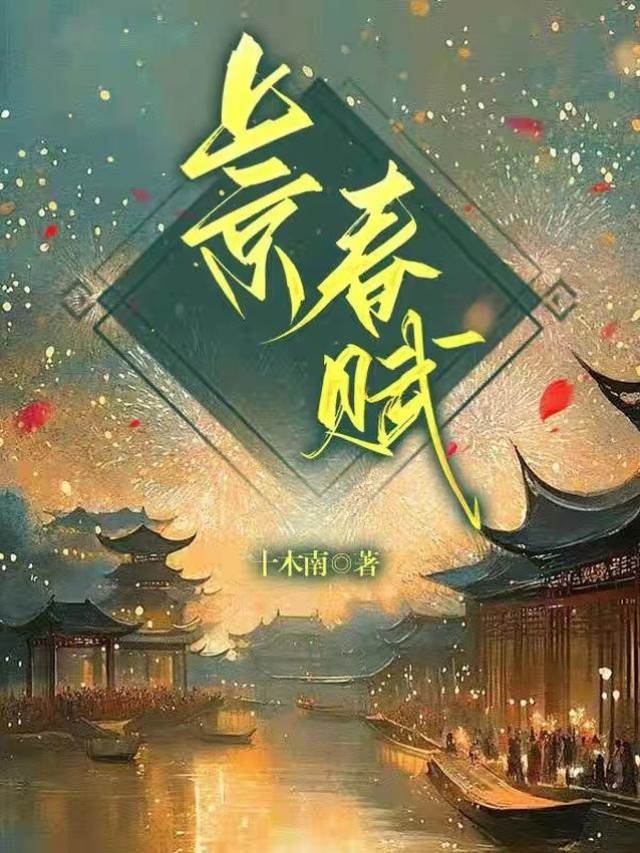《我與夫君天生一對》 第7頁
年輕,還能比不過嗓子?
所以這一嗓子可比蕭姑母清脆響亮多了,旁邊的壯婦都嚇得一個激靈,頭頂樹葉還應景地飄零下幾片。
蕭姑母雙目震,心臟怦怦。
完全沒料到這個崔氏居然敢在長輩面前大喊。
一抿,兩道刻痕明顯的法令紋讓面容變得更為嚴肅,也更威嚴。
高門世家蘊養出的氣度,頗威懾力,尋常人底氣不足,都不敢輕易與之對視。
崔蘭因卻睜大眼睛,不躲不避,口中道:“其一,蕭姑母不招呼就上門來,也未盡到長輩該有的禮節。其二,蕭姑母不給小輩時間整理儀容,催促見面,也未在意我儀容整不整。其三,站得直是我個子高顯得,姑母若覺得這樣不好,那不如我坐下聽講。”
崔蘭因在一眾建康郎里,的確算得上個子高挑,而蕭姑母生得矮小,足足比崔蘭因矮了大半個頭。
“你、你——”蕭姑母被三句話堵得啞口無言,怒火中燒。
這個崔氏!好狂妄!好無禮!
此生除了那個白眼狼前夫,還沒過這麼大的氣!過這麼重的辱。
“夫人!夫人!”
婦人著口進氣多出氣,哼哧哼哧大口吸氣,腔劇烈起伏,旁邊忠心的仆婦左右攙扶,被帶著一一同連連后退,就在這個時候,眾人頭上的樹冠又簌簌晃兩下,一道黑影忽然垂直砸下,好恰不巧好打在蕭姑母頭上,一汩鮮紅的順著的額頭蜿蜒流下。
“!出了!夫人!”仆婦尖。
蕭姑母捂著臉驚惶失措,慌喊:“,我的臉,我的……”
眼皮一翻,竟就這般昏闕過去。
“你膽敢藏匿兇設置陷阱謀害長輩!崔氏!你好大的膽子!”蕭姑母帶來的仆婦氣得不輕,手指沖著崔蘭因指指,恨不得用眼神瞪死。
Advertisement
“你、你就等著有人來收拾你吧!”
崔蘭因何其無辜。
地上摔得四分五裂的機關鳥可不是藏的,兩日前就把它送給了蕭臨。
至于這鳥怎麼飛到樹上又砸中蕭姑母,是一概不知啊!
/
“那位蕭氏出嫁前是蕭家最寵的小兒,十幾年前蕭家式微,夫婿收了一房又一房的小妾,寵妾滅妻,蕭氏為保家族面,一直容忍,直到蕭家東山再起,才由老太公做主,休夫回家。”
“所以老太公、老夫人都很心疼,蕭家上下也都敬重。”
崔蘭因晃著腳在床上拼湊那只損壞的機關鳥,陳媼的話左耳朵進右耳朵出。
“娘子,這次蕭家肯讓這位蕭娘子來指導您,也是誠心誠意想要您好的,可這把人砸暈了……事就大了!”陳媼痛心疾首,一一掰開分析,好崔蘭因明白現在事態急,危在旦夕,可不能再散漫悠閑,不當回事。
崔蘭因把腳一并,歪頭看著陳媼,“旁人說也就罷了,傅母你是母親給我的人,那天也是睜著眼睛看了個清楚,這只機關鳥——”崔蘭因舉起機關鳥,“是、自、己、掉、下、來、的!”
陳媼愁眉苦臉“哎呦”了聲,坐在床邊腳踏上,苦口婆心,“娘子啊,奴看見了有什麼用呢,們不會信我們的話。”
“那你的意思是,我往自己頭上砸一下,賠給,算我自己倒霉?”
陳媼眼皮狠狠一跳,握住機關鳥的尖,“娘子當心!為一老婦弄傷自己的臉,得不償失!”
陳媼再怎麼說,可心里還是明白,蕭氏再怎麼要,也比不上崔蘭因這張如花似玉的臉啊!
是萬萬舍不得崔蘭因傷害自己。
“都怪這只鳥,也不知怎麼就飛到樹上,害娘子有口難辯!”陳媼又把過錯轉到機關鳥上。
Advertisement
可惜機關鳥有口不識言,無法為己辯駁。
“不管如何,這鳥我給了長公子,他就有責任!”崔蘭因表面笑得甜,暗地里卻磨著后牙槽。
陳媼吃驚:“您……要找長公子告狀?”
“這怎麼能告狀,責任在誰總要理個清楚把?”
崔蘭因才不吃啞虧。
但崔蘭因還沒找上門,當日傍晚蕭臨就主過來了。
崔蘭因兩手叉腰準備開戰,蕭臨眉目溫和,主道歉:
“機關鳥是我留在樹下的,興許被野貓帶上了樹,又不小心掉了下來,傷了姑母,此中緣由我已經向母親和姑母解釋,與你無關。”
難怪雷聲大雨點小,那些囂張的仆婦端著一張要撕了的面孔急吼吼走,卻任由逍遙自在大半天,半點事也沒有。
原來是剛正不阿、明磊落的長公子沒有瞞過錯,把自己從這場“意外”中摘出去。
而蕭姑母再怎麼寵,蕭家也犯不著為一次意外責罰長公子。
崔蘭因悻悻放下雙手,“哦”了聲。
還以為至要和蕭臨辯駁幾回,才能把這冤案理清楚,誰曾想居然是以小人之心度
君子之腹了!
蕭臨主認錯。
這種覺很微妙,很復雜。
就像小土丘直面巍峨高山,高低立顯。
蕭臨緩了口氣,又道:“所以姑母傷不便來教你,這些時日我早中晚都會過來指點你,有什麼不明白的盡可問我。”
崔蘭因愣,重復道:“……早中晚?”
蕭臨點頭,詳細解釋:“早上寅初時、中午午正時、晚上戌正時。”
早上出門前,中午吃飯時,晚上下值后就是他能為崔蘭因出來的時間,如此也是他能夠想出最妥當的理方式。
崔蘭因眨了眨眼,居然還有此等好事?
Advertisement
笑盈盈問:“意思是,夫君早中晚都要來看我咯?”
郎的眼睛亮晶晶的,像是在期待著一些不會發生的事。
蕭臨頓了下,“你可以當是這麼一回事。”
第6章
景澄、景瀾兩人手里各捧了幾十本冊子,一腦壘到旁邊隔間書案上。
崔蘭因頭張,“那些是什麼?”
景澄站出來,十分驕傲地道:“回夫人的話,這都是建康城里有名有的世族家譜。”
不但有師承、姻親、故友等關系,重要人還配有畫,這可是蕭家花大功夫做出來的,別的地方還沒有呢!
崔蘭因想起來了,在崔家時,母親也曾經搬來了一大疊冊子,滿頁滿豆子大小的字,要背。
世族表面上以姓氏涇渭分明地劃分,但是幾百年來早在地底下猶如互相盤繞的樹,糾纏不清。
但親緣尚有遠近,姻親也難有長久。
自是一會張家李家親,一會王家謝家親,就好比沒有百日紅的花,也沒有固若湯池的聯姻。
“你今夜先看看,盡量把前面王、謝、蕭、裴幾家人記下來。”
“盡量?”
崔蘭因愕然,長公子是不清楚這四家就有多口人嗎?
蕭臨代完,再次托有事離開,徒留下滿臉郁悶的崔蘭因和滿臉喜的陳媼大眼瞪小眼。
“他是要我亡。”
“這是長公子關心您!”
崔蘭因有氣:“他又不是我父親也不是夫子,怎麼還給我布置功課了!”
“長公子有俊才,不知多人想以他為師都不能夠啊!”陳媼努力勸說道:“長公子如此繁忙還肯空教娘子,可見他對娘子還是有心的,如此一來,娘子更有機會與長公子頻頻接,早日圓房……”
Advertisement
崔蘭因這次把話聽進去了,點頭,“傅母,你說的極有道理。”
反正的目標又不是為家譜大全,能夠和蕭臨早中晚見面,還愁不能尋到他的破綻?
陳媼見崔蘭因開竅了,高興地連連點頭。
開竅的崔蘭因看也不看案上堆積的冊子,打著哈欠往床走,“不管了,頭疼,先睡了。”
陳媼隨著,憂道:“娘子,你好歹看幾眼,明日一早長公子還查驗功課,要是知道你一頁沒看,豈不是要生氣?”
“王家、裴家我不,謝家和蕭家我還能背出幾個,足夠應付差了。”
崔蘭因打定主意的事陳媼很難勸其回心轉意,主仆兩人拉扯了一陣,最后還是以陳媼放棄告終。
熄燈后,陳媼很快就在耳房睡著了,崔蘭因卻翻來覆去到半夜,好不容易才睡著。
寅時初,陳媼被外邊的靜驚醒,約聽見有人在喚,迷迷糊糊穿好,推門出去就見到蕭臨帶著景澄景瀾,主仆三人都穿得齊齊整整,神神。
年輕人就是神好啊。
陳媼越發覺自己年老力衰,尤其是這天一日冷過一天,早上不想起來。
陳媼走上前,行禮,“郎主稍等,奴這就去喊娘子起床。”
蕭臨問:“還未起麼?”
陳媼尷尬地笑了,“興許是昨夜看書晚了。”
蕭臨并沒起疑,讓陳媼進去醒崔蘭因。
只是陳媼進去沒多久,屋子里就傳來一聲“我不起!——”
哦豁,小伙伴們如果覺得不錯,記得收藏網址 或推薦給朋友哦~拜托啦 (>.
猜你喜歡
-
連載47 章
情絲
我是無情道中多情人
53.8萬字8 9569 -
完結268 章

死後第一天,乖戾質子被我親懵了
【雙潔 甜寵 雙重生 宮鬥宅鬥】 【絕美嬌軟五公主×陰鷙病嬌攝政王】 前世,她國破家亡,又被那個陰鷙病嬌的攝政王困在身邊整整兩年。 一朝重生十年前,她依舊是那個金枝玉葉的五公主,而他不過是卑微質子,被她踩在腳下。 西楚國尚未國破,她的親人母後尚在,一切都沒來得及發生…… 看著曾被自己欺負的慘兮兮的小質子,楚芊芊悔不當初,開始拚命補救。 好吃的都給他。 好玩的送給他。 誰敢欺負他,她就砍對方的腦袋! 誰料病嬌小質子早已懷恨在心,表麵對她乖巧順從的像個小奶狗,結果暗戳戳的想要她的命。 少年阿焰:“公主殿下,你喂我一顆毒藥,我喂你一隻蠱蟲,很公平吧!” 然而此時的少年並不知道,上一世的他早已對小公主情根深種,那位已然稱霸天下的攝政王,豁出命也想要給她幸福。 攝政王對不爭氣的少年自己氣的咬牙切齒:“你要是不行換我來!”
48.9萬字8.33 15703 -
完結150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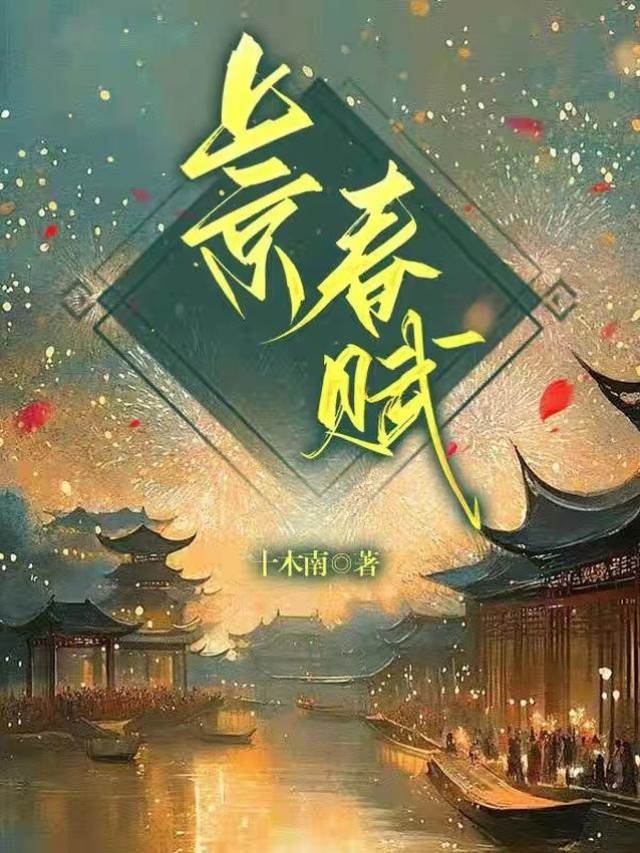
上京春賦
【純古言非重生 真蓄謀已久 半強取豪奪 偏愛撩寵 情感拉扯】(已完結,本書原書名:《上京春賦》)【甜寵雙潔:嬌軟果敢小郡主VS陰鷙瘋批大權臣】一場陰謀,陌鳶父兄鋃鐺入獄,生死落入大鄴第一權相硯憬琛之手。為救父兄,陌鳶入了相府,卻不曾想傳聞陰鷙狠厲的硯相,卻是光風霽月的矜貴模樣。好話說盡,硯憬琛也未抬頭看她一眼。“還請硯相明示,如何才能幫我父兄昭雪?”硯憬琛終於放下手中朱筆,清冷的漆眸沉沉睥著她,悠悠吐出四個字:“臥榻冬寒……”陌鳶來相府之前,想過很多種可能。唯獨沒想過會成為硯憬琛榻上之人。隻因素聞,硯憬琛寡情淡性,不近女色。清軟的嗓音帶著絲壓抑的哭腔: “願為硯相,暖榻溫身。”硯憬琛有些意外地看向陌鳶,忽然低低地笑了。他還以為小郡主會哭呢。有點可惜,不過來日方長,畢竟兩年他都等了。*** 兩年前,他第一次見到陌鳶,便生了占有之心。拆她竹馬,待她及笄,盼她入京,肖想兩年。如今人就在眼前,又豈能輕易放過。硯憬琛揚了揚唇線,深邃的漆眸幾息之間,翻湧無數深意。
25.6萬字8 299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