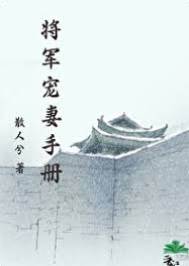《攀高枝》 第1卷 第105章 作案手法
陳寶香手抓住了他的袖。
形一滯,張知序眼睫都了,以為終于愿意解釋清楚,亦或者道歉。
結果這人開口,說的卻是:“帶我一起吧?我自己沒法離開這重重包圍。”
“……”
張知序回眸,眼里都泛起了紅:“我不將你出去就已經算是仁慈。”
“你方才也說了,咱們目的一致,目標也相同。”嬉皮笑臉,“沒理由將我出去的呀。”
“試試看。”他面無表地看向抓自己袖的手,“再攀扯,我立馬人。”
陳寶香苦著臉回了手。
早知道就不那麼耿直地問什麼答什麼了,要坦白也好歹能逃離四神廟之后。
門被他摔上,很大的一聲,足以顯出他的生氣程度。
陳寶香垂眼穿上他留下的外袍,坐在床邊有些出神,不知在想什麼。
剛關上的門沒一會兒就又被打開了。
驟然抬眼,卻發現是謝蘭亭。
他像是被誰推進來的,往門外看了一眼,又神復雜地關上門來看。
旁人方才也許沒看見兇手逃向了何,謝蘭亭一直在窗邊盯著,顯然知道是怎麼回事。
“你是怎麼殺得了陸守淮的?”他進門,不問別的,先問案子。
陳寶香咧笑:“大人在說什麼,我聽不明白。”
“別裝蒜,今日你能出現在這里,兇手的份就已經是板上釘釘。”
“哦?”挑眉,“我只是跟你們一樣來看熱鬧,就兇手了?”
“你還想狡辯?”
“陳某很喜歡大人的一句話:凡事要講證據。”意味深長地看著這人,“謝大人,你有什麼證據能證明我是來行兇的,又有什麼證據證明今日的刺客就一定跟殺害陸守淮的刺客是同一個人?”
Advertisement
謝蘭亭擰了眉頭。
面前的陳寶香好像換了一個人,從天真無辜,變得囂張又無賴。
——亦或者這才是的本,聰慧如張知序,也了掌上的玩。
謝蘭亭搖頭,還是自顧自地分析:“你若要殺人,就只有半個時辰的機會,可半個時辰是如何能從淮口驛站往返的?”
陳寶香面不變,仍舊笑盈盈的:“想知道真相?做個易如何。”
“什麼易?”
“帶我離開此,我告訴你這是怎麼做到的。”
“……”謝蘭亭看了一眼門外,又看了一眼面前這人,好笑又無奈地點頭。
·
護衛將四神廟里里外外搜了個遍,凡是拿不出請帖的,都被盤問了一番。
謝蘭亭坐在馬車上,納悶地道:“你跟卿說什麼了,他突然生這麼大的氣。”
陳寶香皮笑不笑:“還用說嗎。”
即使不知道兩人之間那些過往,也該知道張知序撞破了的謊言。
“現在已經離開了四神廟的范圍。”謝蘭亭看著,“你該說說你的作案手法和殺機了。”
陳寶香扯了扯上裹著的被子,沒好氣地道:“你再這般沒有證據地下定論,我就去衙門里告你污蔑朝廷命。”
自己有職就是有底氣,這話說得擲地有聲,哪怕是謝蘭亭,也只能吞回去話,無奈地道:“行,那你幫我分析分析,兇手是怎麼做到的。”
“簡單。只需兩包迷藥,將押送罪犯的差役迷倒在半路,再讓人把他們扔去淮口驛站。”
陳寶香懶散地道,“如此一來,他們自會說是將人送到驛站之后才暈的,便不用失職之罰。”
謝蘭亭皺眉:“那驛站送出的接執報?”
Advertisement
“五十兩一張。”陳寶香托著下笑,“大人,咱們大盛早從上爛了,什麼章程規矩,只要有錢有權,沒什麼作不得假。”
謝蘭亭被震住了,手里的折扇都險些沒拿穩:“他們敢這麼做,被發現了是要掉腦袋的。”
“是啊,可是大人,律法上說會掉腦袋的事還麼?”敲了敲面前的矮桌,“侵占良田、戕害百姓,哪一條不掉腦袋呢。”
律法不嚴格施行,自然就會讓人心生僥幸。
謝蘭亭怔怔地看著,突然反應過來:“當時在小院,你就是在對判決結果不滿,所以才會問出那句話。”
一條命還不夠嗎?——言下之意,陸守淮憑什麼在犯了那麼多死罪之后還能活命。
陳寶香微笑:“在下聽不懂大人在說什麼。”
“我也想不明白。”謝蘭亭定定地看著,“你是在為民請命?”
“這個由頭好。”嘖了一聲,“說不定能說服卿,讓他別生氣了。”
不是嗎?
謝蘭亭看著的反應,又陷了沉思。
若不是為民請命,陳寶香到底還有什麼非殺陸守淮不可的理由?
車廂里安靜下來,只剩下車軸骨碌骨碌的靜。
趙懷珠坐在外頭的車轅上,時不時擔心地往后頭看一眼。
今日刺殺不,反而暴了大人,很擔心張知序謝蘭亭這些人會和大人為難。
但陳寶香很樂觀,回屋去收拾了些細,一腦地塞到了懷里:“咱們有很長一段時日無法再行,趁著天氣好,你帶含笑去附近的州縣游玩一番吧。”
“我不走。”意識到了什麼,一把將包袱推開,“你在上京,我就跟你一起留在上京,萬一張大人怪罪下來,我也好……”
Advertisement
“怪罪什麼啊怪罪,這才多大點事。”陳寶香不以為意,“張知序沒你想的那麼小氣,好歹有些相的誼在,我又沒礙他的事,他還能把我拎出去砍了不?”
“可是……”
“沒有可是,別人陪著含笑我哪里放心,這里外里的就你們幾位師兄師姐是自己人。”將包袱塞回懷里,神輕松地道,“我雇了車,你們待會兒就走。”
趙懷珠無從反駁,只頻頻回頭打量。
小師妹看起來心不錯,角帶著笑,腳步也輕快,似乎今日當真不是什麼大事。
難不那張家二公子真的對小師妹深種,哪怕發現被欺騙,也會選擇原諒?
猜你喜歡
-
完結556 章
全家去逃荒,她從懷里掏出一口泉(孟青蘿燕修竹)
特種兵兵王孟青羅解救人質時被壞人一枚炸彈給炸飛上了天。一睜眼發現自己穿在古代農女孟青蘿身上,還是拖家帶口的逃荒路上。天道巴巴是想坑死她嗎?不慌,不慌,空間在身,銀針在手。養兩個包子,還在話下?傳說中“短命鬼”燕王世子快馬加鞭追出京城,攔在孟青羅馬車面前耍賴:阿蘿,要走也要帶上我。滾!我會給阿蘿端茶捏背洗腳暖床……馬車廂內齊刷刷的伸出兩個小腦袋:幼稚!以為耍賴他們
102.1萬字8 186538 -
完結171 章

權臣的瘦馬通房
阿鳶是揚州出了名的瘦馬,生得玉骨冰肌,豔若桃李,一顰一笑便勾人心魄,後來賣進安寧侯府,被衛老夫人看中,指給安寧侯世子做了通房。 安寧侯世子衛循爲人清冷,性子淡漠,平生最恨寵妾滅妻,將阿鳶收進後院,卻極少踏進她的院子。 阿鳶自知身份卑微,不敢奢求太多,小心伺候着主子。 時間久了,衛循便看出自家小通房最是個乖巧聽話的,心裏也生出幾分憐惜,許她世子夫人進門後斷了避子湯,生個孩子。 阿鳶表面歡喜的答應,心裏卻始終繃了根弦。 直到未來世子夫人突然發難,讓她薄衣跪在雪地裏三個時辰,阿鳶心頭的弦終於斷了。 她要逃! 起初衛循以爲阿鳶就是個玩意兒,等娶了正妻,許她個名分安穩養在後院,並不需要多費心。 後來阿鳶的死訊傳來,衛循生生吐出一口心頭血,心口像破了個大洞,空了......
29.7萬字8.33 30589 -
完結11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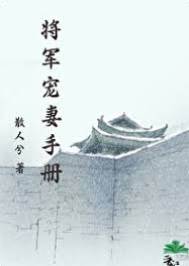
將軍寵妻手冊
雲府長女玉貌清姿,嬌美動人,春宴上一曲陽春白雪豔驚四座,名動京城。及笄之年,上門求娶的踏破了門檻。 可惜雲父眼高,通通婉拒。 衆人皆好奇究竟誰才能娶到這個玉人。 後來陽州大勝,洛家軍凱旋迴京那日,一道賜婚聖旨敲開雲府大門。 貌美如花的嬌娘子竟是要配傳聞中無心無情、滿手血污的冷面戰神。 全京譁然。 “洛少將軍雖戰無不勝,可不解風情,還常年征戰不歸家,嫁過去定是要守活寡。” “聽聞少將軍生得虎背熊腰異常兇狠,啼哭小兒見了都當場變乖,雲姑娘這般柔弱只怕是……嘖嘖。” “呵,再美有何用,嫁得不還是不如我們好。” “蹉跎一年,這京城第一美人的位子怕是就要換人了。” 雲父也拍腿懊悔不已。 若知如此,他就不該捨不得,早早應了章國公家的提親,哪至於讓愛女淪落至此。 盛和七年,京城裏有人失意,有人唏噓,還有人幸災樂禍等着看好戲。 直至翌年花燈節。 衆人再見那位小娘子,卻不是預料中的清瘦哀苦模樣。雖已爲人婦,卻半分美貌不減,妙姿豐腴,眉目如畫,像謫仙般美得脫俗,細看還多了些韻味。 再瞧那守在她身旁寸步不離的俊美年輕公子。 雖眉眼含霜,冷面不近人情,可處處將人護得仔細。怕她摔着,怕她碰着,又怕她無聊乏悶,惹得周旁陣陣豔羨。 衆人正問那公子是何人,只聽得美婦人低眉垂眼嬌嬌喊了聲:“夫君。”
17萬字8.33 56909 -
完結195 章

嫡姐逼我做側房,重生二嫁上龍床
衛南熏一睜眼回到了及笄這一年。按照記憶她這個庶女會因長相出眾,被太子相中,成為嫡姐陪嫁的滕妾入了東宮。 她看似得寵,夜夜侍寢。可太子只將她視作玩物折騰毫無憐惜,更是被嫡姐當做爭寵的工具。 她死了在出嫁第四年的秋夜,無人問津死狀可怖。 重活一回,她要離這些人事遠遠的,回鄉下老宅悠閑度日,偶然間救了個窮教書先生。 她為他治傷,他教她讀書識字,趕走附近的潑皮混子,兩人暗生情愫,她更是動了讓他入贅的心思。 好不容易攢了十錠銀元寶做聘禮,準備與對方談親事,前世的夫婿卻帶人尋到,她慌忙將人護在身后。 不料那個向來眼高于頂,從未將她當人看的太子,朝她身后的人跪了下來:“侄兒來接皇叔父回宮。” 衛南熏:??? 等等,我這十錠元寶是不是不太夠啊……
43.7萬字8 12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