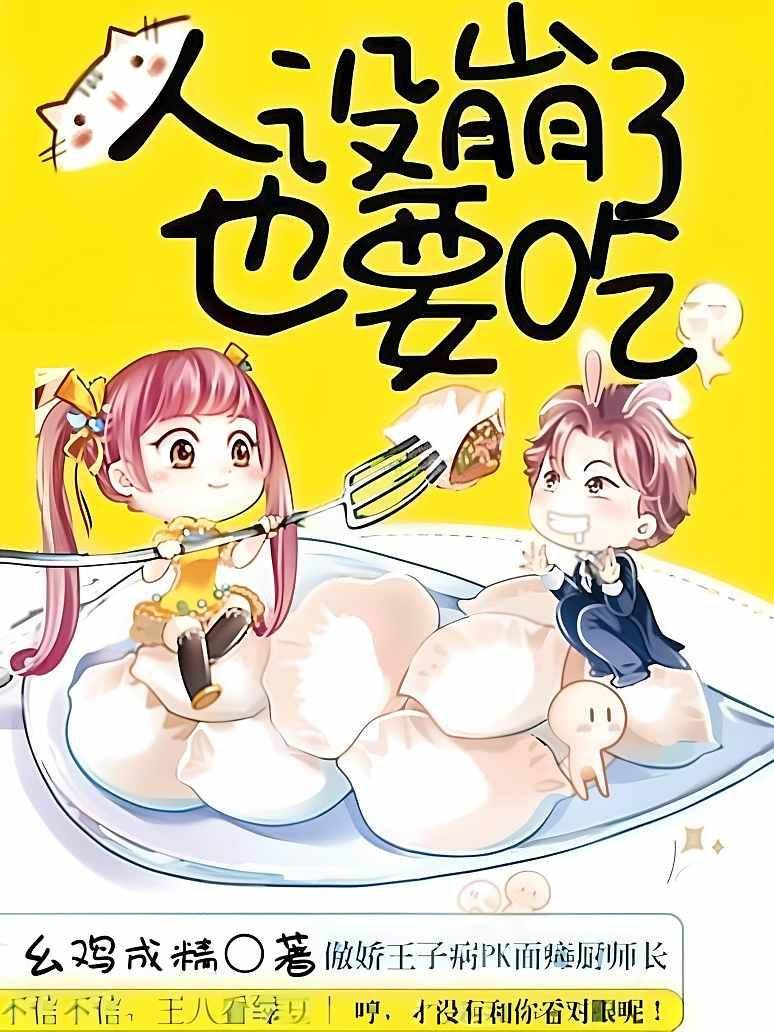《誘他瘋寵》 第1卷 第36章 高高舉起,輕輕放下
剛剛那種況,孤立無援,無人心疼。
像是一只倔強的孤,在用盡全力維護著自己最后的面。
艱難,委屈,失,或許還有其它……顧一笙說不出來,只是覺得難。
“還說不敢。你要是再敢點,這房頂是不是就得給你掀了?”
厲南城坐了下來,手著的小臉,哄,又仔細的看,“過敏的癥狀好了不,你這幾天先住著,等徹底好了再出院。”
皮向來白,卻是被這一次過敏都弄的幾乎毀了容。
小紅人就是。
臉上都是紅疙瘩,一片一片的,看起來有點嚇人。
厲南城不嫌棄,捉著的下,著一只手,用力的親了親,然后又抱在懷里哄:“好了,是我不對,沒有第一時間護你。可你也得知道,在人前的時候,你不要跟比。該怎麼做,我心里有數。”
顧一笙心中一酸,突然就更生氣了。
用力推他:“我也沒想跟比!是你不讓我走的!厲南城,你放手,讓我走!我們以后井水不犯河水,也省得我總是去礙的眼。礙了的眼,惹得你心疼,回來又來找我麻煩!”
Advertisement
突然這麼說,厲南城也快哄不住了,頭疼的很:“別想。你是我的人,一天是,一輩子都是,離開了我,你能去哪兒?”
顧一笙不管。
這個男人懷里有程安雅的氣息,聞著想吐:“那你先放開我。你上有的香水味,我聞著不舒服!”
厲南城一頓,慢慢放開了他:“你倒是生了一只狗鼻子。”
這個男人,手段是厲害,氣場也人。
但他耐心哄的時候,寵著的時候也居多,顧一笙偶爾也會很放肆。
比如現在,趁著他對心有歉意,可勁的折騰:“反正我不管,你不洗澡,就別抱我。”
使起小子,厲南城的眉眼漸漸冷了下來,看到了,也不折騰了,然后又躺下,繼續背對著他,不理他。
厲南城想,他還是太慣著了。
先冷靜一段時間吧!
沒說話,起走了。
醫院洗不了澡,他直接回了一號公館。
高宇在樓下等他,將鑒定結果遞過去:“顧書的服,還有衡山居的沙發座套,以及你的服上,都有明顯的化學纖維殘留。其中,顧書后來換下的那件黑禮服上,殘留的痕跡最多。至于最初的天青裝,倒是沒檢出問題。”
Advertisement
這是加急查出來的結果。
厲南城目沉下。
他剛洗了澡,頭發還是的,材拔,也極有看頭,高宇只瞧了一眼,便將視線轉向了別。
男人拿了報告,看了會兒便放在桌上,點了煙,狠狠的吐出一大口。
高宇問:“怎麼置?”
結果已經很明顯了。
厲南城沒說話,手中腥紅的煙,點在資料上方,寫著‘禮服’二字的地方,被灼得瞬間焦黑。
高宇看了眼,等待下文。
“這件禮服的出,找出來,把人帶過來。”
高宇明白了,這是要高高舉起,輕輕放下了。
不由嘆一聲。
到底委屈的,還是顧書。
“后天的拍賣會,多準備幾套珠寶,給顧書。”厲南城把燒到手指的煙徹底按滅,一雙目晦暗不清。
男人,做到他這個位置的時候,無論是眼,還是心計,都是遠超常人的,手段更是厲害的很。
他厲南城也寵人,但看要是寵誰,又怎麼寵了。
猜你喜歡
-
完結407 章

深夜入懷,禍她成癮
深州市新晉首富江厭離風光大婚,娶的是一個寡婦,且對方還有個三歲的兒子。深州市的人都說江厭離被下了降頭,才會做出給人當后爸這種離譜的事情。只有江厭離自己知道,他何其有幸,能再度擁有她。某天被親兒子氣個半死的江首富討好地吻著他那溫婉動人的嬌妻,“老婆,我們再要個女兒吧?”她柔聲應了聲,“好。”多年以前。一場醉酒,她招惹上了未婚夫的死對頭。事后對方食髓知味,她因有求于他,不得不與他夜夜周旋。深夜,他們縱情貪歡。白天,他們互不相識。她以為她會一直與他糾纏下去,直到他忽然宣布訂婚。他說除了名分,什麼都可以給她,包括他的命。
82萬字8.18 16060 -
完結535 章

白月光進門,我帶崽離婚你瘋什麼
結婚三年,姜芫才跟周觀塵圓房。提上褲子后,他對她說:“你是我見過最無恥的女人。” 姜芫不在乎,她以為只要足夠愛,他一定會回應。 直到周觀塵帶著白月光和那個和他七分像的孩子回家,還要把孩子的戶口落在她戶口本上,她徹底死心。 轉身撕碎了孕檢單,別人的孩子和臟了的男人,她通通不要。 某霸總看著前妻從村姑變身修復文物專家,還是他一直尋找的古文字大師,悔不當初。 他化身舔狗,她虐渣他遞刀;她下墓他當保鏢;甚至連她跟別的男人約會,他都兼職跑腿小哥,送套兒帶孩子。 約會結束后,她對他說:“你是我見過最無恥的男人。” 周觀塵不在乎,他以為只要足夠誠心,她就一定會回頭。 直到她披上婚紗,帶著女兒嫁給了別人…… 他慘淡一笑,單槍匹馬闖入狼窩,救出她最敬愛的師父。 從硝煙中蹣跚走來,他以血染玫瑰,跪在她面前-- “我遺囑上早就寫了你的名字,現在就用我這條命,送你一個新婚大禮。”
96.5萬字8 4007 -
完結7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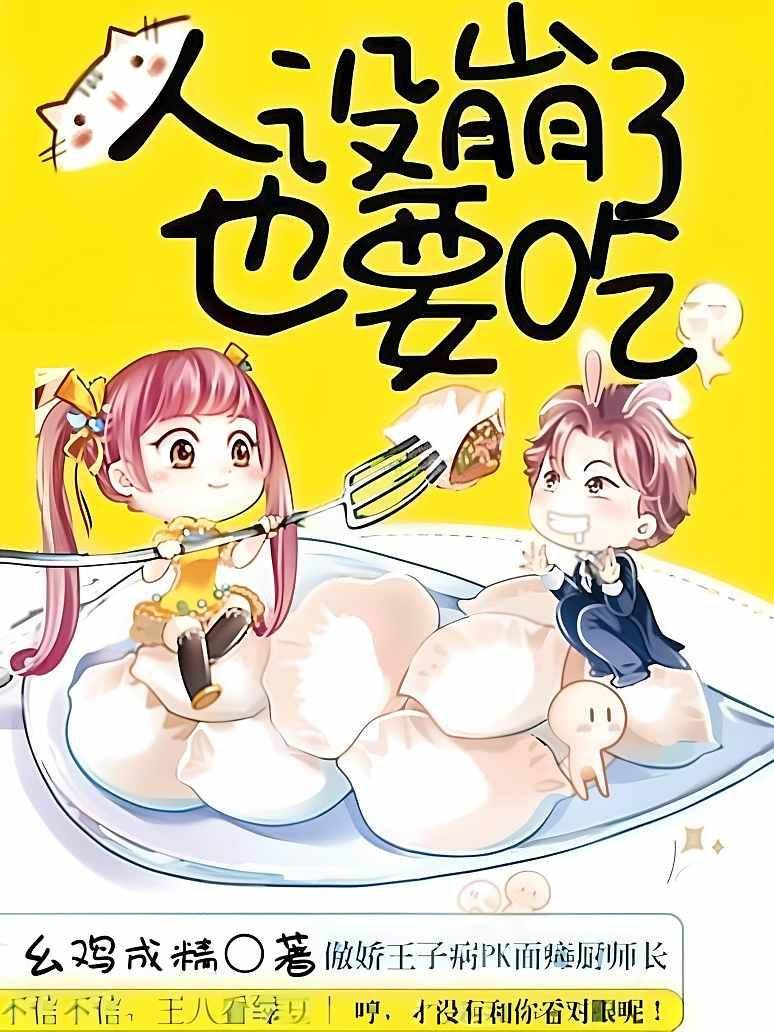
人設崩了也要吃
【那個傲嬌又挑剔的王子病和他面癱很社會的廚師長】 當紅明星封人盛,人稱王子殿下,不僅指在粉絲心中的地位高,更指他非常難搞。直到有一天,粉絲們發現,她們難搞的王子殿下被一個做菜網紅用盤紅燒肉給搞定了…… 粉絲們痛心疾首:“不信不信,王八看綠豆!” 季寧思:“喂,她們說你是王八。” 封人盛:“哼,才沒有和你看對眼呢!” 季寧思:“哦。” 封人盛:“哼,才沒想吃你做的綠豆糕!” 季寧思:“滾。”
17.1萬字8 7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