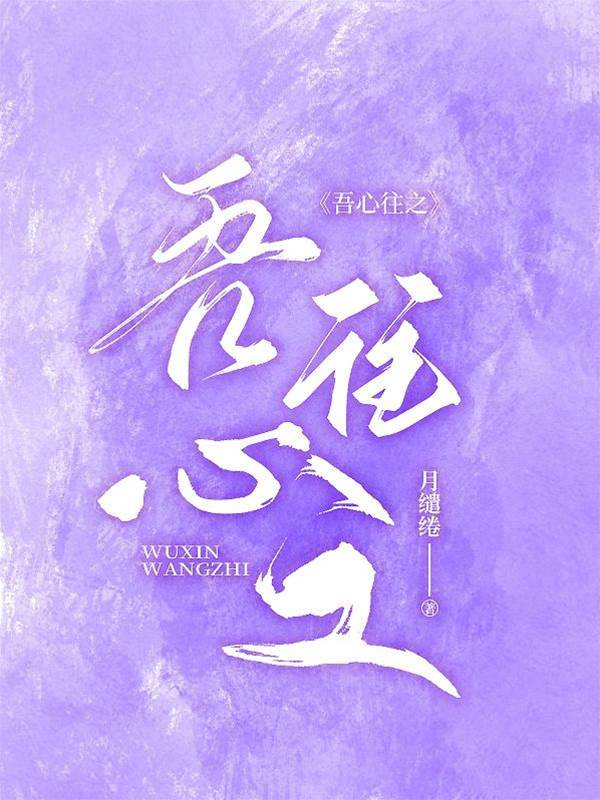《雁來月》 第40頁
他吁了口氣,拈過一個新杯子,把茶倒進去:“我聽說,你和男朋友在冷戰?”
暮里,西月睜大了眼睛看他。
付長涇還跟他說這種事嗎?
冷戰也是他單方面的,并沒有什麼覺,本來也沒怎麼理過他。
懶得多說:“嗯,您有什麼問題嗎?”
聽見的回答,鄭云州篤定地笑:“是這樣,我希你趁這個機會,和他分手。”
他是不是有點越界了?
沒錯,他是救過自己幾次,但不代表必須事事聽從他,尤其,這是的私事。
著急了一下午,被接到這麼個陌生地方,到現在還沒見上弟弟,又擔心又上火,面對這樣的鄭云州,真的有點生氣了。
西月揚起下表示:“為什麼?我不會......”
“聽您擺布”四個字還沒說完。
鄭云州便高聲打斷道:“你會。”
水亭旁的柏樹梢頭,有一只老鴰啞著嗓子哇了一聲,忽地騰空而起。
西月被驚了一下,手腕細微地抖著,迷地向他。
而鄭云州看過來的眼神毫無緒。
覺得很悉,像在哪個地方見過這個眼神。
那仿佛是獵豹一類的食猛tຊ在鎖定了目標獵后,才會有的平靜銳利。
林西月聲問:“所以,我和付長涇分手之后,是必須和鄭總在一起嗎?”
否則他這麼個諸事纏的大忙人,何必花時間來關心的進度?
難道付家也托了他來當說客?
顯然,付長涇怕他怕得要死,還沒有調他的本事。
鄭云州不著痕跡地收回了視線。
他低沉地笑了聲:“我說過,你很聰明。”
Advertisement
林西月一路趕過來,鬢發躁地散在耳邊,手捋了一下,急切道:“抱歉,我還是不太明白,您什麼意思?”
“那我就說清楚一點。”鄭云州站了起來,走到湖邊,背對著,慢條斯理地說:“林西月,我要你待在我邊,做我的朋友。”
林西月尾調上揚地哦了聲:“為什麼是我呢?”
鄭云州不明白,怎麼這樣問?
他轉,不解地擰了擰眉:“這有什麼為什麼?”
“那我來說吧。”林西月抬起下,目沉靜地迎上他,“聶家二小姐得,雙方父母給您的力都很大,這樁婚事令您倍棘手,您需要一個朋友來緩和局面,好彼此都下得來臺,面子上不那麼難看。”
鄭云州皺著眉頭聽完,只覺得小孩子稽荒唐。
他要拒絕聶子珊,把過來,當面跟言語一聲就是了,還用特地找個朋友?還沒那麼大的臉面!
這都哪兒傳出來的野話?
但鄭云州慣了的,他本不屑剖白自己,更懶得解釋什麼。
他微一頷首:“你愿意的話,就這麼想也無妨。”
著他冷峻的眉眼,林西月已懂了大半。
苦笑了下:“您會選中我,因為我只是個窮學生,正著貴集團的資助,無論怎麼樣也翻不出您的手心,拿來當擋箭牌養在邊,再合適不過了,以后再有什麼張家李家的,您也不用愁,真是筆劃算的買賣。”
看來恩如說的是真的。
鄭云州的確有這個打算。
那麼這段時間的相,包括單獨帶去湖邊住,都只是一場不聲的面試,考驗是否有資質勝任這個角?
Advertisement
而表現尚可,既不貪圖富貴也不故作驕矜,甚至還能調起他淡薄的緒,贏得了鄭總友這張offer,是這樣嗎?
現在看來,那些因他而起雀躍,那些下意識的心,不過是個自作多的誤會。
怎麼會覺得鄭云州待與眾不同的?
想到這里,林西月低下頭,不覺勾了勾,出個自嘲的微笑。
是有點太不自量力了。
鄭云州轉過,亭畔幾綠藤的影子在他邊。
他瞥了林西月一眼:“倒也不用說的這麼難聽,你還沒有聽我的條件。”
都考慮好條件了,這更讓林西月確信,鄭云州在和做換。
這個臉丑陋的資本家,連在私人上也奉行金本位制,認為青春同樣有售價。
路上走著的,一個個鮮活的孩子,在他們眼里和櫥窗里的商品沒有區別,都可以一擲千金買下來。
也許有人愿意售賣自己,但做不到。
“條件?”林西月笑著站了起來,眼尾酸得要命,努力地將眼睛睜得圓圓的,不讓自己難堪到掉眼淚,說:“當鄭總的朋友,待遇一定非常優渥,很多人夢寐以求呢。可您搞錯了,我雖然窮,但也上過學念過書,知道什麼能做什麼不能,您的這筆生意,我實在難以從命,還是換個人做吧。”
鄭云州早料到會這樣說。
不要看文弱,但比任何人都要自,是絕不肯答應的,反而會覺得是種辱。
前面十九年的困苦將打磨、拋現在的模樣,沒的選擇,必須堅韌而強大地,孤伶伶地支撐著自我長起來。
林西月心如此,只會這麼認為。
Advertisement
可是他呢,他一發不可收拾地喜歡上,明知道這是個水潑不進的狠角,除了出人頭地,腦子里裝不下第二件事,他只能拿他的權勢來。
他不能接自己鐘意的人,只是中立地、客觀地存在于這個世界,每天漂亮生地盛放在眼前,卻不屬于他。
他要,他要來填滿自己的世界。
鄭云州也只好這麼做。
他掠奪慣了,最擅長的就是生意場上的博弈,談分不如開價碼。
袁褚站在不遠看著這一切,兩個都拿自己不知如何是好的人到了一起,結局只能是撞得頭破流。
靜了片刻,鄭云州輕嘆著說了句:“我的提議三天都有效,先去見你弟弟吧,他好像有事要和你說。”
林西月轉過頭,飛快地抹了下眼尾:“謝謝您替我找到他。”
鄭云州也累了,揮了下手,讓去。
他在湖邊站了很久,直到濃重的夜完全籠罩住他,整個人陷在沖不散的黑暗里。
鄭云州還在想被打斷的話。
如果沒有突然發脾氣,他原本要說什麼來著?
好像是段老派又古板的表白,他坐在辦公室里想了很久的。
“你敏慧得,實在是很合我心意,我很喜歡。”
就這麼被小姑娘掐斷在了嚨里。
算了,講與不講都差不多。
反正最終,都不可避免地要恨上他。
那時他還年輕,不知道這麼樣東西,是如此容易走歧途。
一句沒能說出口的話,一個產生了誤會的表,都將引起巨大的連鎖反應,教他們各自懷揣著沉甸甸的,卻一再地背道而馳。
林西月在后面的廂房里找到了董灝。
Advertisement
他歪扭地坐在羅漢床上,兩只手懊惱地抱著自己的頭,不停地捶著。
“好了。”林西月走過去,把他的手拿下來,“打自己有用嗎?”
董灝抬起頭:“姐姐,我不是故意要讓你擔心的。”
林西月在他邊坐下:“那為什麼不接電話?辭職,招呼不打就要回老家,你到底上什麼事了?”
“我不想拖累你,我不想。”董灝看著說,頭搖搖晃晃的。
林西月的指甲深深嵌進掌心。
有種很不好的覺,像尖細的針一樣扎進腦海中。
已經大概猜到原因,并為此到窒息。
一種命運的冷雨即將兜頭淋下,而卻無力招架的窒息。
林西月低下頭,對上他慌的目:“有事你就說出來,老師把你托付給我了,我們是一家人,應該要互相幫助的,說什麼拖不拖累。”
“幫......幫不了,沒有錢。”董灝的頭又晃了兩下,“那要很多錢。”
林西月不斷追問:“什麼事要很多錢?你跟我講講。”
董灝又背過去,本不敢看的眼睛。
西月幾乎已經敢肯定了。
輕聲的,用一種近乎哀弱的調子詢問:“你生重病了,覺得我們治不起,是不是?”
剛說完,一雙水杏眼里已蓄起了淚。
老天爺真是殘忍,也真是不開眼。
小灝從小底子就差,拖著一副功能不健全的長到這麼大,一路上了那麼多嘲笑和譏諷,好不容易換了個地方,也拾起了重頭再來的勇氣,日子剛剛步正軌,又給他降下這麼一道難關。
哦豁,小伙伴們如果覺得不錯,記得收藏網址 或推薦給朋友哦~拜托啦 (>.
猜你喜歡
-
完結1250 章
強勢纏愛:總裁,你好棒(林語嫣 冷爵梟)
結婚一年,老公寧可找小三也不願碰她。理由竟是報復她,誰讓她拒絕婚前性行為!盛怒之下,她花五百萬找了男公關,一夜纏綿,卻怎麼也甩不掉了!他日再見,男公關搖身一變成了她的頂頭上司…一邊是拿床照做要挾的總裁上司,一邊是滿心求復合的難纏前夫,還有每次碰到她一身狼狽的高富帥,究竟誰纔是她的此生良人……
264萬字8 56104 -
完結1446 章

借住後,小黏人精被傅二爺寵翻了
傅二爺朋友家的“小孩兒”要來家借住壹段時間,冷漠無情的傅二爺煩躁的吩咐傭人去處理。 壹天後,所謂的“小孩兒”看著客房中的寶寶公主床、安撫奶嘴、小豬佩奇貼畫和玩偶等陷入沈思。 傅二爺盯著面前這壹米六五、要啥有啥的“小孩兒”,也陷入了沈思。 幾年後,傅家幾個小豆丁壹起跟小朋友吹牛:我爸爸可愛我了呢,我爸爸還是個老光棍的時候,就給我准備好了寶寶床、安撫奶嘴、紙尿褲和奶酪棒呢! 小朋友們:妳們確定嗎?我們聽說的版本明明是妳爸拿妳媽當娃娃養哎。 小豆丁:裝x失敗……
261.7萬字8.18 126691 -
完結596 章

新婚夜植物人老公親哭我
她愛上霍時深的時候,霍時深說我們離婚吧。后來,顧南嬌死心了。霍時深卻說:“可不可以不離婚?”顧南嬌發現懷孕那天,他的白月光回來了。霍時深將離婚協議書擺在她面前說:“嬌嬌,我不能拋棄她。”再后來,顧南嬌死于湍急的河水中,連尸骨都撈不到。霍時深在婚禮上拋下白月光,在前妻的宅子里守了她七天七夜。傳聞霍時深瘋了。直到某一天,溫婉美麗的前妻拍了拍他的背,“嗨!霍總,好久不見。”
105.6萬字7.77 95117 -
完結12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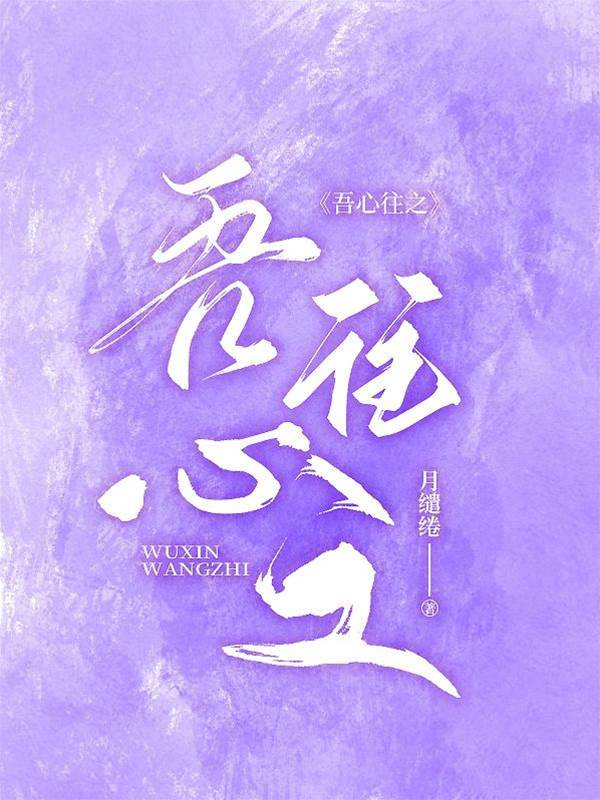
吾心往之
【久別重逢,破鏡重圓,嘴硬心軟,有甜有虐he 】【獨立敏感的高冷美人??死心塌地口是心非的男人】【廣告公司創意總監??京圈權貴、商界霸總】——————阮想再次見到周景維的時候,那一天剛好是燕城的初雪。她抱著朋友的孩子與他在電梯間不期而遇。周景維見她懷裏的混血女孩兒和旁邊的外國男人,一言不發。走出電梯關閉的那一刻,她聽見他對旁邊的人說,眼不見為淨。——————春節,倫敦。阮想抱著兒子阮叢安看中華姓氏展。兒子指著她身後懸掛的字問:媽媽,那是什麼字?阮想沉默後回答:周,周而複始的周。
22.3萬字8 3350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