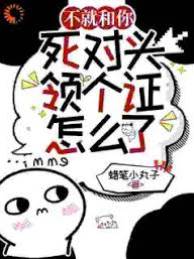《拒婚后我高嫁小叔,太子爺你哭什麼?/刺激!未婚夫成了前任小叔》 第1卷 第262章 我心里只有你
苏逸山一听报警立马道:“都是一家人,没必要闹到这个地步,况且怀礼给以柠下药,要是报警他也脱不了干系。”
司怀礼冷冷一笑,“岳父,谁跟你说是我下的药?你有证据吗?”
他一句话让苏逸山突然明白过来,司怀礼早就找好了背锅侠。
他这样的份,只要拿钱,手上有的是人愿意顶罪。
司家最不缺的就是钱,苏以柠可就惨了,现在他们手上关于的证据是确凿的。
要是报警,被抓的肯定是苏以柠。
局势瞬间颠倒,原本有理的人也了没理的人。
苏婉禾看到这一幕也不觉得寒心了,毕竟的那颗心早就在苏逸山一次又一次的偏爱中消耗殆尽。
庆幸自己嫁的是司家,没想到给撑腰的也是司家人。
司老爷子然大怒,“苏逸山,老实说我对苏以柠这个孙媳妇本来就不满意,一开始就给怀礼下药,作风不端,后来在马场对婉禾不利,还有墓碑的事,今天还要毒害婉禾和孩子,这样的人你称之为儿,在我眼里简直就是蛇蝎!我司家可不敢要这样的人进门。”
Advertisement
苏逸山来之前也想过了,这件事摆明了是司家吃亏,如果能借题发挥,让司家放点出来也好。
正好苏以柠的嫁妆都没了,他打的主意就是从司家这里回。
谁知道剧竟然是这样的,不蚀把米。
“司老先生,你是什么意思?”
“我能容忍一次两次,好事不过三,你自己看看,这做了多次了?这门婚事不如就此作罢!”
“那不!怎么能作罢呢?两家的利益已绑定,而且他们都领取了结婚证,怀礼还持有我们苏家的份。”
“你也知道我们两家已绑定在一起了,那你儿次次作妖,现在连还没有出生的孩子都不放过,的心思得恶毒什么样子?之前我还不明白为什么,原来是上梁不正下梁歪,我就搞不清楚,你放着这么好的儿不喜欢,非得要去宠爱一个人生出来的孩子,瞧瞧,像什么样子?”
司老爷子从前还给了他几分薄面,今天也是怒不可遏,再没有给他一点面子。
Advertisement
“对不起,这件事确实是我的问题,我……”
“从你过来到现在,你一味指责别人,你有没有关心过你的儿?要是喝了药,说不定会一尸两命。”
苏婉禾淡淡开口:“爷爷,你可能还不知道,我已和苏家划分界限,以后再无瓜葛,所以苏先生不关心我也是理所应当的事。”
“苏婉禾,别忘了你现在还姓苏。”苏逸山也不知道为什么,一开口就和苏婉禾吵起来。
苏婉禾笑了笑:“我对这个姓氏也没什么可留的,我可以明天就改为司姓,或者赵钱孙李哪一个都行。”
苏逸山卡壳,不知道该怎么回答,只能放低姿态去哀求司老爷子不要取消婚事。
之前有多嚣张,现在就有多卑微。
苏婉禾懒得再看,时间也不早了,就住在了老宅。
司怀礼跟着而来,在进门之前他开口道:“姐姐。”
苏婉禾没有停下脚步,他今天所做的这一切没有一点波动。
那三年的时,早就在他出轨那天彻底消失。
司怀礼再度开口道:“在我心里只有你才是司太太。”
么?
为什么当初在门外听到的是他要将自己养在南城?
人啊,果然是这个世上最善变的生。
“我不会和苏以柠结婚的,我心里只有你。”
猜你喜歡
-
完結495 章

蝕骨情:賀先生,別亂來
兩年前,她被判定故意弄傷了他心愛之人的腿。于是他把她送進了監獄,廢了她一條腿和她所有的驕傲。兩年后,她自認為已經從地獄中逃出來,立誓再不愿再和他有任何瓜葛。可事實證明,地獄的撒旦怎麼可能會輕易放過你呢。...
85.1萬字5 115964 -
完結8136 章
你是我的難得情深
葉北北一時不防被算計,嫁給坐在輪椅上的顧大少。本以為從此過上豪門闊太生涯,有錢又有閑,哪知道天天被奴役成為小保姆。葉北北拍桌:騙子,我要離婚!顧大少將萌寶推到身前:孩子都有還想離婚?老婆大人你醒醒!“……”葉北北看著和她一模一樣的萌寶一臉懵圈。誰能告訴她,她什麼時候生過孩子!?
726.1萬字8.18 88455 -
完結291 章

霍少別虐了,夫人她嫁給你小叔了
簡介: 五年前,她是驕傲的林家大小姐,一場陰謀,讓她失去一切,含冤入獄生下一子。五年後,她謹小慎微,卻被他們步步緊逼。她知道,他們要的是……她的命!可她林思靜偏偏不信命!她以自己為餌,與帝都最危險的那個男人做了筆交易。本以為是互相利用,卻沒想到婚後他溫柔似水,替她掃平障礙。當一切真相水落石出,死渣男跪在她麵前,“阿靜,再給我一次機會,讓我照顧你一輩子。”霍謹言作者:“滾,叫小嬸!”
28.1萬字8.18 10693 -
連載51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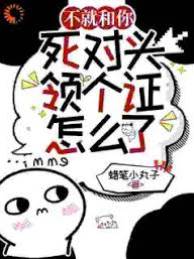
不就和你死對頭領個證,怎麼了?
第三次領證,沈嶠南又一次因為白月光失了約;民政局外,江晚撥通了一個電話:“我同意和你結婚!” 既然抓不住沈嶠南,江晚也不想委屈自己繼續等下去; 她答應了沈嶠南死對頭結婚的要求; 江晚用了一個禮拜,徹底斬斷了沈嶠南的所有; 第一天,她將所有合照燒掉; 第二天,她把名下共有的房子賣掉; 第三天,她為沈嶠南白月光騰出了位置; 第四天,她撤出了沈嶠南共有的工作室; 第五天,她剪掉了沈嶠南為自己定制的婚紗; 第六天,她不再隱忍,怒打了沈嶠南和白月光; 第七天,她終于和顧君堯領了證,從此消失在沈嶠南的眼中; 看著被死對頭擁在懷里溫柔呵護的江晚,口口聲聲嚷著江晚下賤的男人卻紅了眼眶,瘋了似的跪求原諒; 沈嶠南知道錯了,終于意識到自己愛的人是江晚; 可一切已經來不及! 江晚已經不需要他!
92.8萬字8 9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