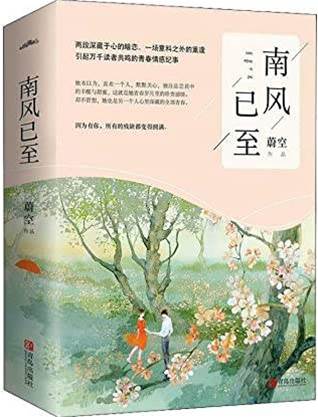《婚後告白》 春夜難眠
尤鞠第一次見到徐疏寒,是在一場飯局上。
此時正因為得罪了某個大人面臨雪藏,而這場飯局,是重新拿到娛樂圈場券的最後機會。
至于用什麽樣的手段和方法,經紀人貌似并不在意,甚至鼓勵要學會利用“資源”。
是最後一個到的,因為豔的皮囊,剛一落座就免不了一頓揶揄,有幾個手握資源、資歷不淺的某某總還嚷嚷著讓喝酒賠罪。
尤鞠深吸一口氣,還是端起了酒杯:“非常不好意思,今天實在是堵車來晚了,我自罰三杯。”
說完,幾乎全場的人都在起哄。
至于為什麽說是“幾乎”,則是因為坐在主位上的那人,一直冷眼旁觀,似乎全然不在意這場小打小鬧。
男人的氣質和長相太過出衆,尤鞠很難不注意到,在慨完他驚為天人的五線條後,尤鞠忍不住地看向男人腕間的限量版名表。
挑眉,在腦袋裏想了個數字。
然後默默撇,慨手握萬貫家財的資本實在是奢靡,連買個腕表都得挑最能彰顯份的。
飯局結束後,尤鞠不聲地接過某位不知名總的名片,神淡淡地掃過印在卡片上的前綴,沒有言語。
可對方卻毫沒看出來什麽,還以為收了名片就是接了自己的暗示,沒聊兩句話就要去摟的肩。
尤鞠今天穿了件黑的連,希臘神式的領口,雪肩/在空氣中,白得晃眼。
心頭湧上一反胃的厭惡,條件反地避開,只隨口吐了兩句客套話,也算將界限劃清。
看到這麽不識擡舉,男人顯然也有些不高興,僵在半空中的手收回,慍怒道:“尤小姐,咱們這個圈子可瞬息萬變,得學會抓住機會啊。”
Advertisement
尤鞠深吸一口氣,邊陪笑邊在心裏作嘔:“是是是,您說的對,我一定認真打磨演技。”
“不只是演技——”
男人的話沒說完,就被不遠傳來的另一道聲音。
“劉總,讓個路?”
也是男聲,但更為年輕清冽。
還含了兩三分笑意。
下意識擡眸看去,尤鞠不自覺了瞳仁,沒想到,此刻陡然現的人,居然是放在在包廂裏、坐在主位的那個男人。
黑的西裝外套不知道什麽時候被下,上只有一件黑襯衫,領口最頂端的扣子松開一顆,恰到好的松弛矜貴,連氣質都尤為出衆。
更何況,是那張毫不輸一線男的臉。
他逆而立,距離僅有半寸之遙。
近到……幾乎可以嗅到來自他上,淡淡的冷掉薄荷味。
還混了縷縷的煙草味。
不濃烈,但印象深刻。
間不自覺一,尤鞠定定地看著他,神停滯。
像是沒有察覺到視線似的,徐疏寒依舊淡然,微微垂頭,看向比自己矮了十幾公分的劉總:“劉總好興致啊,這麽晚了還不走,這是要給小演員講戲?說起來,上周我才見過您兒,很可。”
劉總臉一黑,眼底閃過一心虛,沒再說什麽就離開了。
著那道幾乎可以用落荒而逃形容的背影,尤鞠不自覺地彎了角,心裏只覺得過癮。
“我記得,你尤鞠?”
忽地聽見自己名字,尤鞠的心咯噔一下,看過去:“您好。”
短促地笑了下,徐疏寒道:“別張口閉口就是‘您’,不知道的以為我比你大五十歲。”
半科打諢的口吻,尤鞠心跳怦然。
從來沒在娛樂圈見過這樣的人。
明明剛剛在飯局上,他衆星捧月、孤傲如霜,可此刻,竟然能神隨意地說出這類玩笑話,溫得要命。
Advertisement
真的,是一個人?
徐疏寒又問:“尤其的尤?哪個鞠?”
“蹴鞠的鞠,”尤鞠從善如流地答道:“可能有點難寫。”
“還好。”
話音剛落,徐疏寒出手,那只價格不菲的腕表就這樣直愣愣沖進尤鞠的瞳仁中,然後……眼睜睜地看著這人將原本在自己手裏的名片走。
半秒後,看到已經被他踩在腳底的小卡片,一時間也不知道說什麽。
徐疏寒:“這種東西,別信,也別。”
不可察地皺了皺眉頭,尤鞠抿。
周遭安靜如斯,良久都無人路過。
一時間也不知道是巧合,還是他人故意為之。
今年二十三歲,早就過了相信話故事的年紀,也不相信真的會有一擲千金的大人突然跑出來助人為樂。
明明是第一次見面,明明在飯局上卻一句話都沒說過,為什麽,他要特地來為解圍?
腦袋被數不清的問號填滿,尤鞠只覺得口煩悶得很不舒坦。
見不說話,徐疏寒揚眉,再度開口:“我讓司機送你回去吧,正好順路。”
“順的哪條路?”
他話音剛落,便開口。
小幅度的仰頭,彼此的眸剛好對上。
頗有幾分“你方唱罷我登臺”的氣勢如虹。
深吸一口氣,尤鞠倒也開門見山了:“還沒請教您的名字?”
依舊在用“您”來稱呼。
是故意的。
在試探他。
徐疏寒冷著臉,瞇了瞇眸,邊卻溢出一淺淡的弧度:“徐疏寒。雙人徐,疏散的疏,寒氣的寒。”
“那請問徐先生,為什麽要幫我?”
“覺得好玩。”
他答得隨意,半分搪塞敷衍的意思都沒有。
大概率,是瞧不上搪塞。
尤鞠這樣想,心髒七上八下地跳著,說不清此刻是個什麽心,可不知道為什麽,竟然全然不討厭這位徐先生的蓄意靠近。
Advertisement
甚至,還很期待。
好玩嗎?
他覺得是哪裏好玩,事還是人?又有多好玩?
就在百般糾結的時候,他又道:“看來尤小姐對我警惕心很足啊,這是好事。”
說完,他轉離開。
可也就是這麽一瞬間,有什麽東西從他的西裝口袋裏掉出來。
四四方方、薄薄的一張卡片。
下意識去撿,卻被卡片正中間的一串數字刺激到,指尖虛浮在半空中,拿也不是,不拿也不是。
一秒後,幹道:“徐先生,你的房卡掉了。”
男人聞聲回頭,凜冽的眉眼無端生出些許笑意:“拿著吧,專門讓你撿的。”
滾在被子裏糾結了幾個小時,尤鞠還是決定赴約。
臨出門前,將風裏的打底衫換了一件輕薄款的修吊帶。
指肚掐在冰涼的門扉邊沿,咬著牙,一個字也蹦不出來。
連灰姑娘都知道午夜的鐘聲是危險警告,卻依然在此刻前往,這跟明知山有虎,偏向虎山行的傻子有什麽區別?
如是想著,自嘲地笑了笑。
心知這是一場豪賭,更明白自己是個沒有籌碼又窮途末路地賭徒,可哪怕只有一點點的機會,也想拼命抓住借此翻盤。
既然已經走到這一步了,就算輸,又能輸得多慘呢?
可如果贏了……
這個抉擇帶來的紅利,竟有些不敢細想。
剛剛在房間時,特地從網上搜了“徐疏寒”三個字,總算是明白了為何這人能在飯桌上一次又一次的恭維,哪怕全程冷臉,也無人敢置喙半句。
他的確有這個資本。
因為他手握娛樂圈最著名的影視公司,圈最有分量的“三巨頭”背後都有他的盤,說他間接拿了半個圈子也不為過。
這樣的人,怎麽會缺人,又為什麽偏偏看向?
Advertisement
尤鞠想不通,怎麽都覺得不對勁。
思緒百轉千回間,抵達了那間總統套房的門口。
看著如房卡上如出一轍的數字,心跳得更快。
想了想,還是決定敲門。
不等自報家門,門把手便傳來細微的聲響,跟著,男人清雋的面龐從門框與門扉之間的空隙看得愈加清晰。
他似乎剛洗完澡,連額前的發都還沾著些許水氣。
有種說不出的好看。
他的手裏,還端了只玻璃酒杯。
清,泛著橘黃的調,正中間還擺了幾只棱角已經圓潤的冰塊。
不是尋常紅酒,像朗姆。
看見是,徐疏寒半點也不驚訝,反而笑意始終:“來了。”
尤鞠咬,有種被看了的局促。
覺得自己此刻像只被拖陷阱的羔羊,沒了逃跑的餘地,只能被迫溫順地等著獵人的宰割。
走到房間裏面,接過男人遞過來的酒杯,抿了一小口,悉的口立刻浸潤齒。
果然是朗姆酒。
徐疏寒半倚在落地窗前,饒有興趣地打量著如坐針氈的坐姿,忍不住想笑:“張?”
尤鞠忙道:“沒有啊。徐先生只是想跟我聊聊天,我怎麽會張呢?”
一開口,眼底的怯意更為濃烈。
像煙花一般炸開,于絢爛的夜幕中璀璨奪目。
徐疏寒哂笑,抿了口烈酒,幽幽道:“尤小姐,我比較欣賞聰明人,自欺欺人用一時可以,用不了一世。”
隨著他每個字落地,尤鞠心存的僥幸也即刻然無存。
吞咽一口,著涼意的玻璃杯被放回了手邊的小圓桌上,十指握拳頭,以一個防備心十足的姿勢搭放在膝蓋上,悄然握。
不說話,徐疏寒的耐也漸漸告罄。
也放下了酒杯,他朝走過去,一只手撐在圓桌上,腰俯下:“我想捧你。這樣說,能夠明白嗎?”
他陡然靠近,尤鞠避無可避,只能著頭皮和男人對視。
心跳約失控,不想怯,只得問道:“為什麽選擇我?”
依舊是那個口吻,依舊是慵閑懶散的做派,可他的眼神,卻一點都讓人覺不到輕松。
反而汗直立。
就好像,是死死盯住獵的雄鷹。
他道:“徐某是個淺的人,尤小姐恰好生了張我極為欣賞的皮囊。”
“當然,這是一場易,我會給你想要的,而你,也要付出一些等價籌碼。”
話至此,又還有什麽不明白的呢。
無力地笑了下,尤鞠甚至覺得如釋重負。
至親口聽到他說,比自己戰戰兢兢地猜舒坦多了。
深吸一口氣,似壯膽般:“我現在除了這張臉,好像真的什麽都沒有了。”
徐疏寒更進一步地靠近,掌心上脖頸,緩緩向下。
掌心溫熱,連指腹都帶著驚人的燙意。
尤鞠分不出是因為酒作祟,還是他原本的溫就是如此。
“尤小姐瞧著很有天賦,不試試怎麽知道呢?”
跟著了一下,尤鞠間泛起酸意:“那就試試吧。”
猜你喜歡
-
完結70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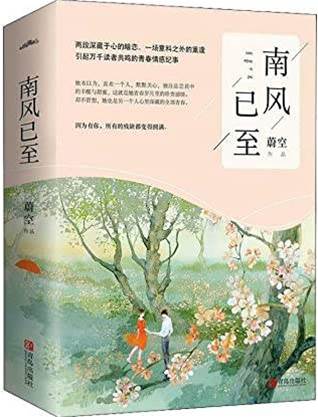
南風已至
——我終于變成了你喜歡的樣子,因為那也是我喜歡的樣子。 在暗戀多年的男神婚禮上,單身狗宋南風遇到當年計院頭牌——曾經的某學渣兼人渣,如今已成為斯坦福博士畢業的某領域專家。 宋南風私以為頭牌都能搖身一變成為青年科學家,她卻這麼多年連段暗戀都放不下,實在天理難容,遂決定放下男神,抬頭挺胸向前看。 于是,某頭牌默默站在了她前面。
22.2萬字8 6582 -
完結1080 章
婚亂流年
結婚紀念日,妻子晚歸,李澤發現了妻子身上的異常,種種證據表明,妻子可能已經……
191.5萬字8 10953 -
完結336 章
錯嫁后她成了第一財閥夫人
被渣爹后媽威脅,沈安安替姐姐嫁給了殘廢大佬——傅晉深。全城都等著看她鬧笑話,她卻一手爛牌打出王炸!不僅治好傅晉深,還替傅家拿下百億合作,成為名副其實的第一財閥夫人
64.8萬字8 53558 -
連載405 章

流產當天,我離婚了
“恭喜你,懷孕了!”她懷孕的當天,丈夫卻陪著另一個女人產檢。 暗戀十年,婚后兩年,宋辭以為滿腔深情,終會換來祁宴禮愛她。 然而當她躺在血泊里,聽著電話中傳來的丈夫和白月光的溫情交耳,才發現一切都只是自我感動。 這一次,她失望徹底,決心離婚。 可在她轉身后,男人卻將她抵在門板上,“祁太太,我沒簽字,你休想離開我!” 宋辭輕笑,“婚后分居兩年視同放棄夫妻關系,祁先生,我單身,請自重,遲來的深情比草賤。” 男人跪在她面前,紅了眼,“是我賤,宋辭,再嫁我一次。”
49.2萬字8 15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