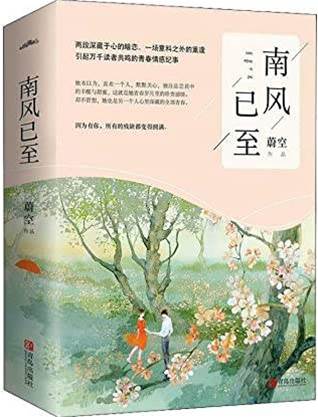《霧色難抵》 第212頁
◎「白頭如新,傾蓋如故。」◎
《Welcome to New York》的歌聲在時代廣場上響徹,煙花在天際燃起,一層一層疊加,落幕又不斷盛放。
所有鼎沸人聲中,他的聲音依然明晰。
周遭的背景不斷倒退,的瞳孔里倒映的只有他。
「新年快樂。」沈怡彎起角,笑眼盈盈。
飄飄揚揚的雪花,散落在空中,落在眼睫上,晶瑩爍著閃。
出手,想要接住那片雪花,冰冰涼涼,很快融化,再重新染上熱度。
雪花紛紛揚揚,可撲不滅熱如火,喧鬧中意沸騰。
「年年有今日,程硯深。」聲音溫,像糖溶在中,翻騰跳。
他們之間好像離不開一個偶然,煙花綻放下,雪花融,又遇到最初的他。
程硯深牽住的手,去掌心的水漬,含笑道:「大小姐,這話該是我說的。」
沈怡踮起腳尖,抱住他的頸子,輕輕晃著:「可這是我的願。」
「想和你一直在一起。」
的耳朵在他的頸側,他心跳的鼓震都傳耳腔,每一瞬都是悸。
沈怡忍不住抱得更,仿佛想要留住這一刻。
「老公,我想回家了。」
外面太吵,有太多想和他說的話。
「我們回家過二人世界吧。」整個人進他懷裡,懶懶地開口,「你背我。」
從擁的人群中離,別墅離得不遠,程硯深滿足今天生日的主人公的願,他背著往回走。
Advertisement
逆著人群,疊在一起的影子被影拖得長長的。
沈怡靠在他肩上,歪著頭看他,下頜線鋒利又清晰。
輕聲開口:「如果在倫敦,我沒有主,是不是我們就沒有故事了。」
其實不喜歡如果,可有時候沉浸其中的時候,有個詞義無反顧,熱烈又激,可又忍不住去想些不一樣的可能。
「傾蓋如故,白頭如新。」程硯深雲淡風輕開口,「可能會有那個如果,但也不會改變結果。」
即便沒有倫敦,也會有其他地方,或許也可能是他們在那個酒莊的第一面。
鍾這件事,在遇到那個人的時候,似乎很簡單。
沈怡埋在他頸窩裡,心間激起波瀾。
「那我們現在呢?」的面頰著他的臉,偶有風雪拂面,近的溫度依然留有那份熱度。
「現在——」程硯深推開別墅的門,深眸掠過,定在瑩白的面上,「需要關門了。」
屬於他們兩個人的二人世界。
房門關閉的那一剎那,上的大已經掉落到地面。
無聲之中,是默契的心。
沈怡沒說話,指尖扯著他的領帶,一圈一圈,將距離一點點拉近。
指腹微涼,點在他的襯衫領口,又向後微仰,錯開彼此之間的距離。
「你去換服。」半靠在門前,興味盎然。
瓷白膩的皮迎著一層,昏黃的燈留下一點暈,在緻的面容上緩緩散開:「臥室床上,已經放好服和配飾,你照著穿就好。」
Advertisement
彼此都清楚的,準備的,親手做的。
鏈。
沈怡是做了點研究的,有些東西不能過於暴,要半半現才更有韻味。
程硯深換過服,從房間裡走出的時候,修長的雙襯出比例極佳的材,沈怡忍不住揚眉,目緩緩向上,角不由勾起。
銀鏈從他的脖子向下,細細碎碎閃著冷,繞過骨的鎖骨,在結下鑲了一顆灼目晶瑩的紅寶石。
冷白之上,一點灼紅。
斯文又慾。
再向下銀鏈細線分散著沒在白襯衫之下。
布料單薄,約過下的理,塊壘分明的腹,實有力的膛。
沈怡打開室所有的燈,明亮清晰,連銀鏈的走向都格外清晰。
還有鑲嵌在銀鏈上的紅寶石。
在襯衫之下,若若現,似有還無。
朦朦朧朧的紅,放縱肆意的。
比想像中,更驚艷。
程硯深將沉溺的表納眼底,步步靠近,低笑間眼皮輕闔:「你這些天在家,就忙著做這個?」
忍了忍想要吹口哨的衝,咽下怦然的悸。
「好看就行。」
「然後呢?」今天大小姐說得算,程硯深一派從容任安排。
沈怡的目幾乎無法從他上挪開。
然後?
緩了幾秒,勉強平復加快的心跳,才拿出手機:「你坐椅子上,讓我拍兩張照片。」
站在不遠,調整著燈,也不忘安排著模特兒本人:「頂端的扣子再打開兩顆,往旁邊扯一下襯衫領子。」
Advertisement
「你下揚起來一點,眼睛半瞇。」
程硯深照單全做,但對這個作有些小疑問。
「程太太,你指導的這個姿勢似乎有些太裝了。」
「你本來不就是很裝嗎?」理所應當的語氣,沈怡眉尖一擰,對他的質疑很是不解,「頂多,也就是本出演。」
拽拽的,端著架子,散漫又慵懶。
帶著做的鏈,又添上幾分秀可餐的味道。
放縱又慾,斯文又不羈。
程硯深輕笑了聲,悻悻閉了。
哦豁,小夥伴們如果覺得不錯,記得收藏網址 或推薦給朋友哦~拜託啦 (>.
: | |
猜你喜歡
-
完結70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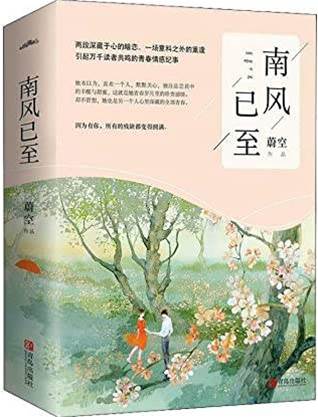
南風已至
——我終于變成了你喜歡的樣子,因為那也是我喜歡的樣子。 在暗戀多年的男神婚禮上,單身狗宋南風遇到當年計院頭牌——曾經的某學渣兼人渣,如今已成為斯坦福博士畢業的某領域專家。 宋南風私以為頭牌都能搖身一變成為青年科學家,她卻這麼多年連段暗戀都放不下,實在天理難容,遂決定放下男神,抬頭挺胸向前看。 于是,某頭牌默默站在了她前面。
22.2萬字8 6582 -
完結1080 章
婚亂流年
結婚紀念日,妻子晚歸,李澤發現了妻子身上的異常,種種證據表明,妻子可能已經……
191.5萬字8 10953 -
完結336 章
錯嫁后她成了第一財閥夫人
被渣爹后媽威脅,沈安安替姐姐嫁給了殘廢大佬——傅晉深。全城都等著看她鬧笑話,她卻一手爛牌打出王炸!不僅治好傅晉深,還替傅家拿下百億合作,成為名副其實的第一財閥夫人
64.8萬字8 53558 -
連載405 章

流產當天,我離婚了
“恭喜你,懷孕了!”她懷孕的當天,丈夫卻陪著另一個女人產檢。 暗戀十年,婚后兩年,宋辭以為滿腔深情,終會換來祁宴禮愛她。 然而當她躺在血泊里,聽著電話中傳來的丈夫和白月光的溫情交耳,才發現一切都只是自我感動。 這一次,她失望徹底,決心離婚。 可在她轉身后,男人卻將她抵在門板上,“祁太太,我沒簽字,你休想離開我!” 宋辭輕笑,“婚后分居兩年視同放棄夫妻關系,祁先生,我單身,請自重,遲來的深情比草賤。” 男人跪在她面前,紅了眼,“是我賤,宋辭,再嫁我一次。”
49.2萬字8 15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