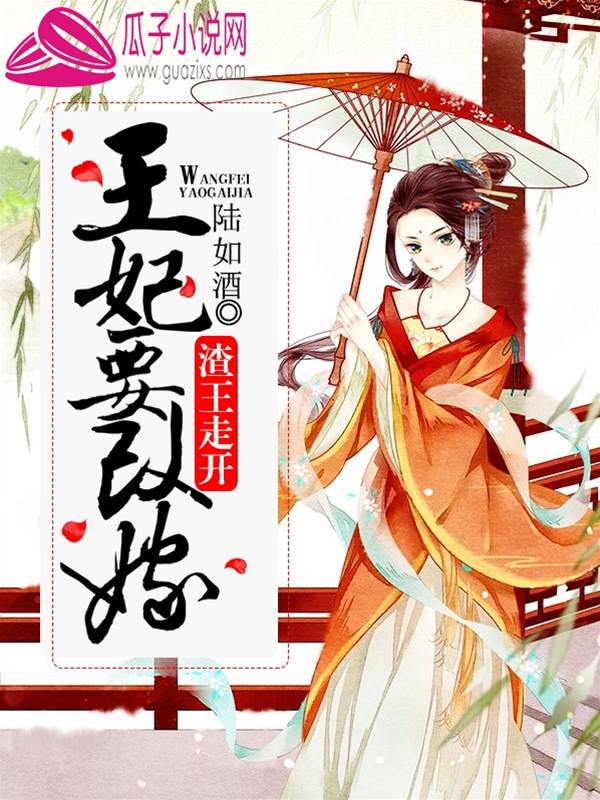《惹皇叔》 第150頁
“梨花,是我的……”他神兇狠,如同貪婪的、不知節制的野,仰起臉,發出了重的嘆息,“你是我的、只能是我的!”
烈日如火如荼,此時正當午,這一天,還有很漫長的時可以消磨……
——————————
白日西沉,殘留一點暮晚照,像是人腮上的胭脂,淺淺一抹紅,印在窗格子上,也印在傅棠梨的手上。
的手指從羅帳中出一截,指尖嫣紅,微微地抖了一下,卻沒有力氣抬起,好似被一頭野牛犁過,骨頭都碾碎了、又重新拼湊起來,這會兒還由不得做主,綿綿、黏乎乎,如同一團春泥,癱在那里,一不能。
微微睜開眼睛,眼眸里滿是水,迷離,想說話,但發不出半點聲音,哭得太厲害了,嗓子啞了,難極了,委屈得不行,扁著,眼淚”叭嗒叭嗒“地掉下來。
第74章 陛下的懲罰,吃不消……
趙上鈞的移了過來,他還在吻,吻全,見哭了,又吻的眼睛,把眼角的淚水掉。
哭起來的模樣好看極了,滴滴的,完全沒有半分平日里端莊嫻雅的正經勁頭,整個人得像一團酪,脂膩,吹彈可破,他吻著,又覺得控制不住了。
勢頭一,就覺察到了,嚇得渾發,用盡全力,勉強發出一點聲音來:“不、不……”
嚶嚶婉轉,恰似驚弓之鳥。
趙上鈞自己也知道來不得,心里頗為憾,停住索,嘆了一口氣,一手攬著,一手從榻邊案頭端過水,小心溫存地喂:“來,喝點水。”
是一碗濃濃的參湯,不知道他什麼時候出去吩咐人備下的。
Advertisement
中間他出去了兩三次,傅棠梨每每以為已經了結,回頭他馬上又來了,提刀上陣,好似把當作生死仇敵一般,殺進殺出,一次又一次,毫不手。
原來早先他都是相當節制的,至今日,才放開手腳,完全施展一番。
到后面傅棠梨都暈厥過去了,迷迷糊糊的,整個人在巫山云雨里翻轉,魂兒都飄沒了,末了,也不知道他是如何收拾殘局、如何清理戰場、又如何抱沐浴干凈……打住,不能再想了,頭上要冒煙了。
喝了一碗參湯,稍微緩了一點神過來,想著方才的形,又覺得頭皮發麻,窩一團,氣息微弱地啜泣著:“……我會死的,我會被你弄死的,可再不能了。”
趙上鈞“哼”了一聲,角帶笑,咬牙切齒,低聲應道:“說來正好,我已經想了很久了,朝也想、暮也想、要你死在我手里,果然有今日,可不是你欠我的嗎?”
傅棠梨噎了一下,喃喃地道:“我好后悔,我真傻……”
趙上鈞此刻心滿意足,溫地了的頭頂,發出了一個表示疑問的:“嗯?”
傅棠梨搭搭,哭得眼睛都紅腫了,氣得要命:“是我錯了,早知道,當初就不該招惹你,好好地做我的太子妃,也不必日日吃這苦頭,這、這……可太難了!”
當日在永壽鎮上,青虛子哄說,玄衍魄強健、氣旺盛,諸般皆勝于常人,本以為是隨口那麼一提,這會兒又回想起來,真真人倒一口氣,原來師父說的都是大白話。
這可太難了,沒人得了。
如今這當口上,提及趙元嘉,趙上鈞可以做到心平氣和,甚至還能耐著子,放下段,低低聲的,試圖哄騙:“太子妃有什麼稀罕的,朕讓你直接做皇后了,不好嗎?”
Advertisement
“不好。”傅棠梨鼻尖通紅,云鬢散,一副頹廢不堪重負的模樣,有氣無力地道,“我單力薄,不堪擔此重任,此事就此作罷了,還請陛下另擇良偶,放過我一馬吧。”
趙上鈞屈起手指,在的腦門上輕輕敲了一記:“瞧你這沒出息的,說什麼胡話,我看你剛才的時候,分明也是快活的,一直抓著我……”,這話才說到一半,忽然收了口,趕去抱,“梨花、梨花!”
原來是兩眼一閉,
得又暈厥過去了。
趙上鈞好不容易把掐醒,這下子真的惱怒了,含著淚花,咬著,臉蛋漲得紅紅的,氣吁吁,扭過頭去,不看他。
“走開,下去,這如今是我的房,不喜歡你,別杵在我面前,煩人得很。”氣鼓鼓的,用沙啞而的聲音撒著。
“對不住,讓你苦了。”他鎮定自若,“你也說過,我這門手藝不行,無妨,日后多學學,我能比現在更進一些,務必你中意。”
這個男人,他在說什麼胡話?傅棠梨聽得頭發都要豎起來了,氣得又要張口咬他。
趙上鈞把摟在懷里,讓咬,無非也就是蹭點口水在他膛上,答答的,有點。
他一邊,一邊輕聲哄著,今天一時忘,放開手腳,委實過于魯些了,他自己也覺得心疼,只能給賠不是,說什麼下次輕一些、快一些、一些之類,豈料傅棠梨并沒有得到安,反而又哭了起來。
就這麼黏黏糊糊的,到了天黑,趙上鈞好不容易把傅棠梨哄住,不哭了,雖然眼睛還是腫腫的。
害得很,掙扎著起,讓趙上鈞替穿了小裳,又披了一件輕羅衫,好歹遮住上殷紅的痕跡,的雪白,一掐就是一個印子,這會兒上上下下都紅了,沒一好的,一就要倒一口氣。
Advertisement
趙上鈞小心翼翼地抱著,當是三歲稚兒,不能離手。
已經到了戌時,案頭香熄,燈火燃起,燭溫存,秋夜微涼,但這房中炙熱的春意卻尚未退卻,空氣里還殘留著他野的腥膻味,宛如濃郁的石楠花。
傅棠梨聞得面紅耳赤,氣地捂著鼻子,他把窗牖支起,風。
頃,趙上鈞命人傳膳進來,他抱著傅棠梨喂了些清淡爛的吃食。懨懨的,吃得不多,他又費了好大力氣哄。
就在兩個人絮絮噥噥地說話著,卻聽見玄安在外頭用力地咳了好幾下,小心翼翼地道:“師兄,傅家的大夫人來了,要見懷真師姐,依您的吩咐,任何人不許進,但這會兒在外頭嚷嚷得厲害,還請師兄示下。”
趙上鈞目一,不知何故,沉了一下。
傅棠梨勉強從趙上鈞的懷里掙出來,巍巍地支起子:“大伯母,大晚上過來?”了幾下,猶猶豫豫的,還是道,“保不齊有什麼要事,讓進來吧。”
但眼下這屋子里有個礙眼的東西,高大、偉岸,一覽無余,聲勢驚人,萬萬不可被外人所見。
蹙著眉頭,指了指一側的碧紗櫥,示意趙上鈞回避一下,還用腳尖嫌棄地撥拉了一下他搭在榻上的裳。
趙上鈞挑了挑眉,端坐不。
傅棠梨瞥了他一眼,眼角嫣紅,帶著一點淚盈盈,又地了他一下。
趙上鈞這才起,拾起裳,施施然走到碧紗櫥后去。
頃,玄安領著嚴氏進來。
傅棠梨待要站起相迎,才一著力,就“嘶”的一聲,了下去,扶著腰,皺著眉頭,直氣。
嚴氏慌忙上前:“哎呦,你這怎麼了,可是傷到哪兒了?”
Advertisement
傅棠梨也不用裝,這會兒說起話來,聲音綿綿的,還打著兒:“今兒早上觀里出了點事,哄哄的,我被人撞了一下,閃著腰了,就這會兒有些疼,不打,養兩天就好,只是大伯母要恕我失禮,不能起。”
“不必、不必,你坐著,可別了。”嚴氏擺了擺手,念了一聲“福生無量天尊”,的臉上剛剛還帶著焦慮之,這下子倒像是松了一口氣的神態。
“我這趟過來,可不就是擔心這個嗎,今兒大早上起,京城中就到戒備,不許人走,到晚上才除了令,你大伯從署回來,說是有反賊殺上元真宮,還炸毀了許多屋舍,火燒了半邊天,嚇人得很,我就慌慌地過來了,如今看你沒大礙,我心里這塊石頭才算是放下了。”
大伯母還是如從前一般,噼里啪啦一堆話,傅棠梨聽了莞爾,也不怪來得不是時候,抬手請坐下慢慢說話。
玄安出去端茶。
嚴氏坐下,這才打量了一下四周的形,還算滿意,點了點頭:“你這住,倒是合宜,就是太素凈了些,你青春年的,不必如此守,依我看,家擺設多添置些,往后住著呢,心里也舒坦。”
傅棠梨抿,淺淺地笑了一下:“我出家修道,比不得先前人間富貴,這樣就好。”
說到這個,嚴氏一拍手,看了看左右,見四下無人,低了聲音:“幸虧你出家了,和幽王了干系,知道嗎,幽王病故,圣上命幽王妃殉葬。”嘖嘖了兩聲,面有余悸之,“你說,多慘。”
傅棠梨這才知道林婉卿竟被勒令殉葬,記起了當日趙上鈞之言,看來這個男人果然記仇,言出必行的。
心里一陣唏噓,搖了搖頭,也不知該說什麼。
哦豁,小伙伴們如果覺得不錯,記得收藏網址 https://.52shuku.net/ 或推薦給朋友哦~拜托啦 (>.
猜你喜歡
-
完結325 章

攝政王冷妃之鳳御天下
不可能,她要嫁的劉曄是個霸道兇狠的男子,為何會變成一個賣萌的傻子?而她心底的那個人,什麼時候變成了趙國的攝政王?對她相見不相視,是真的不記得她,還是假裝?天殺的,竟然還敢在她眼皮底下娶丞相的妹妹?好,你娶你的美嬌娘,我找我的美男子,從此互不相干。
62.7萬字8 16261 -
完結668 章
毒妃傾城:王爺掌中寵
夏吟墨手欠,摸了下師父的古燈結果穿越了,穿到同名同姓的受氣包相府嫡女身上。 她勵志要為原主復仇,虐渣女,除渣男,一手解毒救人,一手下毒懲治惡人,一路扶搖直上,沒想到竟與衡王戰鬥情誼越結越深,成為了人人艷羨的神仙眷侶。 不可思議,當真是不可思議啊!
120萬字8 17247 -
完結150 章

殷總,寵妻無度
姜綺姝無論如何都沒有想到,當她慘遭背叛,生死一線時救她的人會是商界殺伐果斷,獨勇如狼的殷騰。他強勢進入她的人生,告訴她“從此以后,姜綺姝是我的人,只能對我一人嬉笑怒罵、撒嬌溫柔。”在外時,他幫她撕仇人虐渣男,寵她上天;獨處時,他戲謔、招引,只喜歡看姜綺姝在乎他時撒潑甩賴的小模樣。“殷騰,你喜怒無常,到底想怎麼樣?”“小姝,我只想把靈魂都揉進你的骨子里,一輩子,賴上你!”
37.1萬字5 11927 -
連載52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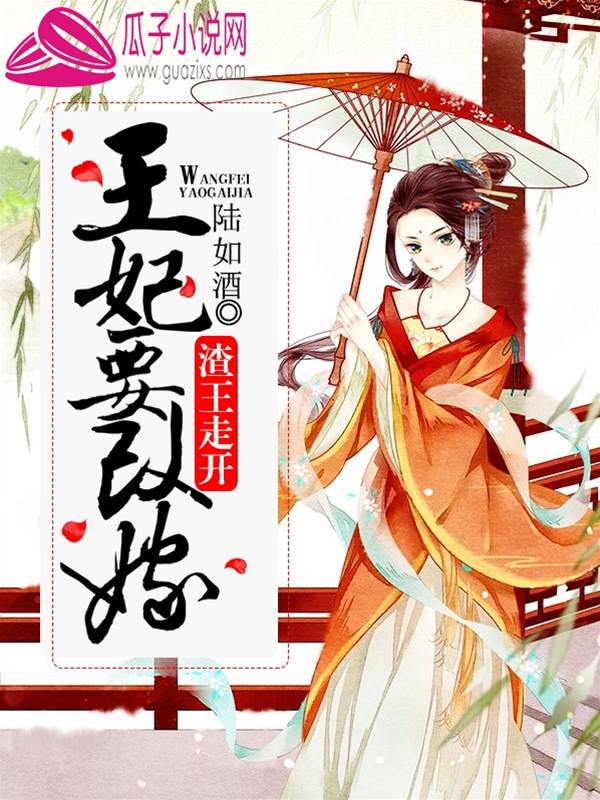
渣王走開:王妃要改嫁蘇妙妗季承翊
蘇妙,世界著名女總裁,好不容易擠出時間度個假,卻遭遇遊輪失事,一朝清醒成為了睿王府不受寵的傻王妃,頭破血流昏倒在地都沒有人管。世人皆知,相府嫡長女蘇妙妗,懦弱狹隘,除了一張臉,簡直是個毫無實處的廢物!蘇妙妗笑了:老娘天下最美!我有顏值我人性!“王妃,王爺今晚又宿在側妃那裏了!”“哦。”某人頭也不抬,清點著自己的小金庫。“王妃,您的庶妹聲稱懷了王爺的骨肉!”“知道了。”某人吹了吹新做的指甲,麵不改色。“王妃,王爺今晚宣您,已經往這邊過來啦!”“什麼!”某人大驚失色:“快,為我梳妝打扮,畫的越醜越好……”某王爺:……
99.7萬字8 13499 -
完結137 章

鶴帳有春
穆千璃爲躲避家中安排的盲婚啞嫁,誓死不從逃離在外。 但家中仍在四處追查她的下落。 東躲西藏不是長久之計。 一勞永逸的辦法就是,生個孩子,去父留子。 即使再被抓回,那婚事也定是要作廢的,她不必再嫁任何人。 穆千璃在一處偏遠小鎮租下一間宅子。 宅子隔壁有位年輕的鄰居,名叫容澈。 容澈模樣生得極好,卻體弱多病,怕是要命不久矣。 他家境清貧,養病一年之久卻從未有家人來此關照過。 如此人選,是爲極佳。 穆千璃打起了這位病弱鄰居的主意。 白日裏,她態度熱絡,噓寒問暖。 見他處境落魄,便扶持貼補,爲他強身健體,就各種投喂照料。 到了夜裏,她便點燃安神香,翻窗潛入容澈屋中,天亮再悄然離去。 直到有一日。 穆千璃粗心未將昨夜燃盡的安神香收拾乾淨,只得連忙潛入隔壁收拾作案證據。 卻在還未進屋時,聽見容澈府上唯一的隨從蹲在牆角疑惑嘀咕着:“這不是城東那個老騙子賣的假貨嗎,難怪主子最近身子漸弱,燃這玩意,哪能睡得好。” 當夜,穆千璃縮在房內糾結。 這些日子容澈究竟是睡着了,還是沒睡着? 正這時,容澈一身輕薄衣衫翻入她房中,目光灼灼地看着她:“今日這是怎麼了,香都燃盡了,怎還不過來。”
20.8萬字8.33 1493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