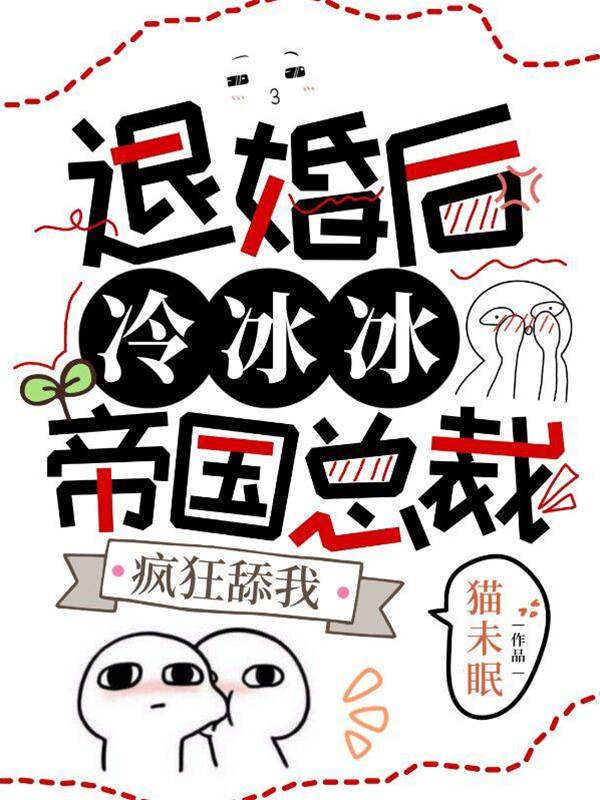《小心肝要分手!禁欲大叔纏她別走》 第287章 她沒辦法斬斷過去,拋開他不管
把安安托付好,阿全開車把夏挽星和紀蕓白送到提前定好的酒店,然后立馬去清點人手,順利的話,一早便能出發。
房間門關上,紀蕓白拉著夏挽星在沙發坐下,一肚子話要說,又不知從何說起。
最后總結一句:“星星,你干嘛還救?”
夏挽星坐在那,慢慢垂下眸子:“蕓蕓,我欠他的,我要還。”
“你欠他什麼?”
紀蕓白提起秦謹之除了厭惡還是厭惡,“當初他囚你威脅你,本就沒尊重過你半分。現在他淪落到這一步完全是自作自,你還去救他,你就不怕他有天想起以前的事了,再把你關起來?”
夏挽星沉默。
不是沒想過這種可能。
但,的命是阿冷救的。
拋開以前那些恩怨糾葛,沒有他,都不知道能不能順利生下安安。
而如今,他深陷困境,也有的原因在里面。
以前欠秦謹之的還了,但欠阿冷的,不敢說一句還清。
黎朗說他和薩在一起了,但夏挽星始終不愿相信。就算是真的,也要親口聽他承認一句。
過了許久,說:“蕓蕓,我知道我這樣做很傻,但如果我不去緬普把他帶回來,我會一輩子都良心不安。”
“良心值幾個錢。”紀蕓白著,又氣又拿沒辦法,“真要去?”
“要去。”聲音輕,卻無比堅定。
紀蕓白無奈嘆口氣。夏挽星看著弱,但打定主意要干的事誰都勸不。
頓了幾秒,起:“好吧,我給主任打個電話,把年假請了。”
聞言,夏挽星詫異看:“你要跟我一起去?”
“不然呢。”紀蕓白心卻得很,“你再跟我玩一次失蹤試試,我把你頭擰下來。這次我親自守著你,看你還敢不敢來。”
Advertisement
夏挽星心頭一暖:“蕓蕓,我就知道,你最我了。”
“別我,沒結果。我八塊腹的帥氣男模。”紀蕓白扔下一句,進去打電話了。
……
這一晚夏挽星和紀蕓白睡在一張床上,說了很多閨間的話。
一聊就到了深夜,沒睡幾個小時就被通知可以出發了。
早晨6點,們頂著寒風走出酒店,外面已經有安排好的車在等們。
車上放著兩件厚厚的士羽絨服,想來是阿全注意到夏挽星昨天穿的服太單薄,特意備的。
夏挽星朝前面看一眼:“謝謝。”
阿冷還是那張萬年不變的冰山臉,邦邦道:“沒什麼好謝的,我只是不想你冒了傳染給小爺。”
昨天還說吵死個人,今天就直接變小爺了。
夏挽星沒說什麼,就笑了笑。
紀蕓白套上羽絨服,撞了下旁邊的人,小聲說:“星星,真是什麼老板就帶什麼樣的下屬,說話一樣不好聽,黑著個臉跟誰欠他八百萬一樣。”
紀蕓白自以為音量足夠小,前面的人肯定聽不見,可阿全憑著非凡的聽力還是聽到了。
他鬼使神差地看了眼后視鏡,又鬼使神差地對著后視鏡牽了下角。
他的臉很黑嗎?還好吧。
半個小時后,車開進私人飛機停車場。
阿全帶著兩人進機艙,說:“我們先出發,老爺子的人晚一點,晚上統一集合。”
夏挽星找到座位坐下,點點頭:“謝謝。”
阿全沒回話,面無表走了。
機艙除了們還有其他人,夏挽星往后掃一眼,看到幾張眼的面孔,想來就是秦謹之手下那些人了。
紀蕓白沒一次見過這麼多保鏢,往后看一眼,又看一眼,忍不住道:“星星,果然什麼老板就帶什麼樣的人,后面那群人都好嚇人啊。”
Advertisement
夏挽星笑笑沒說話。
恐怕不是他們嚇人,而是他們和阿全的心態一樣,對這個害自己老大墜海的人沒什麼好,但迫于況,又不得不跟一起去緬普。
從京北到緬普,飛了近6個小時。
紀蕓白上飛機不久就睡了,夏挽星卻一直沒有睡意,盯著窗外逐漸明朗的云層,心緒復雜。
紀蕓白說的其實不無道理,千方百計,甚至不惜付出生命要擺秦謹之。
好不容易徹底擺了,秦謹之又失憶,這樣的況就像老天給開了后門,讓可以獨善其,過完余生。
但……
好像做不到。
沒辦法就那麼斬斷過去,拋開他不管。
縱夏挽星是鐵石心腸、狼心狗肺的人,也沒辦法把阿冷對的那些好全部抹滅。
他失憶了,他不認識,卻還是不計回報地護了一年。
300多個日日夜夜,說沒是假的。
靠著窗,突然覺得自己矛盾得可以。
旁邊傳來紀蕓白睡的輕微鼾聲,夏挽星偏頭看一眼,突然就釋懷笑了。
管他呢,矛不矛盾糾不糾結都是以后的事。
紀蕓白說的假設都是在秦謹之能恢復記憶的基礎上,如果他恢復不了記憶,他們之間就沒那麼多牽扯糾葛了,一切順其自然就好。
中午,私人飛機抵達緬普。
熱浪撲人滿懷。
紀蕓白從機艙出來,陡然到熱帶氣候的溫度,當即把羽絨服了,嘆道:“星星,托你的福,我的年假也算出國旅游一趟了。”
夏挽星被逗笑,提醒:“緬普都不算一個真正意義的國家,這里沒有完善法律,不算安全,而且這里也不槍。”
阿全走在兩人前面,聽到夏挽星的話回頭看一眼紀蕓白,問:“你會不會用槍?”
Advertisement
槍?
這對于從小生長在華國的紀蕓白來說,這玩意兒只在電視上看過,搖頭:“不會。”
阿全皺眉:“不會用槍你跟來干什麼?也不怕被子彈崩了。”
紀蕓白一聽就不服氣:“不會用槍怎麼了?我會用手刀,你們在前線沖鋒陷陣難道就不要后勤醫務了?”
阿全反駁不了,干脆就不反駁了,轉過去繼續往前走。
紀蕓白死死盯著前面男人的背影,咬牙切齒:“看不起人,他最好別落我手里,不然……”
后面的話沒說完,近30度的高溫,夏挽星覺到一涼颼颼的冷風。
看了眼前面走的人,又看了眼旁邊散發冷氣的人,心里默默為阿全點了蠟燭。
紀蕓白不是上隨便說說的人,論記仇這塊,說第二,沒人敢說第一。
阿全……希他不要落到紀蕓白手里吧。
猜你喜歡
-
完結1101 章

藺先生一往情深
曾有記者舉著話筒追問C市首富藺先生:“您在商界成就無數,時至今日,若論最感欣慰的,是什麼?” 被眾人簇擁,清俊尊貴的男子頓步,平日冷冽的眸難得微染溫色,回答:“失而複得。” - 人人都說她死了,藺先生心裡有一個名字,彆人不能提。 他走她走過的路,吃她喜歡吃的食物,人前風光無限,內心晦暗成疾。 情天眉眼寂淡:有些愛死了,就永遠不在了。 他眼眸卻儘是溫然笑意:沒關係,沒關係。 她的心再冷,他捂暖。 世人隻知商場中藺先生殺伐決斷手法冷酷,卻從不知,他能將一個人寵到那樣的地步。 - 但後來 人來人往的步行街頭,商賈首富藺先生仿若失魂之人,攔著過往行人一遍遍問—— “你們有冇有看到我的情天……” 他的情天,他的晴天。 · ·寵文·
138.8萬字8 91312 -
完結2339 章

豪門第一寵婚:總裁好難纏
五年前,她被設計和陌生男人發生關係,珠胎暗結。 訂婚宴上被未婚夫淩辱,家人厭棄,成為江城最聲名狼藉的女人。而他是手握權柄,神秘矜貴的財團繼承人,意外闖入她的生活。 從此,繼母被虐成渣,渣男跪求原諒,繼妹連番求饒。 他狠厲如斯,霸道宣告,“這是我楚亦欽的女人,誰敢動!” “五億買你做楚少夫人!” 她的生活發生了翻天覆地的變化。
234.9萬字8 141313 -
完結12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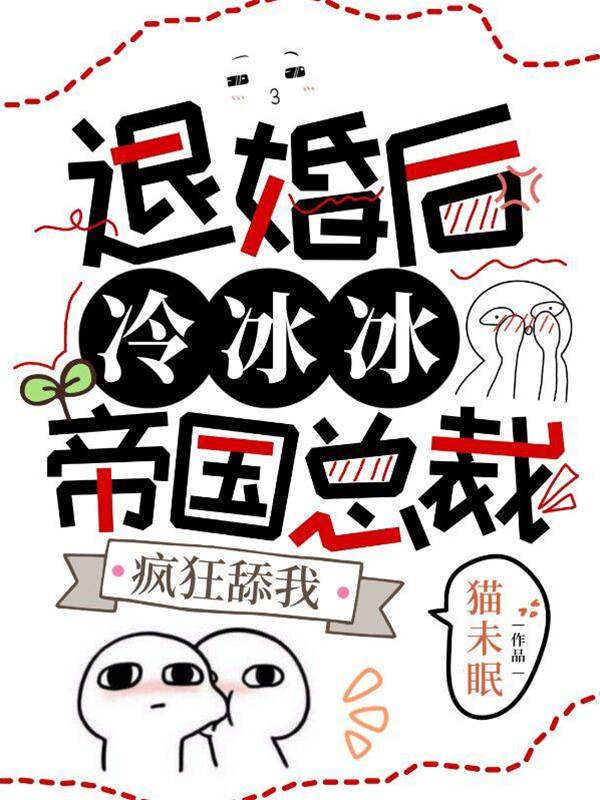
退婚後,冷冰冰帝國總裁瘋狂舔我
退婚前,霸總對我愛答不理!退婚後,某狗他就要對我死纏爛打!我叫霸總他雨露均沾,能滾多遠就滾多遠。可霸總他就是不聽!就是不聽!就非要寵我!非要把億萬家產都給我!***某狗在辦公桌前正襟危坐,伸手扶額,終於凹好了造型,淡淡道,“這麼久了,她知錯了嗎?”特助尷尬,“沒有,夫人現在已經富可敵國,比您還有錢了!”“……”
29.4萬字8 16470 -
完結181 章

清冷美人逃走後,瘋批弟弟後悔了
瘋狗和月亮強取豪奪 雙潔 姐弟戀 男配和男主一樣瘋 小虐怡情主cp:瘋批大佬x清冷閨秀副cp:腹黑公子x明豔美人霍九淵幼時在程家生活,因為一副優越的皮囊受盡世家子弟們的欺負。他恨程鳶,覺得她是他們的幫兇。一日他傷痕累累地躲在閣樓裏,程鳶不忍想幫他塗藥,他卻惡劣的脫光了她的衣服。自此程鳶看見他就落荒而逃。霍九淵被財閥家裏認領回去的時候,他在豪車上冷冷地看著程鳶:“姐姐,我會回來的。”因為這句話,程鳶做了好多年的噩夢。當她終於披上婚紗準備嫁給青梅竹馬的男友,也以為噩夢終於醒來的時候,他來了。婚禮現場,他拿槍指著她的竹馬,“跟我走,否則我殺了他。”當年如同野狗一樣的小少年,骨指冷白,腕戴佛珠,高高在上,魅惑眾生。但野狗卻長成了一條不折不扣的瘋狗。噩夢沒有醒來,噩夢剛剛開始。——沈確對女人過敏,直到霍九淵搶婚那天,他遇見了盛意。?他說給她一個月的時間,搬去和他同居,盛意覺得他異想天開。?直到見識到他種種可怕的手段,她笑不出來了。
31.5萬字8.18 3345 -
完結321 章

把她嬌養
【缺愛硬柿子美人+腹黑反差萌教授】常南意以為自己走運撿到寶了,沖動相親閃個婚,對方竟然是年輕有為的法學系教授。不僅帥氣多金,還對她百般討好,寵愛備至。 正在小姑娘被英俊老男人寵得暈乎乎時,猛然發現,相親對象搞錯了! 不僅搞錯了,這男人還是她死對頭的小叔!她忘年交老閨蜜的兒子! 天,這是什麼狗屎的緣分! 常南意想跑了,結果下一秒,就被老男人壓制在床。 姜逸:“想始亂終棄?” 常南意:“我們根本沒亂過!” 姜逸:“那可以現在亂一下。” 常南意…… 姜逸:“我的字典里,只有喪偶,沒有離婚!” 直到后來,常南意才知道,原來姜逸這狗男人已經盯了她三年,結果她卻自投羅網! (避雷:男女主都有所謂的前任,但有名無實!身心健康,1v1甜寵!有嘴!一切覺得不合理的地方,書中后期都有解釋!有招人煩的角色,但都沒有好下場!)
60萬字8 4182 -
完結797 章

車禍當天,封總在陪白月光慶生
結婚兩年,封寒對慕千初有求必應,除了一件事,他不愛她。后來慕千初撞見他和白月光相處,才知道,他不是不愛她,而是他的溫柔和呵護,全給了另一個人。所以慕千初選擇放手。一向體貼關懷的小妻子送來離婚協議,封寒對此嗤之以鼻,并放話出去:不出三天,慕千初自己會回來。直到半年后,他發現離開他的慕千初,怎麼追求者多到有點礙眼?
141.5萬字5 742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