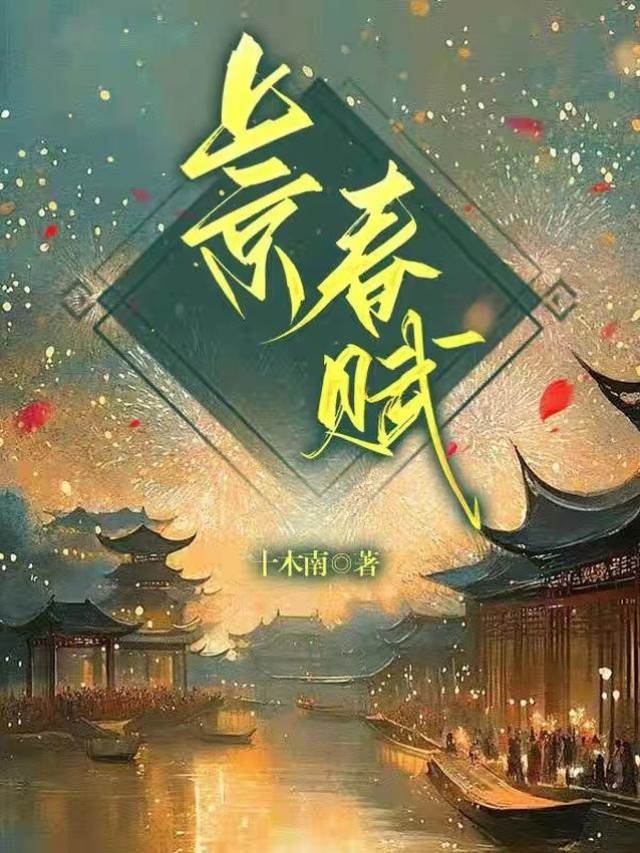《春雪欲燃》 第80章 第80章 紅痣 “當家主夫。”……
第80章 第80章 紅痣 “當家主夫。”……
說眼前是春日, 其實有些不合適。
五月的暖仍帶著春的明淨,如一泓亮的溪流,漫過檐角和庭中草木。可當它灑在上時, 卻出幾分蟄伏已久的燥意。
蕭燃便站在這片恣意的下, 武袍勾著金邊,正負手立于石階前, 同庭中的親衛代些什麽。
見到披推門, 他立刻就過來了, 一邊靴上廊,一邊指揮商家姐弟呈藥布膳, 一點也沒拿自己當外人。
這副稔的樣子, 特別像……
“當家主夫。”
沈荔扶著門扇淺淺一笑, 揶揄他。
“看來是病好了, 還有心打趣本王。”
蕭燃上前探了探前額的溫度, 眼睫一垂,見眼底和的笑意, 終是沒繃住破了功, “還笑?”
他眉頭一松,似是無奈,又似是抱怨:“你是沒看見, 今早帶你回來時, 你哥那一聲不吭的眼神,涼颼颼似要將我剮了似的。”
沈荔與他朝客室走去,聞言側首, 聲音帶著病後的微啞:“天不怕地不怕的丹郡王,竟會怕阿兄的眼神?”
蕭燃揚起眉峰,冷哼一聲:“我怕他?除了阿母, 你見我怕過誰?”
那還真沒見過。
“我是因為你,才心生憂怖。”他又低低補上一句。
那聲音幾乎融進穿廊的風裏,輕輕叩響心弦。
沈荔攏了攏襟,輕聲問:“後來呢?”
“後來就守著你汗喂藥,掖被更,連口茶都沒敢喝,就一個勁兒地反思問題出在了何。”
蕭燃拉開客室的門,與一同在席上坐下,“這樣想了許久,後悔事後沒有給你換幹爽的,穿著的睡,怎能不生涼?又想是不是草地上的夜風太冷,嗆著你了;再或許是讓你吃了不慣的炙,引發腹中不適……”
Advertisement
沈荔忙解釋:“是我自己的心病,與你無幹。”
“你還知道是心病?後來醫師診脈,說你是思慮過重,肝火虛旺,才引發此疾,沈筠這才將眼刀收回去。”
說著,蕭燃單手支著額角,擡起一手輕輕的臉頰,咬著牙輕輕道,“心裏藏著事,也不和我說,總自己一個人胡思想。是嫌我不夠心疼嗎?”
沈荔眼睫微,垂眸擡掌,輕捂住被他得緋紅發燙的臉頰。
自己放縱了大半宿,到頭來還是要蕭燃收拾爛攤子,不免有些慚愧:“有勞殿下。”
“……”
蕭燃似是噎了一瞬,索連另一只手也出來,氣急敗壞地捧起的臉,“你這是什麽話?我介意的是這個?”
難道不是嗎?
“我是心疼你不惜自己!多思傷神,最損心脈啊,沈令嘉。”
門口,商風和商靈捧著托盤和湯藥而立,目瞪口呆地看著自家清冷端莊的郎,被高大的年來去地“教訓”。
不由齊齊僵立,進也不是,退也不是。
“放下吧。”
沈荔飛速端正形,溫聲道。
商靈將藥碗和餞置于案上,角一一,拼命忍笑。
商風則頭也不敢擡,尤其不敢看蕭燃的眼神,快速布完菜,抱著空托盤頷首一禮,便邁著碎步逃也似的退下了。
沈荔實在疑:“商風為何這般怕你?”
蕭燃那一瞬的眼神有些意味深長,又有些古怪,半晌才漠然道:“不知道,或許心裏有鬼的人都怕我。”
沈荔忍不住為年辯解:“商風心細如發,勤勉斂,絕非心不正之人。你是不是……誤會他了?”
蕭燃長眉一挑,面更古怪了。
古怪中著青黑之氣,還意義不明地哂笑了一聲。
沈荔毫未曾察覺,撚起玉勺道:“你不吃麽?”
Advertisement
“氣飽了。”
蕭燃淡淡然說著,手將面前的藥碗移開,換上熬得晶瑩粘稠的碧玉粥,“先喝口粥墊墊肚子,再飲湯藥。”
沈荔只當他還在因自己不同他傾訴心事而生氣,抿一口粥,看他一眼;再抿一口,又看一眼……
“我……”
“方才……”
兩人異口同聲,又不約而同收住了音。
蕭燃似被這無意間的默契取悅,破功一笑:“你先說。”
“先前我以賑災糧為餌,出了當年殺害母親的燕子匪首。他臨死前為保家人平安,曾向告知我一個:當年洩母親行蹤,慫恿匪衆于風雪截殺的那名神人,小指側生有三枚小痣。”
沈荔已然恢複了清明,將昨夜零碎閃現的思緒驟然串聯線,擡眸道,“昨夜聽你提及,章德太子孤上有一枚可供辨認份的印記時,我便覺得……”
“那印記并非胎記,而是三枚小痣。”蕭燃瞬間會意,接過話茬。
“不錯。”
沈荔頷首,“如此一來,一切都解釋得通了——前朝舊黨需要銀錢養兵,故借燕子匪之手劫殺母親的車隊。事之後,再將燕子匪改名換姓,收為私兵,藏世家麾下為棋。這般不斷地挑起長公主與世家的相爭,待兩敗俱傷,便可趁機扶前朝脈複辟,坐收漁利。”
眸漸沉,袖中指尖也不斷絞:“只是不知先是前朝舊黨鬧事,轉投謝氏門下,還是自始至終……都是謝氏從中控。”
“別忘了,章德太子妃也姓謝。”
蕭燃擡掌覆在泛白的指節上,遞來安穩的溫度,“雖說謝敬一族已遷居蘭京,與前朝太子妃并非同支近親,但終究脈同源。”
“這只是猜測,并無實證。”
“若本王手中,正握著謝敬攬財養兵的實證呢?”
Advertisement
沈荔倏地擡頭,眼中驚瀾驟起:“是何證據?”
“這正是我要與你相談之事。”
蕭燃從懷中出一份文,夾在修長的指間揚了揚,眼尾微挑,“你先將藥喝了,我便給你看……”
話未落音,沈荔已雙手捧起面前的藥碗,仰首一口氣飲盡。
皺眉放下空碗,息著朝他出一手。
蕭燃線微揚,擡指自然而然地為抹去角的苦水漬,又撚了顆餞塞間,這才將證據遞于。
“探子順著嬰娘藏的樂坊往上查,倒還真查出點東西。的上一位恩客兼主子……哦,就是騙你叔父的那位雲游名士,乃謝敬麾下豢養的謀士。”
蕭燃指腹輕點膝頭,慢悠悠道,“你猜怎麽著?這位謀士每年經手的錢財,數額龐大到你無法想象,不是用來收編燕子匪那般私兵死士,就是替謝家做些上不得臺面的髒活。”
沈荔展開信,上方果然詳細記載了這名謝氏黨羽的人際往來,進出數目大得嚇人——
是一筆即便是蘭京世家之首的沈氏看來,也依舊難以想象的巨款。
天下最燒錢的行徑,莫過于養兵。這的確是一份鐵證。
饒是早有預,當親眼見到與祖父好的謝氏包藏禍心,竟不惜放縱匪徒向故好友的妻子痛下殺手時,的心中仍是泛起了冰冷的寒意,錐心刺骨。
謝敘知道此事嗎?
若他知曉,又是如何做到一邊與溫言相、手談論道,一邊卻為虎作倀、暗下殺手的?
“有這些還不夠。”
沈荔闔目呼吸,很快沉靜下來,“若謝敬咬死不知,將一切罪責盡數推于謀士上,亦有逆風翻盤的可能。”
蕭燃指節一頓,傾靠近了些:“我與阿姊也這麽想,所以來問問你的意見。”
Advertisement
“要麽,找到謝氏勾結前朝舊黨的鐵證。要麽……”
沈荔眼睫一擡,霎時如明乍現,清泠泠道,“從楊氏手。”
“楊窈?”
“不錯。”
四年前,那場震驚河東的案發生後,面對沈荔的質問,楊窈曾梨花帶雨地解釋:
戚氏領兵與李氏的部曲火拼時,四縱火屠殺,以至于誤傷了被囚困李氏牢獄中的楊氏全族。是為了給枉死的族人報仇,才設計奪權,反殺了戚氏全族……所做的一切,都是被的!
沈荔并非傻子,知道一個菟花般依附別人而活的楊氏孤,再如何設計奪權,也不可能將戚氏的一千部曲一夜屠盡。
一直覺得,楊氏全族死得太過蹊蹺,蹊蹺得仿佛在迫不及待地掩蓋著什麽。
或許螳螂捕蟬的背後,還另有黃雀。
直至昨日在儀殿,楊窈緒失控之下,對說了一句話——
“……楊窈說:‘大家族就是如此,什麽都要爭,什麽都要搶。雪沒有姊妹,又怎會懂我的痛?’”
聽完沈荔複述此言,蕭燃擰眉沉:“此話有何不對?”
“楊窈是楊氏嫡,只有三位阿姊、兩位兄長,并無妹妹。”
沈荔緩聲道,“昨日見時,我心緒煩,以至于忽略了諸多細節,事後冷靜下來才覺蹊蹺:楊窈素有溫婉賢名,又是衆星捧月的、負皇後之命的貴人,楊氏上下呵護尚且不及,何來‘爭搶’之苦?”
這便有些意思了。
蕭燃微瞇眼眸:“所以定有,令對自己的族人有恨,恨不得他們去死。”
“非但如此,只怕那時便已與謝氏勾結。”
怎會忘了?
那年的冬天,謝敘與在曹公的梅園初見,也一并見到了跟著養傷的楊窈。
如此一來,戚氏一族背後的那只黃雀,便有跡可循了。
思及此,沈荔心間一沉,喃喃道:“若楊窈份存疑,更兼弒親背友之罪,又豈配母儀天下?”
蕭燃懂了:“若楊氏確系罪徒,那麽力主迎宮,又與前朝舊黨牽扯不清的謝氏一黨,便難逃其咎。”
“不錯。唯有從楊窈斬斷源,方能徹底扳倒謝敬……”
沈荔說著,擡眸撞進一雙含笑的桀驁眼睛,不由一怔,“怎麽了?可是我……說得太過了?”
蕭燃只是笑著看。
“我信你是真的振作起來了。”
他手了的發頂,帶著逗弄的氣,語氣卻很認真,“你運籌帷幄的樣子,像是在發。”
沈荔心尖一跳,忙低頭勺子,又抿口粥水。
忙忙碌碌半晌,才擡起眼來,遲疑道:“其實,我沒有你說的這般好。”
“怎麽就不好了?在我眼裏、心裏,你就是世間最好、最聰慧的子。”
蕭燃又靠近了些,低頭看躲閃的眼睛:“願意同我傾訴一二嗎?”
沈荔指腹挲勺柄,沉了好一會兒,方將四年前那樁舊事娓娓道來。
開口直面錯誤,并沒有想象中那麽艱難。
并未提及李氏與戚氏的名號,只撿了如何救下楊窈,又如何出于不忍、給指了一條生路的重點,說了個大概。
“……我不殺伯仁,伯仁卻因我而死。是我識人不清,恃才傲,才釀就如此惡果。”
沈荔這樣說著,擡起哀傷得近乎破碎的眼睛,靜靜地著蕭燃,“去年在學宮,你說我教不出好學生,我生氣了。可只有我自己知道,我沒有資格生氣,我只是被中痛,下意識選擇逃避而已……”
最佩服蕭燃的一點,便是他有直面失敗、矯正錯誤的勇氣。
做不到。
“我就是這樣一個識人不清,剛愎自用之人……”
“沈荔,人非聖賢,孰能無過?你不必對自己這般苛刻。”
蕭燃輕輕打斷的自厭,指腹碾過的眼尾,聲音帶著一貫的明朗張揚,“以前阿父說過,人總是要跌跤後,才知道痛;要犯過錯,才懂得長。犯了錯就改嘛,去面對、去彌補,多大點事!你看我,十六歲時打了那麽大一場敗仗,不也照樣活著?”
沈荔著他故作輕松的笑,角了,卻只品出了無盡的酸:“這一點也不好笑,蕭燃。”
知道他那幾年很難熬,很難熬……
眼前所謂的輕松,都是用命搏出來的。
“說真的,和我捅出的簍子相比,其他的都不算事兒。”
蕭燃低下頭,與平視,又了的後頸,“我啊,就是名得太早了,沒吃過虧。那時殺上癮了,拿手下的人命當棋子看,總覺得十四歲能贏,之後的每一次也能。那時我真覺得,老子天下第一……結果你也知道了,我吃到了人生中最慘痛的一次教訓。”
沈荔沒說話,只是悄悄移過去一寸,握住了他的青筋凸顯的手。
蕭燃一怔,反手回握住,深吸一口氣,又徐徐吐出。
“說是三萬兵,其實也不全是。裏頭有五千步族,一千騎兵,是幾位仰慕我聲名的兄弟帶來的部曲。兩千出自江氏……就是你那學生,江什麽……”
“江月。”
“對,這兩千是的兄長帶來的部曲。還有兩千步卒,一千騎兵,是戚氏二公子帶來的私兵……”
“……”
沈荔的聲音,驀地有一輕:“你說的,是哪個戚氏?”
“陳留戚氏,怎麽了?”
蕭燃問,“你認識他?”
猜你喜歡
-
連載47 章
情絲
我是無情道中多情人
53.8萬字8 9569 -
完結268 章

死後第一天,乖戾質子被我親懵了
【雙潔 甜寵 雙重生 宮鬥宅鬥】 【絕美嬌軟五公主×陰鷙病嬌攝政王】 前世,她國破家亡,又被那個陰鷙病嬌的攝政王困在身邊整整兩年。 一朝重生十年前,她依舊是那個金枝玉葉的五公主,而他不過是卑微質子,被她踩在腳下。 西楚國尚未國破,她的親人母後尚在,一切都沒來得及發生…… 看著曾被自己欺負的慘兮兮的小質子,楚芊芊悔不當初,開始拚命補救。 好吃的都給他。 好玩的送給他。 誰敢欺負他,她就砍對方的腦袋! 誰料病嬌小質子早已懷恨在心,表麵對她乖巧順從的像個小奶狗,結果暗戳戳的想要她的命。 少年阿焰:“公主殿下,你喂我一顆毒藥,我喂你一隻蠱蟲,很公平吧!” 然而此時的少年並不知道,上一世的他早已對小公主情根深種,那位已然稱霸天下的攝政王,豁出命也想要給她幸福。 攝政王對不爭氣的少年自己氣的咬牙切齒:“你要是不行換我來!”
48.9萬字8.33 15703 -
完結150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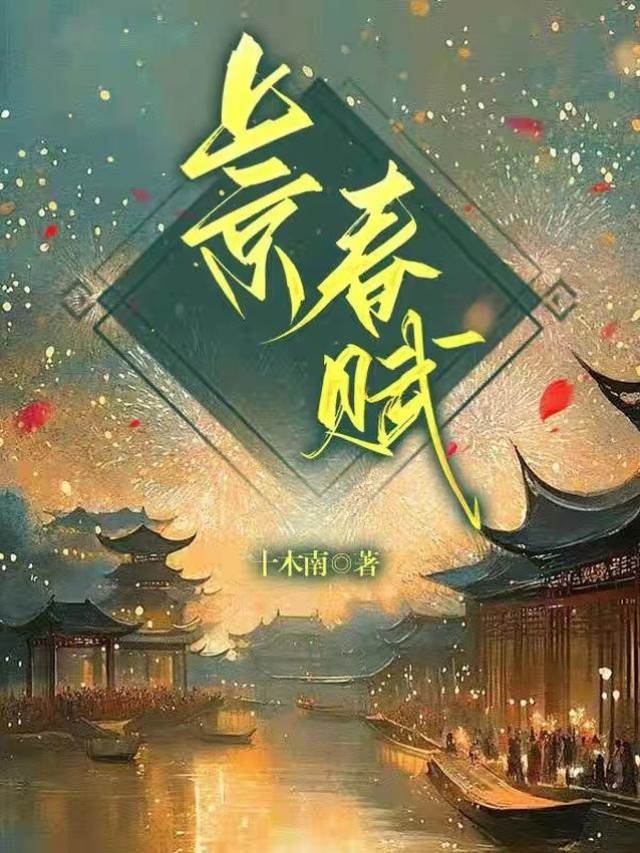
上京春賦
【純古言非重生 真蓄謀已久 半強取豪奪 偏愛撩寵 情感拉扯】(已完結,本書原書名:《上京春賦》)【甜寵雙潔:嬌軟果敢小郡主VS陰鷙瘋批大權臣】一場陰謀,陌鳶父兄鋃鐺入獄,生死落入大鄴第一權相硯憬琛之手。為救父兄,陌鳶入了相府,卻不曾想傳聞陰鷙狠厲的硯相,卻是光風霽月的矜貴模樣。好話說盡,硯憬琛也未抬頭看她一眼。“還請硯相明示,如何才能幫我父兄昭雪?”硯憬琛終於放下手中朱筆,清冷的漆眸沉沉睥著她,悠悠吐出四個字:“臥榻冬寒……”陌鳶來相府之前,想過很多種可能。唯獨沒想過會成為硯憬琛榻上之人。隻因素聞,硯憬琛寡情淡性,不近女色。清軟的嗓音帶著絲壓抑的哭腔: “願為硯相,暖榻溫身。”硯憬琛有些意外地看向陌鳶,忽然低低地笑了。他還以為小郡主會哭呢。有點可惜,不過來日方長,畢竟兩年他都等了。*** 兩年前,他第一次見到陌鳶,便生了占有之心。拆她竹馬,待她及笄,盼她入京,肖想兩年。如今人就在眼前,又豈能輕易放過。硯憬琛揚了揚唇線,深邃的漆眸幾息之間,翻湧無數深意。
25.6萬字8 299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