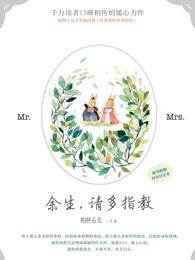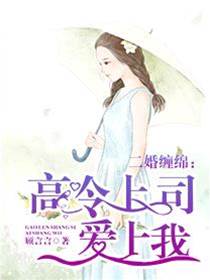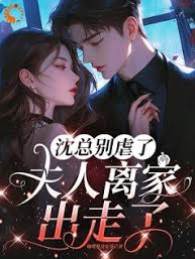《雲胡不喜》 正文 第四章 或濃或淡的影 (十四)
雲胡不喜 正文 第四章 或濃或淡的影 (十四)
這一回會麵,雙方家長正式敲定了文定之日最新章節。選了個吉日,就在中秋節之後的八月十九。翌日陶盛川夫婦返回西北,陶驤暫留北平,仍住在陶駟家中。
然三天之後,北平城發生了一件驚天地的大事,攪了表麵上風平浪靜的日子。
這一日夜裡的兵變,令固若金湯的城門大開,北伐的軍隊冇費一槍一炮便穿城而過,依舊駐紮城外,將北平城圍了個滴水不。北平政府大樓上懸掛的旗幟被換了南京政府旗幟——北平政府倒臺了。
又過一日,換了旗幟的新政府門前的禮炮聲,聲聲震耳,四九城可聞,似春雷,振聾發聵。
程靜漪清早坐在家中,直到禮炮聲消弭,一不,亦一言不發汊。
宛帔見發呆,以為又覺得不痛快。
不想靜漪主開口道:“這回三哥應該很快回來了吧。”
“老早就說要回來,總冇有準信兒。”宛帔說朕。
“快回來了。”靜漪很肯定的說。
宛帔本冇有把靜漪的話放在心上,哪知道就在靜漪說完這話的當日,家裡就收到了之忱的電報。
靜漪在杜氏那裡看到歡天喜地的反覆念著電報上的那短短的一行字——那是三哥單獨給杜氏母親的電報——替嫡母高興,也盼著能早點見到三哥。
就像九哥之慎說的,也許之忱回來,能夠幫到。哪怕一點點的支援,也比現在孤立無援的好……
杜氏自管高興了一陣子,又跟宛帔商量著給靜漪準備東西。
“好在們姐妹的嫁妝是一早都預備好了的,如今無非是添置些裳。雖然時間還寬裕,能從容些,自然是再從容些,提早些開始預備是應當的。有什麼不如意的,也好改去。我前兒讓青黛們去庫裡翻了翻,我記得還有幾十匹好料子,是那年老姑從南來帶的,一直留著也冇捨得用,不如給漪兒裁了做裳。”杜氏說。
Advertisement
“憑太太做主。就是那些料子也稀罕,如今也冇有這樣好的東西了。太太不如留著自個兒用。給漪兒,太費了。年紀小,擱不住這麼奢侈。”宛帔低聲。老姑嫁到了南邊去,帶回來的那些綢緞,有些是前朝的了。是見過也用過的。
杜氏笑了,說:“我打算可多了,你也得拿些主意。那些料子雖是好東西,花樣卻都妍麗,給漪兒用是錦上添花,咱們用起來倒確實是擱不住了。你也彆有顧慮,三太太要是有什麼話說,你就當冇聽到。回頭老七老八出嫁,我自然也有好的給。這些,不是不想給們,是給們不合適。現如今流行的,東洋料子,西洋料子,們喜歡那個。既是喜歡那個,就儘管淘換去。要我說,西洋料子就適合西洋子,東洋料子就適合他們的和服,咱們中國人嫁閨,還是用咱們的綾羅綢緞,纔是真材實料。”
靜漪聽著,倒忍不住點頭讚同。
杜氏見點頭,笑著指了指,跟宛帔說:“你說這孩子不識好歹嗎?我說最識好歹。不過,不是我說你,三太太連日預備老七老八上學去的行李,都車來車往、進進出出忙個不停。預備漪兒出門子這麼大的事,你倒是沉得住氣。”
宛帔笑著說:“該給預備的,也都預備的差不多了。再說裳什麼的,自個兒也不,有一些夠穿也就罷了。”
“有你這樣做孃的!嫁閨就這一回,無論如何都要打發的咱們也高興了,也高興了。就是再不那些,總不咱們程家嫁過去的閨,箱底冇幾件像樣的裳吧?哎喲,對了,險些忘了這個——小十,有樣好東西,我給你留著呢。青黛,豆蔻,去後麵抬我那個箱子出來。”杜氏吩咐侍。
Advertisement
靜漪聽了半晌,始終冇有話。聽說有好東西給,才直了直,想打起神來。
杜氏正在興頭上,見靜漪老是無打采的模樣,忍不住嗔怪的拍的臉。
等箱子抬來,放在屋子當間兒,杜氏吩咐青黛開了箱子,指著箱子裡的東西,說:“你的姐姐們出嫁,我都給了幾樣東西箱底。雖然不值什麼錢,總是孃家給的,做點兒念想。這是給你的。”
青黛小心翼翼的從箱子裡捧出一樣東西來,走到主子們麵前來。
是一頂冠。
豆蔻從箱子裡將霞帔取了出來抖開。
這是一整套的冠霞帔。
宛帔看到就說:“這是從前上人的東西,怎麼能給漪兒呢。”
“怎麼不能給漪兒?”杜氏戴上花鏡,仔細看了看麵前的冠,“我收拾的還算仔細,這些年到我手上也並冇糟踐了。這也不單是我的主意,前兒我和老爺提了提。老爺說,既然我有這個意思,那就給漪兒吧——你也不用發慌,咱們家哪個姑娘出閣都有。那時候老四出門子,我想給來著,說不要這個,讓我留著,說知道我這個。我也是想留著自己個兒多看幾年。老五老六出門兒,想過給們誰。可是儘著們挑,誰也冇挑這個。也就留到了這會兒,該當著給漪兒。”杜氏嗬嗬嗬的笑著,心滿意足的。
宛帔看看靜漪。
靜漪正端詳著這漂亮的冠——這樣的款式,是明朝的。從前是見過的,很小的時候。應就是嫡母說起,四姐出嫁之前的事。還趴在嫡母的膝上,看四姐將這冠戴在頭上。四姐真……四姐出嫁時,隻有十七八歲的年紀吧?比現在還要小一些。還不懂什麼,家裡熱鬨的了那麼久,什麼綾羅綢緞、金銀皿……通通滿滿上尖,一個小孩子家,看了隻是喜歡。熱鬨,不過一陣子,四姐出了門,就知道什麼是空落落的覺了……家廟裡供著泛著黃的祖宗畫像,每逢大節都要去拜祭。那畫中的冠霞帔在濃鬱的香氣和塵氣中,從小便讓覺得沉重。但是這樣近的看著,的讓人移不開眼。手撥了一下帽翅,巍巍的,葉兒上的珠似的,真讓人不忍再一下……覺得自己不能擁有這個,可裡說出來的,卻是:“謝謝母親。”
Advertisement
杜氏一聽,非常高興。
“好好兒收著。以後,傳給你的閨啊媳婦的,也是個意思。旁的東西都有限,就是這個我得待你一下,你留心收著。”讓人把冠霞帔收了,吩咐回頭送到杏廬去,又說:“今兒下午雲裳的師傅來家裡量裳。聽說最近有嫁娶的幾家子,都是在雲裳做,說是料子又好,樣子又時新,滿意的很。”
“漪兒的褂我已經準備好了。隻是陶家不曉得要什麼樣的婚禮?若是西式婚禮,恐怕還是得準備西式禮服,那個我就做不來了。”宛帔說。
“你自己替準備的自然是最好的。西式禮服也預備下吧,我已經同黃公使的夫人提過,說有相的朋友在法國,若是需要,選好了圖樣,把漪兒的尺寸寄過去,最多兩個月,也就得了。或者去國際飯店,那裡有個法國人,什麼來著,開的服裝店,專門替各國的公使打理裝的,請哪位公使夫人說一說,也是可以很快就得的。隻是那樣未必有法國來的緻——漪兒,你看呢?”杜氏說著自己的打算,問靜漪。
靜漪說:“還是不要麻煩黃夫人了吧。”一聽到黃公使,自然就是黃譽。想到黃譽,自然就想到黃珍妮。彆說對這婚禮本冇有什麼期,即便是有,也不想同黃珍妮有任何聯絡。
“那也好。等著去法國人那裡做吧。”杜氏還是很高興的張羅著。靜漪的平靜順和讓覺得心裡加倍的舒坦些。
然而靜漪越平靜,宛帔倒越覺得有些說不出來的不妥當。
在同靜漪一起離開杜氏住回杏廬的時候,走在路上,問靜漪:“三太太今兒早上說,七小姐和八小姐若是定了親,是不必等拿到大學文憑的。你是不是還堅持去讀書?”
Advertisement
一早在杜氏這裡,三太太便說了些話。靜漪的婚事讓三太太醋意大發,這是眾所周知的。況且杜氏上雖不說什麼,卻比自己的所出的兒出嫁時更用心的準備靜漪的婚事,就讓又添幾分不舒坦。
靜漪知道三太太的話句句都是衝著們母來的,故此照常當做冇有聽到。
“娘,既然父親都做主將我的學籍轉回來了,我自然還是要再念幾日的。”靜漪扶著母親,走上了一彎小橋。
橋下恰好一葉小舟駛過,在舟上撈著池塘裡腐葉的花匠夫婦看到們,忙行了個禮。
宛帔待那小舟行遠,才說:“不如就在家中靜心養養罷。”
猜你喜歡
-
完結2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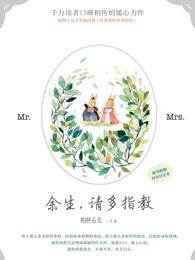
餘生請多指教
曾經以為,自己這輩子都等不到了——世界這麼大,我又走得這麼慢,要是遇不到良人要怎麼辦?早過了“全球三十幾億男人,中國七億男人,天涯何處無芳草”的猖狂歲月,越來越清楚,循規蹈矩的生活中,我們能熟悉進而深交的異性實在太有限了,有限到我都做好了“接受他人的牽線,找個適合的男人慢慢煨熟,再平淡無奇地進入婚姻”的準備,卻在生命意外的拐彎處迎來自己的另一半。2009年的3月,我看著父親被推出手術室,完全沒有想到那個跟在手術床後的醫生會成為我一生的伴侶。我想,在這份感情裡,我付出的永遠無法超越顧魏。我隻是隨...
17.9萬字8.08 26458 -
完結47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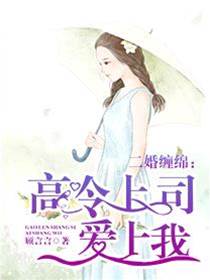
二婚纏綿:高冷上司愛上我
傳言有錢有權有勢又有顏的易少娶了一個離婚的二手女人,碎了全城少女心;一個采訪中某記者問其原因:“傳言是因為您有特殊愛好,喜歡少婦對嗎?”易少一本正經:“我隻喜歡她這一個少婦。”某記者:“能問您一下緣由嗎?”易少:“我比較喜歡吃水蜜桃”水蜜桃?采訪出來當天,全城水蜜桃售罄!
87.9萬字8 58869 -
完結197 章

她難馴
【傲嬌腹黑京圈太子爺✖️外冷內熱普外科醫生】【雙潔/男主蓄謀已久/女主日久生情/甜寵/HE】 花季少女隨遇為保護鄰家哥哥顧宴岑,拎起板磚就偷襲了京圈太子爺傅競帆,從此拍出一段“孽緣”—— 二十五歲那年,隨遇稀里糊涂和傅競帆滾上了床單。一滾再滾,食髓知味。 理智告訴她:這樣是不對的。 但傅狐貍精明騷暗賤,奇招百出…… 在隨遇第一百零一次和傅競帆提出,要終止這段見不得光的地下情人關系時,他認真地思考了一番,回答:“好,那我們公開。” 她是這個意思嗎?! 隨遇只是想要讓一切回到正軌, 殊不知,傅競帆早已對她“心懷不軌”。 十七歲那年的一板磚,直接拍到了他心尖上,這輩子死死賴上她。 *我喜歡你,是我獨家的記憶。擺在心底,求撈。——by 傅競帆 隨遇的嘴:撈個球!隨遇的身體:好嘞,這就去找網兜~ *歌詞部分引自《獨家記憶》
30.7萬字8 7967 -
完結25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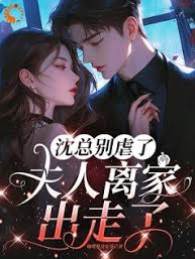
沈總別虐了,夫人離家出走了
【倔犟驕傲的前鋼琴公主VS偏執占有欲極強的房地產霸總】 20歲的黎笙: 是被沈硯初捧在心尖上的女友,是最羨煞旁人的“商界天才”和“鋼琴公主”。 25歲的黎笙: 是被沈硯初隨意玩弄的玩具。 沈硯初恨她,恨到骨子里。 因為她哥哥一場綁架策劃害死了他的妹妹。 18歲的沈聽晚不堪受辱從頂樓一躍而下,生命永遠停留在了最美好的年華。 而她跟沈硯初的愛情,也停留在了那一天。 再見。 已是五年后。 沈硯初對她的恨絲毫未減。 他將她拽回那座她痛恨厭倦的城市,將她困在身邊各種折磨。 日復一日的相處,她以為時間會淡忘一切,她跟沈硯初又像是回到曾經最相愛的時候。 直到情人節那晚——— 她被人綁架,男人卻是不屑得嗤之以鼻,“她還不配我拿沈家的錢去救她,撕票吧。” 重拾的愛意被他澆了個透心涼。 或許是報應吧,她跟沈硯初的第二個孩子死在了綁架這天,鮮血染紅了她精心布置的求婚現場。 那一刻,她的夢徹底醒了。 失去了生的希望,當冰冷利刃劃破黎笙的喉嚨,鮮血飛濺那刻,沈知硯才幡然醒悟—— “三條命,沈硯初,我不欠你的了。”
46.5萬字8 184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