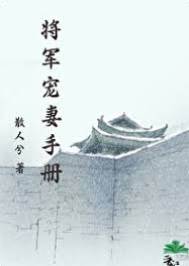《鳳月無邊》 第189章 “小小”的教訓
也不知過了多久,盧縈聽到頭頂上傳來一個冰冷的聲音,“起來吧。”
盧縈恩了一聲,站了起來。起先是準備應得諂一點的,可後來想到自己不是還在妒忌嗎?因此那一聲應答,便矜持起來,傲驕起來。
劉疆還在盯著,盯了一陣後,他頭也不回地低聲命令道:“去準備吧。”
“啊?”盧縈一怔擡頭時,只見站在門外的郭允已朗聲應道:“是。”
劉疆對上盧縈詫異不解的眸,臉上毫無表,他彷彿看一個陌生人一樣地盯了盧縈一眼,朝一個僕人命令道:“拿件黑袍給。”
盧縈一怔,這時,僕人已把裝著裳的包袱送到了手裡。盧縈暗暗蹙了蹙眉,老實地接過,轉步廂房。
不一會,再出來時的盧縈,便如一個一襲黑的冷峭年了。
劉疆不再向看來,袖一甩命令道:“走。”
衆人無聲地跟在他後,走下了閣樓。
樓下地坪中,站了十幾個便服護衛,而此刻,這些護衛都換上了一襲黑。在盧縈過來時,有人遞給了一副面巾,然後又遞給了一匹馬。
上次從武漢到那一路,盧縈得了囑咐,已學會了騎馬。此刻一襲黑,混在衆騎士中,臉上蒙著面巾,頗像個長期生活在黑暗中殺人放火的冷殺手了。
一出莊子,又圍上了一排黑人,這前後幾十個黑人無聲地籌擁在劉疆側,帶著一種難以言狀的肅殺!
不一會,劉疆上了馬車。一行人在黑暗的巷道中無聲無息走了一會後,漸漸的,前方出現一片河灘,卻是來到了河邊上。
河邊上,早就數十隻黑的快船,也不知是誰一聲唿哨,只見那快船中,無聲無息地走出了上百個同樣打扮的黑人。
Advertisement
這時,劉疆下了馬車。他剛下馬車,同樣穿上了黑,臉上圍著黑巾的郭允便拿過一件黑披風,把它披在劉疆上。
穿上黑袍後,劉疆給自己戴上一頂紗帽,回過頭來,面無表地盯向正一臉霧水的張著的盧縈。
盧縈對上他的目,連忙按下心中的疑,快走一步站到他側。
便這樣,劉疆左有郭允等人,右伴著盧縈,跳了一隻快船上。
隨著衆黑人進,劉疆低低說了聲,“出發!”聲音落下,快船如箭般飛馳而出。
數十上百隻漆黑的快船,這般無聲無息的走在河道中,饒是天上彎月如鉤,卻也著種說不出的詭異。
衆船駛得很快,不到小半個時辰,便進河中流。就在這時,郭允手放在脣邊,低低嘬出聲,隨著他這一聲嘯,衆船悄無聲息地四散而開,像是雨滴落河水中,完全溶了黑暗,再也不可見,不可尋。
被衆船籌擁的中央,劉疆面無表地看著河道前方。夜風吹起他的外袍獵獵作響,高大偉岸的男人,這一刻,形直如這河道兩側的山峰般,沉凝中著神,同時又帶上了幾分陌生和寒。
盧縈站在他側,不自地擡頭看向他。有很多話想問,可四下毫無聲息,也不敢吱聲。
夜,漸漸深了。
慢慢的,月上中天。
慢慢的,彎月西斜。
盧縈把手捂在脣上,小小地打了一個哈欠。再次擡頭看向站在前的男人,這個按道理應該比更養尊優的男人,一直到現在都沒有一下,那影如此沉穩,又如此的寒凝。彷彿他這樣不言不語,可持續千年。
Advertisement
就在一陣河風拂起他的袖時,突然的,郭允低聲說道:“來了。”
盧縈順著他的目看去。
只見河的另一頭,出現了十數個點。那點隨著船隊越來越隊而越來越亮,直把這個暗的天地間都照亮了許。
郭允說出那兩個字後,衆人依然一不,劉疆只是略略擡頭,冷冷地看著那些船隻駛來的方向。
不一會,那些點終於出現在盧縈的視野中。
這是四條大船,駛在最前面的大船,只有二層,那船吃水很深,裡面分明裝滿了極重秤的貨。
盧縈只朝行駛在最前面的大船看了一眼,便再也移不開目!
那個站在第二層甲板上,一襲銀甲,臉戴面,騰騰燃燒的火把下,眸子如山水如畫的,可不正是澈?
竟然是澈!
劉疆郭允等人半夜出現在河道中,埋伏著等侯的人,居然是澈!
彷彿知道盧縈在想什麼,劉疆慢慢回過頭來。
黑暗中,他雙眸如星,那眸子靜靜地盯了一眼後,他微微一傾,湊向低低說道:“這四條船中,裝的是朝庭看重的生鐵,澈正是這百里段河河道的押運……如果這些生鐵失了事,他將非常被。”
他盯著盧縈,薄脣微,說出的話音溫如呢喃,卻也冰寒如劍鋒,“然,這次,還只是一個小小的教訓!”
丟出這句低語後,他轉過頭,手放在脣間一嘬,瞬時,一陣烏聲口而出!
隨著三聲烏啼,驀然的,數十條快船上的百數個黑人,齊刷刷地點燃了火把,就在燈火在一瞬間變得通明,澈等人齊刷刷被驚,一個個都轉過頭看來時,只見百數個黑人的手中,已換了弓箭!
Advertisement
這些弓箭,箭頭燃燒著火焰,竟然全部都是火箭!
燈火大亮中,戴紗帽的劉疆右手朝空中一舉,只聽得“嗖嗖嗖”的一陣破空聲急促傳出。卻是衆黑人同時把那火箭衆船!
這一下變故不可謂不突然。
就在出發之時,澈還讓人查過河道四周,不管是報還是明報,今天晚上都應該是平平安安,順順利利的。
更何況,這裡已是城中!
大船上的衆人,幾乎是剛剛駛近,便看到前方突然火大作,無數黑黑船出現在他們的視野中。
而不等他們做出任何反應,對方的火箭已接二連三地出。一隻只燃燒的火箭落在船頭,船尾,船各,饒是船上的役夫和士卒急急撲向火焰,轉眼間,四條大船還是不可避免的燃燒起來。
快船上的黑人,個個訓練有素,在大船裡面嘶奔忙時,它們始終不不慢地跟著這四條船,然後,一波又一波的火箭到了那些大船上!
漸漸的,大船會船帆和船無法控制地燃起大火,盧縈只看到站在二層甲板上的澈,聲嘶力竭的下著一道道命令。火騰騰中,那張面下的眼,在燃燒著無比的憤怒……
就在這時,盧縈側的劉疆低聲命令道:“拿弓來!”
“是。”
不一會,一個巨弓出現在劉疆手中。
“滋滋——”一陣刺耳的弓弦拉聲中,劉疆接過郭允遞來的一支寒森森的利箭,他把那箭搭上弓弦後,弓微微向上一仰,然後,箭頭指向澈那張戴著面的臉!
看到他的作,盧縈的脣起來。可什麼也不能說,饒是張到了極點,心下也明白,只有什麼都不說,才能助得澈一二!
Advertisement
在盧縈手足冰寒時,劉疆低低的,冷笑出聲。然後,弓弦一鬆,那鋒利的箭頭如流星般出,以尋常人看不到的速度向澈直而去!
偏偏,盧縈不是尋常人,一向眼力過人!
在陡然小的瞳孔中,那箭,快如閃電地直向澈……大船上的衆人,沒人想得到今晚的來客不止是燒船,竟還兼行刺客之事!澈也沒有想到!
就在盧縈下意識的手指勾,肢發直時,那箭劃出一道寒後,衝到了澈的前,在他急急一個後仰時,過他的臉頰,“滋——”的一聲了他後的船艙上,直把木板了一個對穿!
大船上的衆人一驚,在士卒護衛如流水一樣涌向澈,把他團團圍住時,盧縈看到澈猛然轉頭,月下,著銀甲的他,慢騰騰地袖拭了拭頰側的,沉下眼,低聲說了句什麼。
大船上兵荒馬,衆快船上依然悄無聲息。只有劉疆好整以暇地盯了澈幾眼,慢條斯理地把那強弓遞給護衛,淡淡說道:“差不多了。”
他這聲音一出,衆黑人同時了,只是一轉眼,他們便熄滅了火把。
而這時,四隻大船已被燒得不樣,只見幾個護衛衝到澈側,強行下他的銀甲,然後擁著他跳了河水中……
這時,一個黑人沉喝道:“撤——”
喝聲一出,一隻只快船像是幽靈般,在月下悄無聲息的退了下去,轉眼間,整個河道中便只剩下四條騰騰燃燒的大船,還有那大船上,躲避不及的船伕發出的慘聲……
離開時,盧縈很安靜。
有點冷。
從剛纔直到現在,劉疆不過說了三四句話。
可他說的每一句話都不是廢話。很明顯,今天晚上,不過是劉疆在用自己的行警告盧縈,教訓澈。
這個男人,這個強橫的男人,一把火燒掉四船生鐵,不過是給今晚上試圖染指他的婦人的澈一個教訓而已。
當然,他更是用這個作警告盧縈。警告,有些事,最好想也別想,不然的話,那個後果不是能承的!
繼續試試看能不能送上第二更。(未完待續。
猜你喜歡
-
完結2476 章
一世傾城:冷宮棄妃
那一夜,她褪去了少女的青澀,成為冷宮深處的悲傷漣漪...... 那一天,她跪在他的腳下苦苦哀求,她什麼都不要,只想要出宮,做個平凡女人... 幾個風神俊秀的天家皇子,一個心如止水的卑微宮女... 當他們遇上她,是一場金風玉露的相逢,還是一闕山河動蕩的哀歌......
600.3萬字7.94 728802 -
完結1946 章

農女雙雙的種田悠閒生活
老穆家人人欺負的傻子穆雙雙,突然有一天變了個樣!人不傻了,被人欺負也懂得還手了,潑在她身上的臟水,一點點的被還了回去。曾經有名的傻女人,突然變靈光了,變好看了,變有錢了,身邊還多了個人人羨慕的好相公,從此過上了悠閒自在的好日子!
341萬字8 118440 -
完結1858 章
王妃她不講武德
寧孤舟把劍架在棠妙心的脖子上:“你除了偷懷本王的崽,還有什麼事瞞著本王?”她拿出一大堆令牌:“玄門、鬼醫門、黑虎寨、聽風樓……隻有這些了!”話落,鄰國玉璽從她身上掉了下來,他:“……”她眼淚汪汪:“這些都是老東西們逼我繼承的!”眾大佬:“你再裝!”
326.8萬字8.18 263247 -
完結266 章

邪帝溺寵妖孽冷妻
前塵愛錯人,家族滅,自爆亡。今世重來,她要擦亮眼睛,右手靈氣,左手煉藥,她一路升級打怪,斗皇室,滅渣男,扶家族,憑借自己的能力傲世與這個以實力為尊的世界。 而她的身邊,也多了一個真正可以與她攜手并肩的妖孽男人,傾世風華只為她一人展顏,翻手為云覆手為雨,只為護她亂世周全。
78.1萬字8 32780 -
完結11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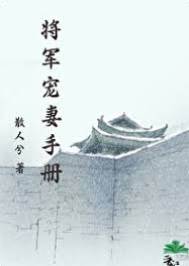
將軍寵妻手冊
雲府長女玉貌清姿,嬌美動人,春宴上一曲陽春白雪豔驚四座,名動京城。及笄之年,上門求娶的踏破了門檻。 可惜雲父眼高,通通婉拒。 衆人皆好奇究竟誰才能娶到這個玉人。 後來陽州大勝,洛家軍凱旋迴京那日,一道賜婚聖旨敲開雲府大門。 貌美如花的嬌娘子竟是要配傳聞中無心無情、滿手血污的冷面戰神。 全京譁然。 “洛少將軍雖戰無不勝,可不解風情,還常年征戰不歸家,嫁過去定是要守活寡。” “聽聞少將軍生得虎背熊腰異常兇狠,啼哭小兒見了都當場變乖,雲姑娘這般柔弱只怕是……嘖嘖。” “呵,再美有何用,嫁得不還是不如我們好。” “蹉跎一年,這京城第一美人的位子怕是就要換人了。” 雲父也拍腿懊悔不已。 若知如此,他就不該捨不得,早早應了章國公家的提親,哪至於讓愛女淪落至此。 盛和七年,京城裏有人失意,有人唏噓,還有人幸災樂禍等着看好戲。 直至翌年花燈節。 衆人再見那位小娘子,卻不是預料中的清瘦哀苦模樣。雖已爲人婦,卻半分美貌不減,妙姿豐腴,眉目如畫,像謫仙般美得脫俗,細看還多了些韻味。 再瞧那守在她身旁寸步不離的俊美年輕公子。 雖眉眼含霜,冷面不近人情,可處處將人護得仔細。怕她摔着,怕她碰着,又怕她無聊乏悶,惹得周旁陣陣豔羨。 衆人正問那公子是何人,只聽得美婦人低眉垂眼嬌嬌喊了聲:“夫君。”
17萬字8.33 5690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