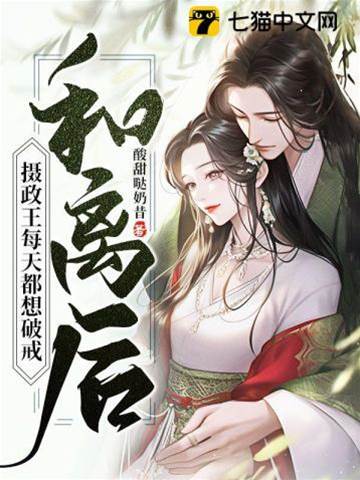《鳳月無邊》 第245章 劉疆,請允許我驕傲
這時,昏暗的殿中,有人絡續退場,劉疆坐直子,面無表地命令道:“走吧。”
“是。”
一行人悄無聲息地向後退去。
來時這裡顯得幽深詭,去時走的卻是另一條道,當盧縈站在外面的街道中時,才發現滿天繁星,遠的高門大閥中,森森院落裡,不時傳來笑聲陣陣。
衆人上了馬車,馬蹄行走在青石板上,發出靜謐的噠噠聲。
一路上,一直沒有人說話,直到走了近一個時辰,盧縈發現自己和劉疆站在一個山峰上時,才驚醒地想道:今晚怎地如此安靜?
山峰上,劉疆走出兩步,他負著雙手,居高臨下地看著下面起伏的華屋房啥,山巒樹林。夜風中,一切顯得那麼的安靜,只有後不遠幽深的樹林中,不時傳來一陣陣古怪的烏啼鳴。
他一直不說話,衆人也不敢說話,於無聲的安靜中,也不知過了多久,在樹叢中的火把下,急步走來二十幾個黑人。
那二十幾個黑人行走時落地無聲,直到了近前,盧縈才發現他們地到來。
他們走到劉疆後,齊刷刷跪拜在地,沉聲說道:“臣見過主公!”
“平吧。”
“謝主公。”
黑人站起後,一個個躬而立,低著頭不敢看向並肩而立的劉疆和盧縈兩人。
劉疆低下頭瞟了他們一眼,淡淡問道:“一切都佈置好了?”
“是!”
夜中,劉疆雙眸如電,他冷漠地說道:“地下暗標殿散於民間的暗帝玉牌,共一百七十二枚,可有查清今晚亮出的玉牌共有多?”
一個黑人上前一步。低頭稟道:“直到一刻鐘前,出現在暗帝玉牌共有一百二十有四!”
Advertisement
劉疆點了點頭,淡淡說道:“是近十期中最多的一次。”
說到這裡,他不知想到了什麼,沉默下來。負著手盯著遠方沉黑的山峰,他好一會才聲音冰寒地說道:“發出號令,行吧!”
這幾個字一落,衆黑人連同郭允在,齊刷刷地站起來。他們整齊地應道:“是!”
劉疆冰寒的命令聲繼續傳來,“絕殺吧。”
絕殺這兩字一出,衆黑人似是給驚住了,一陣無聲的沉寂中,一個量魁偉的黑人上前一步。他來到劉疆面前,低聲說道:“主公,地下暗標殿屹立千年而不倒,無論場權貴,老百姓,還是市井匪徒,都有他們的人……他們的勢力如此深葉茂。若能收服,於主公大有好。”頓了頓,他又說道:“臣查前朝諸事,發現歷代皇室。都有收服之舉,而臣經過查探亦知,每到天下大治,地下暗標殿亦樂於投靠君王。雖有保存實力之嫌,然而。他們在這千餘年間,實是積累了無以計數的財富,能收於麾下,將爲主公添得一臂!”
劉疆轉過頭,他目如電,冷冷的從衆黑人臉上掃過。
片刻後,他冷笑道:“不親至此地,孤竟不知他們囂張至此!皇室子弟,皇室家眷,就算是落了勢,就算是隻求一死,也不到這種醃髒之人作踐!正因爲歷朝歷代只想收其爲自己所用,所以才容得這些人立千年而不倒!”他冰寒地說道:“孤的治下,不需要這種醃髒之臣!傳孤號令,務必把地下暗標殿圍個水泄不通,我要讓那裡的人,無論男,不管主客,一律殺絕,通通犬不留!若有走,你們自盡吧!”
這是沒有半點商量餘地了!
Advertisement
衆黑人大凜,同時跪下應道:“遵令!”
他們應過之後,急速後退,轉眼便消失在盧縈的眼前。
當他們走了不到一刻鐘,只見不遠的樹林中,突然火大作,那火沖天而起,轉眼間,火由一轉四!
火由一轉四,就是四面絕殺令了!
於是,在第四道火燃起的那一瞬間,四野中陡然安靜了片刻。然後,一陣令得天崩地裂的喊殺聲混合著猛烈的炸聲,還有無數人同時衝撞傳來的腳步聲陡然傳來,在一瞬之間,驚醒了整個沉睡的長安城!
著下面左側一那漫天飛舞的火箭還有巨響,盧縈脣抿了抿。
就在這時,的手一暖,卻是劉疆握住了。
在他握住的那一刻,原本冰寒的手,奇蹟般的變得溫暖起來。
站在後面,郭允瞟到這一幕,無聲地嘆了一口氣。
想了想,他上前一步,走到劉疆後,郭允低聲說道:“主公,地下暗標殿寶藏無數,何至於不留一個活口?”
他顯然也知道,劉疆一旦決定一件事,便是再也難以改變。因此他這時說出這話,已不是建議,而是惋惜。
劉疆頭也不回,他面無表地盯著那響聲和漫天火衝出的所在,冷冷地說道:“我的人,我自己亦對百般縱容忍讓,這等醃髒之徒,向誰借的膽竟敢以作標?”
果然是爲了盧氏!
郭允嘆了一口氣,心中想道:人家之所以這麼做,那也是他們不知道盧文是你的逆鱗啊!
他瞟向驚得呆住,傻傻地轉頭看向劉疆,眼中有淚的盧縈,不由想道:主公太也沉迷於,盧氏啊盧氏,你何德何能令他至此?
Advertisement
這時刻,山下面的喊殺聲越來越響,引得天崩地烈的巨響“轟——轟轟”的不斷傳來。看著那變了火海的地方,郭允低聲說道:“主公,這裡不安全,我們還是走吧?”
劉疆沒有,他淡淡地說道:“此甚好。”
只是四個字,郭允便不敢再什麼了。
這一個晚上的長安城,一直一直都沒有安靜過,那一堆堆沖天而起的火焰中,那藏在嘶喊聲中的哭嚎聲,那令得大地都爲之震的巨響轟鳴中,那一夜不停徹夜奔馳的馬蹄聲中,把整個長安城都變得沸騰了。於這無邊的喧鬧中,劉疆一直這樣站著,他不,盧縈也沒有。
和他牽著手,便這般靜靜地看著下面,看著那了人間煉獄的所在。
也不知過了多久,彷彿是鳴第二遍時吧?一直靜佇於天地間,如同山峰一樣的劉疆開口了,“你們都退下。”
“是。”
郭允等人退了下去。
當他們的腳步聲漸漸不可聞時,劉疆轉過來。
因站得太久,夜間的珠都染上了他的髮鬢,令得這個強橫不可一世的男人,因那一點點珠的晶瑩反,彷彿發染白霜,平添了幾分說不出的滄桑和孤寂。
不知不覺中,盧縈眼睛又紅了,從懷中掏出手帕,擡手拭向他額側的珠。
的手剛剛靠近他的髮鬢,劉疆突然手一,啪地一下把的手拍了下來。因作過猛,握在盧縈手中的手帕給他打落在地,飄飛到了草叢中。
盧縈慢慢彎腰,撿起那手帕,再舉起手,又一次拭向他額側的白霜。
這時的,薄脣抿幾一線,昏暗的,幾乎看不清面目的夜下,的眼中有淚在浮。
Advertisement
再一次,的手帕按在他的鬢角時,他重重一拍,把的手又打落下去。
盧縈低下頭,看著那塊被夜風吹得遠遠飄開的手帕,突然的,慢慢落下來。
倒在他前,出雙臂,盧縈抱著了他的雙。
地抱著他,把臉埋在他的雙膝間。因用力過猛,在他膝上的臉孔都有點變形了。
這般的,地摟著,盧縈嘶啞地開了口,“阿疆,我歡喜你,我很早很早前就歡喜上你了。”
說到這裡,黑暗中,似乎有劉疆哧之以鼻的屑笑聲傳來。
盧縈著他的小,覺到那的強勁和溫熱,啞著聲音繼續說道:“可是阿疆,我拿什麼來你?”
約的亮中,的淚水一滴一滴地順著他的下服流下,那淚水直浸溼了裳,直浸溼了他的小,直是一滴一滴地落草叢中,再不復見。
沙啞著,盧縈的聲音哽咽中帶著幾分固有的清冷,“阿疆,你說我有什麼?盧縈也罷,盧文也罷,有什麼?沒有家世,沒有靠山,沒有人脈,沒有金錢,那麼驕傲,卻又那麼貧窮。的心上人是這個世間最爲尊貴的男兒,的心上人整個天下的人都想靠近,的心上人天下的世家都想結,的心上人是站在那裡,便能令得所有想接近他的人,都變得卑微……原本低賤如泥,卻因沾上了這世間獨一無二的權貴,才一步步有了今日的榮。可這些榮是的心上人所賜啊!若不爲自己做些什麼,不爲自己多經營一點,是不是有一日的心上人歡喜上了別的人後,又變回了泥土?”
伏在他足下,啞著聲音,流著淚,卻清冷而又平靜地說道:“阿疆,我歡喜你,很歡喜很歡喜。我也知道你歡喜我,很歡喜很歡喜……所以,請允許阿文自私一點,允許永遠保持一份驕傲,允許有一日被你所棄之後,依然是那個你曾經過,心痛過,並珍惜過的盧文。雖年老,姿不再,卻依然從容驕傲,從泥土中爬起來後,便是死,也不再跌落到泥土中。依然來去從容,依然談笑風流,依然富貴,依然自信,依然想風時,便能風!”
我要紅票票,我要很多很多紅票票!這個月底應該沒有一票抵兩票的事,所以,大夥清清個人書屋吧。
猜你喜歡
-
完結1410 章

傾世獨寵:娘娘又出宮了
一頓野山菌火鍋,沐雲清成了異時空的王府小姐,父母早亡哥哥失蹤奶奶中風,她被迫開始宅鬥宮鬥。 對手手段太低級,她鬥的很無聊,一日終是受不了了,跑到了蜈蚣山決定占山為王,劫富濟貧,逍遙快活。 可誰知第一次吃大戶,竟是被燕王李懷瑾給纏上了。 山頂上,沐雲清一身紅衣掐著腰,一臉怒容:“李懷瑾,我最後一次警告你,我此生隻想占山為王與山為伴,王妃王後的我不稀罕!” 在戰場上煞神一般的燕王李懷瑾此時白衣飄飄站在下麵,笑的那個寵溺:“清清,你怎麼知道我還有個彆名叫山?” 沐雲清氣結:“你滾!”
267.3萬字8 34344 -
完結382 章

深宮策·青梔傳
她的眼看穿詭術陰謀,卻不能徹底看清人心的變化; 他的手掌握天下蒼生,卻只想可以握住寥寥的真心。從一個為帝王所防備的權臣之女,到名留青史的一代賢後,究竟有多遠的距離?一入深宮前緣盡,半世浮沉掩梔青。梧桐搖葉金鳳翥,史冊煌煌載容音。
77.2萬字8.18 25607 -
完結56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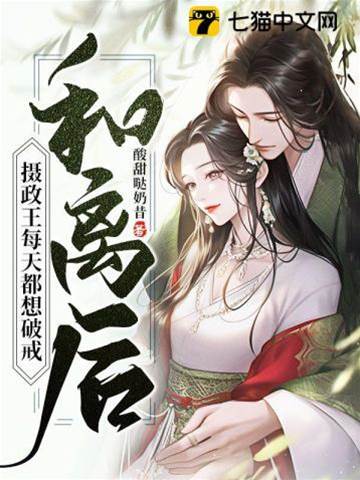
和離後攝政王每天都想破戒
葉芳一朝穿越,竟然穿成了一個醜得不能再醜的小可憐?無才,無貌,無權,無勢。新婚之夜,更是被夫君聯合郡主逼著喝下絕子藥,自降為妾?笑話,她葉芳菲是什麼都沒有,可是偏偏有錢,你能奈我如何?渣男貪圖她嫁妝,不肯和離,那她不介意讓渣男身敗名裂!郡主仗著身份欺辱她,高高在上,那她就把她拉下神壇!眾人恥笑她麵容醜陋,然而等她再次露麵的時候,眾人皆驚!開醫館,揚美名,葉芳菲活的風生水起,隻是再回頭的時候,身邊竟然不知道何時多了一個拉著她手非要娶她的攝政王。
99.6萬字8 948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