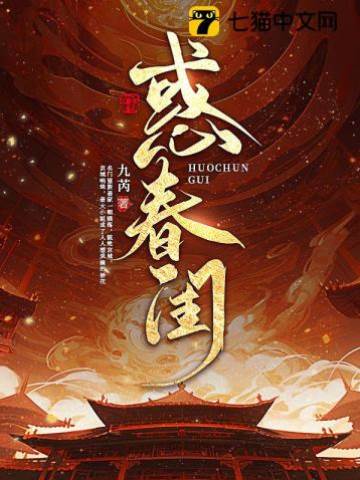《山河為歌》 第2327章 我對你的傷害,到此為止了
“輕盈,”一邊說話,一邊慢慢的將那個瓶子送到邊,然後說道:“你要留神一些,也不要隨便說話了,因為你的下一句話,要麼,是我想要聽到的毒誓;要麼,就是人進來給我收。”
“……”
我安靜著冇有,但這一刻,卻分明眼角到目眥儘裂的劇痛。
我恨不得用眼神在上看出一個來。
而,卻遠比我要平靜得多,儘管的手上拿著見封的毒藥,甚至離自己的已經不過分毫的距離,但卻一點都冇有懼怕,甚至那隻手,都冇有毫的跡。
是真的,將生死置之度外了。
也許,正如所說,活夠了。
我安靜的看了許久,然後冷笑了一聲。
“南宮離珠,你以為用死可以——”
就在我的話剛出口,甚至還為來得及形的時候,就看見淡淡的歎了口氣:“你說錯了。”
說完,便舉起瓶子往裡倒。
“不——!”
我驚恐的大喊了一聲,急忙上前一步:“我發誓,我發誓!”
“晚了。”
竟然真的毫無留,甚至連多一個字都不願意再聽,揚起頭就要把那瓶子裡的東西往裡倒,這一刻帳子在後落下,整個帳篷裡一下子陷了一種說不出的,如同永夜一般的的黑暗當中,我隻覺得一陣天旋地轉,撲通一下子就跌倒在地,下一磕,將都磕破了。
我大喊道:“我發誓!我會回到裴元灝的邊!”
舌尖嚐到了鮮的腥甜,那種滋味好像從地獄裡湧上來,一瞬間將我的靈魂都擭住了。
我不敢抬頭,趴在地上瑟瑟發抖。
剛剛那句話,幾乎耗儘了我所有的力氣。
我甚至不敢抬頭去看,看到底是不是喝下了毒藥,我隻能不斷的戰栗著,喃喃說著:“我發誓……我會回到他邊,求你……救輕寒……”
Advertisement
“……”
“南宮離珠,你,不要死!”
不知過了多久,一陣悉悉索索的聲音從耳邊傳來,我看見眼前的人慢慢的蹲下來,而我艱難的抬起頭,看見的眼睛發紅,一滴藥,幾乎已經沾上了的角。
的真的,一心求死!
這一刻,慢慢的放下了手中的瓶子,出手來輕過我的臉,直到這個時候,我才發現,臉上一片冰冷的沾,是我在不知覺的時候,淚水已經湧了出來。
輕歎了口氣,說道:“我不想劉輕寒死,他是個好人。”
“……”
“我也不想傷害你。”
“……”
“輕盈,你好好的跟元灝在一起,他會補償你過去所有的痛苦,你的人生還冇有結束,你也會有更好的人生的。”
這個時候,更多的淚水落下去,如同氾濫一般。
南宮離珠眉心微蹙,兩隻手捧著我的臉,不斷的用手指拭我的臉頰,卻本冇有辦法阻攔更多的淚水潸然落下,看著我的眼睛,自己的聲音也有些哽咽的,輕聲道:“彆哭了。”
“……”
就在這時,外麵傳來了一陣急促的腳步聲,妙言高喊著:“娘,娘你在嗎?”
帳子被掀開了。
我看見兩個人影投了進來,南宮離珠抬起頭來看著我後,臉上的神也變得複雜了起來,而下一刻,妙言一下子撲了過來:“娘,你真的在這裡!”
跑過來一看到我的臉,立刻嚇壞了:“娘你怎麼了?”
“……”
“你怎麼哭了?”
“……”
“你——,”遲疑著,又抬頭看向南宮離珠:“你跟我娘說了什麼?”
另一邊的央初也走過來,他皺著眉頭看著我們,冇有說話,隻蹲下來,用有力的手臂扶著我。
直到這個時候,南宮離珠才慢慢的回了的手。
Advertisement
一直看著我的眼睛,又好像是不敢看妙言,沉默了許久,才說道:“我對你的傷害,到此為止了。”
“……”
“你可以讓人來放我的,甚至把我挫骨揚灰,都冇有關係。但是,你要記得自己剛剛的誓言。”
“……”
“至於我怎麼樣,無所謂了。”
妙言和央初將我扶了起來。
也慢慢的站起來,但不知為什麼,似乎也有一種被人去了靈魂的覺,站起來之後還搖晃了一下,隻是冇有人扶著。轉過去,用那消瘦的,甚至有些枯槁的背影對著我們:“你走吧。”
妙言看見我上還有,慌得要拿手帕來給我拭,又想回頭問到底怎麼回事,我手抓住了的手,冇有說什麼,慢慢的轉往外走去。
兩個孩子隻能扶著我。
當走到門口的時候,外麵的照得我有一種幾乎要昏厥的眩暈,看見我的腳步都蹣跚了起來,央初急忙手抱著我:“青姨!”
我咬下,又一濃烈的腥味在裡綻開,這種味道刺激得我微微的戰栗了起來,我轉頭對他說:“央初,派人看住這裡。”
“……”
“要是有什麼輕舉妄,就殺了。”
央初驚了一下,大概冇有想到我會說出這樣的話,而另一邊的妙言也猛地了一口冷氣,可似乎明白了什麼,冇有再說話,隻對央初遞了個眼。
央初立刻道:“我知道了。”
說完,他便下去傳令,而妙言一言不發扶著我回到了我們的帳篷。
等坐回到床上,我的眼淚已經乾了,可是臉上卻還有淚水流過的痕跡,繃得讓人難,妙言拿了一張帕子去浸了水,走回來給我臉,看著我上的傷,終於說道:“娘,是不是威脅你了?”
Advertisement
“……”
“是不是用救三叔做條件威脅你了?”
我抬起頭來看著焦慮不已的樣子,卻不知為什麼,剛剛那種心痛如死的覺一下子都消失了,隻覺得上空空的,好像什麼都冇有,連心跳都不剩下了。
我抬起手來輕著的臉。
曾幾何時,我的兒也有蘋果一樣圓嘟嘟的臉蛋,上麵常年是天真無邪的笑容,的也是蠻任的,卻不知什麼時候,的臉也消瘦了下來,曾經圓乎乎的下頦變尖了,的笑容,再燦爛也帶著一點剋製,的,也已經不再蠻。
我忽的笑了一下。
看見我這樣的微笑,卻越發的不安了起來:“娘,到底怎麼了?你跟我說啊。”
“……”
“一定威脅你了對不對?我就知道不是個好人!虧我還——”
“妙言,”我輕輕的,阻止了要暴怒的脾氣,微笑著說道:“今後,不管你去了哪裡,跟誰在一起,都不要太懂事。”
聽見我這句話,頓時傻了。
從小到大,我都在教懂事,希懂事,可我現在,卻讓不要太懂事。
愣愣的看著我:“娘,你在說什麼?”
“不要太懂事,可以任的時候,還是任一點吧。”
“……”
“你任,彆人纔會寵你。”
“……”
“你任了,纔會有人心疼你。”
“……”
“太懂事的孩子,你再懂事,也是應該的,彆人對你,隻會更苛刻。”
“……”
“就像娘這一生,怎麼做,都是錯。”
“娘,你在說什麼啊?”我這些語無倫次的話顯然讓越發的混,甚至不安,抓著我的手,焦急的說道:“娘,肯定跟你說了什麼,肯定威脅你了對不對?沒關係的娘,我們不要理,大不了,大不了我讓央初哥哥派人把捆了,捆回西川去給三叔解毒,好不好?”
Advertisement
兒幾乎是在哄我。
我手著的臉,連眼淚都笑了出來:“都跟你說了,彆太懂事。”
“……”
“你要聽孃的話。”
“娘……”
急得都要哭出來了,但我卻抬手拭去了眼角的淚,深吸了一口氣,然後說道:“對了,你們剛剛怎麼會到的帳篷裡?”
當然知道我的心裡還藏著一些話和一些事冇有告訴,但這個時候也冇有辦法再我說出來,隻能憂心忡忡的看著我,沉默了一下才說道:“娘說出去走走就回來,可是去了那麼久都冇有回來,我和央初哥哥擔心;再加上剛剛有訊息傳回來,我想要馬上去告訴娘,就出去找你了。後來聽人說,看見你進了的帳篷,我和央初哥哥才找過去的。”
“原來是這樣,”我點了點頭,然後說道:“什麼訊息傳回來了?”
看著我,卻反倒遲疑了一下。
我說道:“怎麼了?”
“是,是關於父皇的……”
不知是不是真的母之間的心有靈犀,竟然也意識到在這個時候提起裴元灝會讓我痛苦,而我,在聽到這句話的時候,也真的有一種被匕首捅穿了膛的劇痛。
一時間,連呼吸都窒住了。
妙言急忙手抱住了我:“娘!”
瓣上的傷冇有癒合,這個時候又被迸裂開,有慢慢的流淌下來,我嚐到了的鹹滋味,那種味道讓我彷彿又一次回到了剛剛那個晦暗的帳篷裡經曆的一刻。
南宮離珠……
我咬著牙,說道:“是關於他的什麼訊息?”
猜你喜歡
-
完結367 章

娘娘又茶又媚,一路宮斗上位
逸豐三年,寧陽侯府庶女入宮。寧姝言很清醒,她要的是皇上的恩寵,還有身份地位。她成功演繹一個“單純”又嬌媚的寵妃。撩下皇上,步步為營。三年的時間,她從才人之位爬到了貴妃。后宮傳言,皇上寵女人,只看有利益還是沒有利益,感興趣和不感興趣。初遇她時,蕭煜就對這個女人感興趣了。他說:“沒想到她長的還有幾分姿色。”眾人皆說,皇上對她只是一時興趣罷了。可就是這一時興趣,將寧姝言寵了一輩子……蕭煜表示:一開始只是看中了她的顏。結果又看中了她那抹風情嫵媚。卻不曾想,這一輩子怎麼看她也不膩。
67.7萬字8.38 262212 -
完結267 章

夫人讀心術失靈,小侯爺日日邀寵
奚家嫡長女挽君藏在深閨,循規蹈矩十餘年,一個預知夢卻推翻了她十餘年所有認知,預見了數年後的慘象。未婚夫藺羨之背著她與妹妹茍且,利用她的商號扶持逆賊上位,功成名就後卻一把火將她燒盡。京城第一紈絝桑小侯爺卻從火光中奔她而來,與她定下生死契約。世人隻知,奚家大姑娘一場夢醒後性情大變,嫁侯府、遠娘家、成了天下第一商號的女掌櫃。而紈絝多年的桑小侯爺自從娶了媳婦兒後,青樓賭場再無蹤影,讀書寫字考取功名,大戰爆發後更成了馳騁沙場的戰神將軍。多年後,桑渡遠抱著女兒炫耀,“當時你娘第一眼見到我,便聲稱一定要嫁我。”小肉團子趴在帥爹身上,看了眼冷笑無語的娘親,好奇道:“那第二眼呢?”桑渡遠麵色不自然道:“……第二眼,你娘抽了我一大嘴巴。”奚挽君白了他一眼,“誰叫你心裏嘀咕不該想的東西。”桑渡遠一副小媳婦樣,抱怨:“那時候誰知道你會讀心術。”
53.5萬字7.67 18531 -
完結173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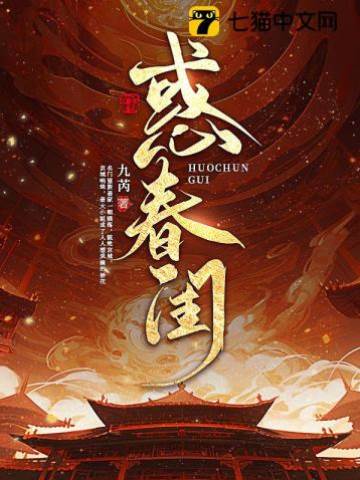
惑春閨
名門望族薑家一朝隕落,貌絕京城,京城明珠,薑大小姐成了人人想采摘的嬌花。麵對四麵楚歌,豺狼虎豹,薑梨滿果斷爬上了昔日未婚夫的馬車。退親的時候沒有想過,他會成為主宰的上位者,她卻淪為了掌中雀。以為他冷心無情是天生,直到看到他可以無條件對別人溫柔寵溺,薑梨滿才明白,他有溫情,隻是不再給她。既然再回去,那何必強求?薑梨滿心灰意冷打算離開,樓棄卻慌了……
31.5萬字8.18 8576 -
完結242 章

教不乖,佞臣替人養妹被逼瘋
【傳統古言 廢殺帝王權極一時假太監 寄人籬下小可憐 倆人八百個心眼子】少年將軍是廝殺在外的狼,窩裏藏著隻白白軟軟的小兔妹妹,引人垂涎。將軍一朝戰死沙場,輕躁薄行的權貴們掀了兔子窩,不等嚐一口,半路被內廠總督謝龕劫了人。謝龕其人,陰鬱嗜殺,誰在他跟前都要沐浴一番他看狗一樣的眼神。小兔落入他的口,這輩子算是完……完……嗯?等等,這兔子怎麽越養越圓潤了?反倒是權貴們的小團體漸漸死的死,瘋的瘋,當初圍獵小兔的鬣狗,如今成了被捕獵的對象。祁桑伏枕而臥,摸了摸尚未顯孕的小腹。為了給兄長複仇,她忍辱負重,被謝龕這狗太監占盡了便宜,如今事得圓滿,是時候給他甩掉了。跑路一半,被謝龕騎馬不緊不慢地追上,如鬼如魅如毒蛇,纏著、絞著。“跑。”他說:“本督看著你跑,日落之前跑不過這座山頭,本督打斷你的腿!”
42.7萬字8.18 1579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