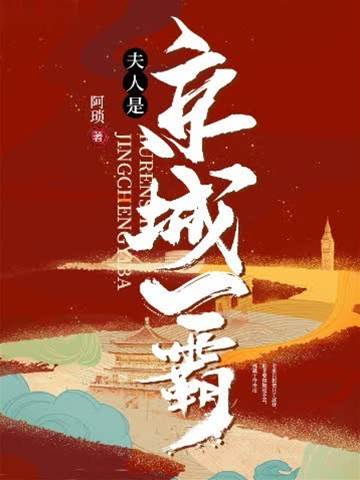《上邪》 第122章娘說了,見麵打一拳
靳月張了張,心口鈍痛,卻不知該說什麼。嗓子裡發,眼眶發燙,在府衙當捕頭這麼久,進過房,知道死亡意味著什麼。
那些人不是的至今,尚且覺得心裡不舒服。
但若是至親,任誰都會瘋!
十萬大軍……
浮遍野,修羅場! 靳月坐在那裡,很久很久都沒能回過神,直到傅九卿握住了的手,冰涼的掌心在的手背上,才紅著眼回他。
「現實之所以為現實,是因為超出了你所能想象的殘酷。」傅九卿眸平靜,口吻盡量平緩,不至於讓察覺到,掩於其中的波瀾,「要不要告訴漠蒼,是你的選擇,誰都不會幹涉!但有一點你必須明白,撕開陳舊的傷疤一定會流!」
靳月仲怔。
不可否認,隔了這麼多年的傷疤,一旦被揭開,何止是流……也可能會喪命!
傅九卿走的時候,靳月還定定的坐在原地,彷彿失了魂魄,有些神恍惚。
「丫頭?」靳年嘆口氣,「別查了!」
靳月略顯遲滯的盯著他。
「你若要查,傅九卿一定會幫你,可結局未必是你想要的。」靳年意味深長的開口,「時間隔了太久,別說痕跡淺顯,查詢不易,就算被你找到了又如何?死去的人回不來,活著的人被牽連進去,到時候這雪球會像當年一樣,越滾越大,最後一發不可收拾。」
靳月忽然握住靳年的手,「爹,傅九卿是不是知道一些?」
「我不知道他是否去查過,畢竟這事我原是想帶進棺材裡的。」靳年輕輕拍著的手背,「月兒,別查了,算是爹求你了!」
靳月抿,「那……爹不是細作吧?」
「屁話!」靳年拍案而起,瞬時目猩紅,「我對天發誓,絕對沒有出賣將……軍!若有虛假,必天打雷劈,不得好死!」
Advertisement
靳月慌忙摁住他,「爹,我就是隨口一問。」
「月兒,別手!」靳年咬著後槽牙,「當年因為這事,多無辜的人到牽連,即便有人僥倖逃出,隻怕這輩子都不敢去回想,那淋淋的日子。」
靳月狠狠皺眉。
「上至文武百,下至黎明百姓,禍連一萬多人,流放數萬,知者不是被殺就是逃匿,當時的場景……隔了十數年依舊曆歷在目。」靳年搖搖頭,委實不願再回想。
靳月從未見過父親這般神,滿臉晦暗,就好似又回到了那個時候,被軍追殺,如同老鼠一般東躲高原地,不得不姓埋名。
「所以爹也是因為這事,兒改名換姓的?」靳月問。
靳年點頭。
如此,便說得通了。
「罷了,你讓那混小子來找我吧!」靳年把心一橫,「我與他說就是,反正我知道也不多,該說不該說,乾脆一腦全告訴他,也免得他日後與你糾纏不休。」
靳月眉梢微挑,「爹,認真的?」
靳年翻個白眼,「再不去就反悔咯!」
「明珠,把漠蒼帶來!」
明珠去帶人的時候,漠蒼正敲著二郎,悠哉悠哉的坐在視窗,吹著冷風哼著家鄉的小調,瞧著極是閑適,隻是這閑適在明珠出現後便被打破了。
「疼疼疼……」明珠直接揪著漠蒼的肩胛,麵無表的把他往外拖,驚得漠蒼連呼帶,「人,你能不能溫點?就溫一下下也。」
明珠橫了他一眼,「不能!」
漠蒼:「悍婦!」
這詞是他剛從說書先生那裡學來的,活學活用。
悍婦?
明珠還是頭一回聽到有人這麼形容,拽著他走出傅家大門時,冷風吹得人睜不開眼睛,勾揚起嘲諷的弧度,「你怕是沒見過,真正的悍婦是什麼模樣吧?」
Advertisement
漠蒼還沒回過神來,屁上忽然捱了一腳,整個人幾乎以飛騰的姿勢被踹上了馬車。剎那間,五臟六腑都好似被摔碎,疼啊……真他孃的疼啊!
「悍……婦……」
到了醫館的時候,漠蒼是自己跳下馬車跑進去的,屁疼,肚子疼,全疼,但如果他慢一步,有可能會更疼,畢竟明珠這「悍婦」委實太彪悍,他吃不消、吃不消!
「你們……」漠蒼齜牙咧,瘸著進門,「幹什麼?」
「你怎麼了?」靳月不解。
漠蒼著屁,悄悄回頭瞧了一眼麵無表的明珠,「沒什麼,被狗咬了一口。」
說完這話,漠蒼一溜煙跑到靳月邊上坐著。
明珠裹了裹後槽牙,算你小子命大,把我比作狗……嗬!嗬!
「什麼事?」漠蒼忙問,「這麼著急,難道是找到了我要找的人?雲中客在哪?人呢人呢?哎呦,不要賣關子!」
瞧著他那急子的模樣,靳月手指了指邊上的靳年。
「我知道這是你爹,也知道你爹是個大夫,可能會認識這一行不人,四一打聽,估計就能有訊息!」漠蒼其實沒抱多大希,手去抓桌案上的花生。
靳月皺眉,「我表示得還不夠明顯?」
漠蒼眨著眼,「什麼意思?」
「咳咳咳!」靳年輕咳兩聲,「在下,雲中客是也!」
漠蒼笑得眼淚都出來了,「哎,別鬧了,你們父兩個要套我話就直說,我來京都城這麼久,承蒙五夫人關照,好吃好喝的待著,所以沒拿你們當外人。」
靳月瞧著靳年,靳年著靳月。
父兩個很是發愁啊,就漠蒼這般腦子,是怎麼活著離開南玥,活著走到京都城的?
笑了半晌,漠蒼愣了愣,默默放下了手裡的花生,瞧著麵麵相覷的靳家父,「你們……認真的?」
Advertisement
靳月、靳年,「你哪隻眼睛看到,我們在開玩笑?」
漠蒼:「……」
我的乖乖!
麵鐵青的站起來,漠蒼間發,上下仔細的打量著靳年,「你……真的是雲中客?」
「信不信,不信拉倒!」靳年有些氣惱,挑破了窗戶紙竟還不信,真是氣煞人也!
誰知下一刻……
「爹!」
「靳大夫?」
「靳大夫!」
幾聲驚呼,明珠當即摁住了漠蒼,靳月和霜枝慌忙攙起莫名其妙捱了一拳的靳年。
口中滿是鹹腥味,靳年啐一口口水,滿是殷紅的,「你腦子有病?」
「漠蒼,你發什麼神經?」靳月亦盛怒難耐,「爹,你快坐著,怎麼樣?」
靳年捂著生疼的麵頰,漠蒼這一拳不輕,打得他牙都鬆了,滿都是。生生嚥下口中腥味,靳年深吸一口氣,「今日不說清楚,我就了你小子這皮,把你做燈籠掛街上!」
明珠用力的將漠蒼摁在桌上,渾然彈不得。
「我……我娘代過,見到、見到雲中客,一定要替打一拳!」漠蒼也委屈。
母親的臨終言,他能違背嗎?
靳月瞪大眼睛,忽然近前仔細的瞧著漠蒼,然後又回到靳年邊,見鬼般的盯著自家老父親,「爹,你是不是幹了什麼壞事?」
「什麼什麼壞事?」靳年訓斥,「你爹我,像是這麼風……這麼瘋狂的人嗎?我是個大夫,大夫得正,這都不懂?」
靳月了,「爹啊,你坦白承認,我不會怪你的,娘也不會怪你的。」
承認?
承認什麼?
靳年咬牙切齒,「你個死丫頭,我……我沒有!」
「沒有什麼?」
「沒有睡他娘!」
靳月了鼻尖,「哦……」
猜你喜歡
-
完結45 章

繁花落盡暮白首
仙霧之下,九州之上。她身為九天神女,一血誅盡天下妖魔,一骨盪盡九州魑魅。但她身為天妃,卻被自己愛了千年的男人一休二棄三廢,直至魂消魄散。「帝旌,如有來生,願不識君……」
4.6萬字8 7157 -
完結572 章
回眸醫笑:逆天毒妃惹不起
她,二十一世紀頂級醫學女特工,一朝重生,卻成了大將軍府未婚先孕的廢物大小姐。渣爹不愛?渣姐陷害?沒關係,打到你們服為止!從此廢物變天才,絕世靈藥在手,逆天靈器隨身,還有個禦萬獸的萌娃相伴,風華絕代,震懾九荒,誰敢再欺她?可偏偏有人不怕死,還敢湊上來:「拐了本王的種,你還想跑哪裡去?」納尼?感情當年睡了她的就是他?某王爺十分無恥的將人帶上塌:「好事成雙,今夜我們再生個女兒給小白作伴。」
98.1萬字8.18 45505 -
完結78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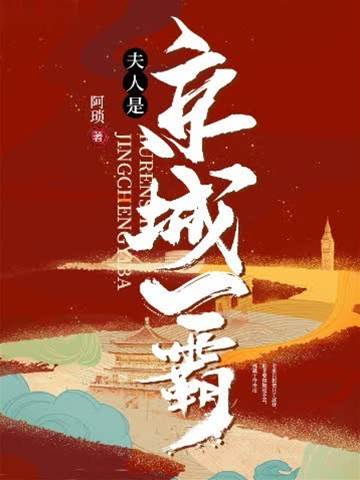
夫人是京城一霸
七姜只想把日子過好,誰非要和她過不去,那就十倍奉還…
123.2萬字8 19066 -
完結209 章

云鬢楚腰
陸則矜傲清貴,芝蘭玉樹,是全京城所有高門視作貴婿,卻又都鎩羽而歸的存在。父親是手握重兵的衛國公,母親是先帝唯一的嫡公主,舅舅是當今圣上,尚在襁褓中,便被立為世子。這樣的陸則,世間任何人或物,于他而言,都是唾手可得,但卻可有可無的。直到國公府…
68.7萬字8 26115 -
完結698 章

神醫娘親她特會講理
她來自中醫世家,穿越在成親夜,次日就被他丟去深山老林。四年里她生下孩子,成了江南首富,神秘神醫。四年里他出征在外,聲名鵲起,卻帶回一個女子。四年后,他讓人送她一張和離書。“和離書給她,讓她不用回來了。”不想她攜子歸來,找他分家產。他說:“讓出正妃之位,看在孩子的份上不和離。”“不稀罕,我只要家產”“我不立側妃不納妾。”她說:“和離吧,記得多分我家產”他大怒:“你閉嘴,我們之間只有死離,沒有和離。”
121.9萬字8 162108 -
完結184 章

紅酥手
蕭蔚看着爬到自己懷裏的女子無動於衷:餘姑娘,在下今晚還有公文要審,恐不能與你洞房了。 餘嫺抿了抿嘴脣:那明晚? 蕭蔚正襟危坐:明晚也審。 餘嫺歪頭:後夜呢? 蕭蔚:也要審。 餘嫺:再後夜? 蕭蔚:都要審。 餘嫺:我明白了。 蕭蔚:嗯……抱歉。 餘嫺笑吟吟:沒事。 蕭蔚疑惑:嗯? 餘嫺垂眸小聲道:白天? 蕭蔚:?(這姑娘腦子不好? 爲利益娶妻的腹黑純情男x爲真愛下嫁的天真軟萌妹 簡述版: 男主:對女主毫無愛意卻爲利益故作情深,作着作着走心了 女主:對男主頗有好感卻因人設假裝矜持,裝着裝着上癮了
29.2萬字8.18 422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