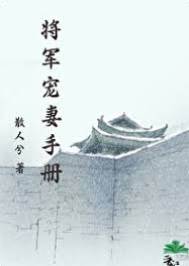《問鼎宮闕》 第64章 打臉
夏雲姒竭力地磨泡,頗有幾分恃寵而驕的味道,直至磨得他點了頭。
反正他都已看得滿目欣賞,便早晚會見那人的。若是如人,多半這一兩日就要來見;若是吉經娥,或許礙於先前的事一時不想見,可必定再尋機多加“偶遇”兩三回,遲早會讓他搖。
那便還不如來開這個口,占據幾分主。
是以用完午膳,趁著午後小歇時,他就著人去傳了那人過來。前宮人何等機靈,早已打聽清了是誰,不過一刻就將人傳了來。
是吉經娥。
夏雲姒見到是,未作掩飾的麵一冷,淡淡地垂下眼簾。
歡天喜地地進了殿來的吉經娥亦是臉上一僵,見禮間不無幾分窘迫。
自然窘迫,用這樣的爭寵手段後得了召見,誰能想到屋裡還有個別的人呢?
尤其還是個先前有過過節的人。
賀玄時也還記得先前的事,亦不喜這樣沒規矩又過於蠢笨的子,不由眉宇微皺。
剛開口,卻聽夏雲姒先笑道:“今兒和皇上同遊湖上,偶然得見經娥在亭中起舞。那舞從前不曾見過,且離得遠又看不清,便請經娥來再舞上一曲吧。”
吉經娥的麵愈發難看。
雖然那舞本來就是跳來邀寵的,可皇帝喜歡才邀寵,眼下這窈姬張口說要跳,是拿當什麼了?
賀玄時側首看看夏雲姒,原想勸說算了,但見滿麵的期待便又嚥了回去,也向吉經娥說:“是,舞不錯。窈姬磨了朕許久說想再看一遍,你便再跳來瞧瞧吧。”
吉經娥一時滿目錯愕,麵上怒更甚,卻又不敢發作,怔怔地滯在那裡。
夏雲姒心下玩味地想,吉經娥現下心裡應該很難過吧。
不論對皇帝說不說得上是真心,心謀劃了這樣一場,便總是希被珍惜的。皇帝卻隻依著旁人的話要求跳來看,這就是將的心意往地上踩。
Advertisement
可偏偏話都說到這兒了,這舞今天非跳不可。
不得不說,這吉經娥雖是可恨,但生得著實好看,流出兩分委屈的樣子連瞧著都有點不忍,無奈皇帝的心思沒在吉經娥上,也未顧及這份緒。
夏雲姒饒有興味地輕嘖一聲,略帶著半分輕佻逗弄說:“突然邀你來倒是我唐突了。不然這樣好不好?你好好地跳上一曲,除夕那日的事我便不同你計較了。”說著睇一眼皇帝,口吻嗔起來,“我一會兒央皇上賞你。”
吉經娥自聽得出的辱,然皇帝淡然不語,終是不敢說什麼,終是咬一咬牙,示意宮人去傳了樂師。
這一舞也不過小半刻就跳完了,舞是真好,賀玄時卻莫名覺得邊這適才便在有意賭氣的小人更加有趣。
是以整支舞他都看得心不在焉,待得一舞終了就揮退了吉經娥,一把將夏雲姒攏進了懷裡:“離除夕幾個月了,還記著仇跟較勁?心眼愈發小了。”
臉上毫無懼,反倒銜起笑來,垂眸輕聲:“皇上看出來了?”說著又笑一聲,信手從榻桌上揀了顆葡萄喂到他口中,“臣妾氣不過那樣欺負和貴姬罷了,皇上生臣妾的氣麼?”
的人臥在懷裡、還言輕語地說著話,他如何生得起起來?
明眸著他,辨出他的緒,竟還膽子更大了,抬手拍拍他的臉:“若不生氣,皇上就要幫臣妾賞,臣妾適才都誇下海口了呢。”
他低笑著俯吻:“說吧,怎麼賞?”
夏雲姒眼波流轉,在他上輕輕一咬:“晉一例位份,可好?”
他微微瞇眼,笑意變得促狹:“這麼刻薄,可真不是什麼賢惠姑娘。”
著他眨眼:“那皇上不喜歡了麼?”
Advertisement
語聲上挑,挑心絃,挑得他再度深吻而下,許久都不捨得將放開。
從除夕便失寵的吉經娥為晉一例了徽娥,訊息一夜間就傳遍了行宮。
與之一同散開的是晉位的原因。
就連灑掃宮道的使宮人一時間就在竊竊私語,說吉徽娥可真是慘,失寵近半年,皇上再沒翻過一次牌子,大約早忘了是誰。末了被窈姬娘子當舞姬一般傳了去,跳了支舞讓窈姬高興了,便晉了位份。
“說是晉位,其實是打的臉吧!”
“倒還幫和貴姬出了一口惡氣,宮裡頭還沒見過這般以下犯上的人呢!”
在有心的推波助瀾下,這樣的話被津津樂道了幾日都未消散。
而後,卻聽聞吉徽娥當真被“打了臉”,還在人來人往的地方被罰跪了半個時辰。
這卻是出乎夏雲姒意料之外的,聽聞後也不由一怔:“怎麼回事?”
小祿子笑嘆一聲:“嗨,吉徽娥著實是腦子不靈,聽得宮人議論氣得,發落了宮人便是,偏要編排您與和貴姬,聽聞還大罵和貴姬生下的孩子也……不會是什麼好的。恰巧上一位太妃路過,哪裡聽得了這般詛咒皇嗣的事,當即讓人賞了二十個,跪在那兒思過呢。”
夏雲姒輕笑:“罰得不冤。”
小祿子又道:“二十個,一時半會兒是消不了腫了。再者那條道恰是鵝卵石道,修建時工匠挑細選的鵝卵石,鑲得漂亮,跪半個時辰可就不好了。”
“若好,哪拘得住那張沒邊兒的呢?”夏雲姒淡聲,略作思量,又道,“不過這般鬧上一場,怕是更要視和貴姬為眼中釘了。”
“是。”小祿子躬,“下奴聽聞吉徽娥罵出的話裡,便有指摘和貴姬在皇上耳邊吹風的意思。瞧著是不敢太怨您,便索都怪到和貴姬上。”
Advertisement
“可見也是個沒本事的。”夏雲姒搖搖頭。
可有時偏是這樣沒本事的,反讓人小覷不得。因為沒本事才心思更淺,做事更不計後果,就如瘋狗咬人一般反教人難以防備。
循循地沉了口氣:“和貴姬有著孕呢,你們暗中把吉徽娥盯住。邊的宮人但凡出行宮,我一應都要知道。”
“諾,這個好辦,您放心。”小祿子應下就告了退,夏雲姒自顧自地又思量了會兒,覺得倒也不必擔憂太多。
說到底,吉徽娥不比貴妃昭妃與覃西王有牽連、又都出自宦人家,多有些基。
吉徽娥是從斯遠嫁而來的,在京中毫無勢力可言,又子淺薄,在宮裡應是也培養不出什麼親信幫辦事。盯住行宮的出記檔,應是足以察覺異樣了。
不出時日,果真就尋出了些端倪。
邊的宦有去幫買點心的、有去附近的集上幫淘新鮮玩意兒的,這都稀鬆平常。隻有個宮的出記錄耐人尋味——每兩日出去一次,說是去附近的集上走走,回來的時間也大抵對得上這路程,隻是每次出都是兩手空空,什麼也不見買。
這般去集上閑逛的宮,豈有次次都空手而歸的道理?就是鶯時這樣不買東西的偶爾出了門,也多會買些有趣的小回來。
更何況這人還有個拗口的名字,一瞧就是吉徽娥從斯帶來的人。
所以雖沒有實證,但此事若沒問題,夏雲姒半點都不信。
螳螂捕蟬黃雀在後,倒又白撿了個便宜。
原本並未想著要用這孩子將吉徽娥算計進來,隻想讓皇帝難過一場、以此謀得想要的便好。
無奈吉徽娥偏在這個時候自己往外跳。
既如此,找個機會收拾了吉徽娥、順便博得和貴姬的愧疚與信賴,倒也不妨礙原本讓皇帝難過的打算。
Advertisement
一箭三雕,何樂而不為呢?
隻是,這機會最好來得快一點兒。
這孩子已經快三個月了,若等到四五個月,胎傷與否還可另說,慢慢地顯了形不好再瞞便首先是個麻煩。
可乾著急也沒用,夏雲姒這陣子便分外信起了神佛,日日都會在佛前跪上兩刻、念一念經,祈求佛祖給個機會,讓心想事。
小半個月後,佛祖還真顯了靈。
這日正虔誠禮佛,鶯時進了屋,揮退旁人,在邊也跪下,音道:“和貴姬近來總覺得煩悶,皇上便賜一席船宴解悶兒,和貴姬邀了各宮嬪妃同往,剛傳了人來請您。”
夏雲姒點點頭:“什麼時候?”
鶯時道:“就今日傍晚。”
便又問:“吉徽娥可去麼?”
“若您先前所想沒錯。”鶯時抿一抿,“大概必是要尋一套說辭前去的。”
夏雲姒微微笑了笑,偏首示意鶯時退下,而後麵朝著那尊慈祥又威嚴的金佛,五投地地叩拜下去。
佛祖在上,信夏雲姒,一會兒要去害人了。
這人不似昭妃,與我姐姐的事並無什麼關係,算來我還真有那麼一點點愧悔。
所以這筆賬要怎麼記隨您的意,待得了阿鼻地獄、抑或轉世回之時,也隨您要我怎麼還。
但求您莫要慈悲為懷,發善心擋了我路。
您若非擋我的路,明兒個我就將您的金撤了,換太乙真人來供上。
漫天神佛都等著香火供奉,誰幫我我信誰。
你們都不幫我,我就都不供了,還不必擔心死後下地獄了呢。
滿懷戲謔地將這番話唸完,又磕了幾個頭,倒還算磕得虔誠。
站起,還端端正正地敬了三炷香。
輕聲籲氣,夏雲姒默唸著“阿彌陀佛”,轉離開了供佛的廂房。
船宴,從氛圍上來說,也算是紙醉金迷了。
正合喜歡的妖嬈的妝,也襯這一場大戲。
問鼎宮闕
問鼎宮闕
猜你喜歡
-
完結2476 章
一世傾城:冷宮棄妃
那一夜,她褪去了少女的青澀,成為冷宮深處的悲傷漣漪...... 那一天,她跪在他的腳下苦苦哀求,她什麼都不要,只想要出宮,做個平凡女人... 幾個風神俊秀的天家皇子,一個心如止水的卑微宮女... 當他們遇上她,是一場金風玉露的相逢,還是一闕山河動蕩的哀歌......
600.3萬字7.94 728802 -
完結1946 章

農女雙雙的種田悠閒生活
老穆家人人欺負的傻子穆雙雙,突然有一天變了個樣!人不傻了,被人欺負也懂得還手了,潑在她身上的臟水,一點點的被還了回去。曾經有名的傻女人,突然變靈光了,變好看了,變有錢了,身邊還多了個人人羨慕的好相公,從此過上了悠閒自在的好日子!
341萬字8 118440 -
完結1858 章
王妃她不講武德
寧孤舟把劍架在棠妙心的脖子上:“你除了偷懷本王的崽,還有什麼事瞞著本王?”她拿出一大堆令牌:“玄門、鬼醫門、黑虎寨、聽風樓……隻有這些了!”話落,鄰國玉璽從她身上掉了下來,他:“……”她眼淚汪汪:“這些都是老東西們逼我繼承的!”眾大佬:“你再裝!”
326.8萬字8.18 263247 -
完結266 章

邪帝溺寵妖孽冷妻
前塵愛錯人,家族滅,自爆亡。今世重來,她要擦亮眼睛,右手靈氣,左手煉藥,她一路升級打怪,斗皇室,滅渣男,扶家族,憑借自己的能力傲世與這個以實力為尊的世界。 而她的身邊,也多了一個真正可以與她攜手并肩的妖孽男人,傾世風華只為她一人展顏,翻手為云覆手為雨,只為護她亂世周全。
78.1萬字8 32780 -
完結112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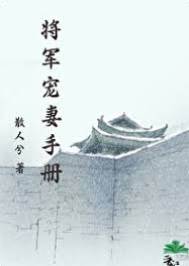
將軍寵妻手冊
雲府長女玉貌清姿,嬌美動人,春宴上一曲陽春白雪豔驚四座,名動京城。及笄之年,上門求娶的踏破了門檻。 可惜雲父眼高,通通婉拒。 衆人皆好奇究竟誰才能娶到這個玉人。 後來陽州大勝,洛家軍凱旋迴京那日,一道賜婚聖旨敲開雲府大門。 貌美如花的嬌娘子竟是要配傳聞中無心無情、滿手血污的冷面戰神。 全京譁然。 “洛少將軍雖戰無不勝,可不解風情,還常年征戰不歸家,嫁過去定是要守活寡。” “聽聞少將軍生得虎背熊腰異常兇狠,啼哭小兒見了都當場變乖,雲姑娘這般柔弱只怕是……嘖嘖。” “呵,再美有何用,嫁得不還是不如我們好。” “蹉跎一年,這京城第一美人的位子怕是就要換人了。” 雲父也拍腿懊悔不已。 若知如此,他就不該捨不得,早早應了章國公家的提親,哪至於讓愛女淪落至此。 盛和七年,京城裏有人失意,有人唏噓,還有人幸災樂禍等着看好戲。 直至翌年花燈節。 衆人再見那位小娘子,卻不是預料中的清瘦哀苦模樣。雖已爲人婦,卻半分美貌不減,妙姿豐腴,眉目如畫,像謫仙般美得脫俗,細看還多了些韻味。 再瞧那守在她身旁寸步不離的俊美年輕公子。 雖眉眼含霜,冷面不近人情,可處處將人護得仔細。怕她摔着,怕她碰着,又怕她無聊乏悶,惹得周旁陣陣豔羨。 衆人正問那公子是何人,只聽得美婦人低眉垂眼嬌嬌喊了聲:“夫君。”
17萬字8.33 5690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