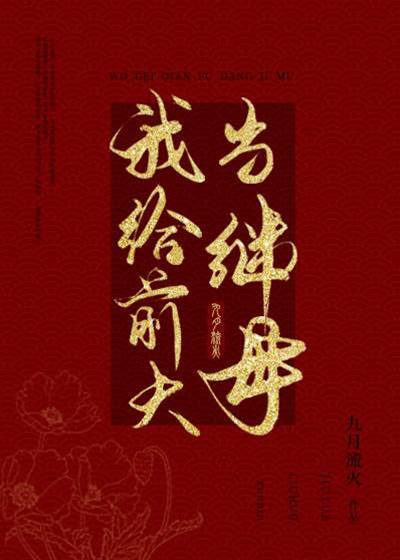《攻玉》 第133章 (1)
藺承佑帶著滕玉意上前同長輩們一一見禮。
一圈下來,滕玉意得了不寶貝。
關公公也從宮里帶來了圣人和皇后的賞賜,笑著對藺承佑和滕玉意說:
“清元王府的宅邸是王爺和王妃日后的新居,修葺上斷乎馬虎不得。
圣人指了宮廷將作大匠馮瑜親自打造,只是再好的工匠也只能雕琢大,細小之還得由殿下和王妃自行斟酌,趁這幾日休沐無事,殿下不如帶著王妃到親仁坊多走幾趟,若有什麼新的想頭,也好及時告知馮大匠。”
藺承佑和滕玉意謝恩領賞。
舅父瞿子譽素來偏疼外甥,聞言頷首道:
“ ‘清元’‘清元’,這封號對大郎而言,倒是再切不過。
這孩子可不是生來便以‘滌瑕穢’為己任?
打小跟著他師公捉妖降魔,十一二歲便能獨當一面,過后又到大理寺供職,奇案詭案之類的沒破。”
外祖母瞿陳氏接話說:
“說到這個,記得有一回南城有只花妖幻化貌婦人四吃人心肝,那時候佑兒也才十二三歲,追了三天三夜,到底把這妖怪逮住了。
花妖看大郎年歲小,妄圖用花言巧語迷他,結果被大郎直接摁到地上打了一灘花泥,巧我們也在,看得我心肝直,他阿娘倒好,一個勁地在旁邊好,真可謂有其母必有其子。”
藺效微微一笑,沁瑤哭笑不得:
“娘,您說大郎便說大郎,何苦說到兒頭上。”
滕玉意甚聽到藺承佑這些兒時趣事,自是聽得津津有味。
藺效怕妻子窘迫,對兒子兒媳說:
“好了,師公想必也惦記著你們,這邊見過禮了,到青云觀給師公磕頭去。”
滕玉意便隨藺承佑起了,瞿沁瑤招手讓滕玉意近前:
Advertisement
“你那把神劍是不是找不回來了?”
滕玉意憾地說:
“是。”
“你本就不懂道,如今連趁手的法都沒有了,日后就算跟佑兒一同降妖,怎好為自己積攢功德。”
瞿沁瑤低嗓門說,“你師公那兒寶貝多,待會去青云觀,你自管讓佑兒幫你向師公討法,師公為賀你們新婚之喜,自會準備禮,你只管挑最好的要,師公就算上不樂意,末了也會給你的。”
滕玉意赧然點頭。
瞿沁瑤說完一抬眼,發覺兒子正注視這邊,低笑著說:
“以佑兒的子,多半一早就替你在打他師公那堆寶貝的主意了,回頭到了青云觀,佑兒搶都會幫你搶一件。
去吧。”
藺承佑拉著滕玉意向眾位長輩告別:
“晚輩帶阿玉去給師公請安。”
到了青云觀,下車前藺承佑果然攔住滕玉意:
“待會見了師公你先別說話,看我的眼行事。”
滕玉意眼睛一亮:
“你要幫我討寶貝麼?”
藺承佑托起滕玉意的雙手打量,一臉嫌棄的樣子:
“你瞧瞧你,號稱跟端福學了快一年的功夫,連幾個賊都打不倒,雖說輕功還不錯,那還是有我渡給你的力做底子,我估著以你這進度,說要個三年五載才能有點樣子。
這回出遠門,我們除了要去南,順便還得去濮、江南等地捉捉妖,要是再不幫你弄點好寶貝,你可就要拖我的后了。”
滕玉意秀眉一挑:
“呵,依我看,端福可真冤枉,想當初我第一回完完整整學武功,還是世子教的那套桃花劍法呢,真要說起來,你才是我的師父。
徒兒學得慢,師父不幫著找補誰幫著找補?”
“這不是幫你找補來了嗎?
Advertisement
稍后你看中哪樣法只管給我使眼,我保證替你討來。”
滕玉意心里一高興,環住藺承佑的脖頸:
“那你得先告訴我哪樣法最好。”
藺承佑了滕玉意的臉頰:
“師公那兒就沒有差的,況且越是好的法越認主,你能看上人家,也得人家能看上你才行。
反正你待會兒別說話,師公他老人家小氣得很,同他老人家要東西,還屬我有法子。”
滕玉意笑瞇瞇說好。
兩人剛邁上臺階,絕圣和棄智旋風般迎出來了。
“師兄,滕娘子。”
觀里的幾個老修士含笑提醒:
“該改口嫂嫂了。”
絕圣和棄智樂呵呵:
“師兄,嫂嫂,師公在經堂等你們呢。”
說著風一般跑回耳房,沏茶端點心忙得不亦樂乎。
滕玉意隨藺承佑往走,青云觀松柏參天,一派道家清幽世界,多虧絕圣和棄智說笑才不顯得太寂寥。
清虛子端坐在經堂的團上打坐,藺承佑帶著滕玉意上前磕頭:
“師公,徒孫和阿玉來給您請安了。”
清虛子掀了掀眼皮:
“起來吧。”
這會兒老修士們端著茶進來了,滕玉意恭恭敬敬奉茶到清虛子面前:
“師公,您請喝茶。”
清虛子依舊板著臉,眼底卻微笑意,一甩拂塵,右手接過茶盞,喝完茶,用廛尾指了指一邊的托盤:
“佳偶天,琴瑟和鳴,那是師公為賀你們新婚之喜準備的,拿著吧。”
藺承佑瞟了瞟,托盤上放著兩柄犀角黃金鈿莊如意,也不知師公他老人家從哪個旮旯角翻出來的,看這樣式,多半是宮里往年的賞賜。
另有兩塊金元寶,倒像是師公自行準備的,元寶倒是黃澄澄的,然而個頭只比栗子大那麼點兒。
Advertisement
他簡直頭疼,早知道師公這般摳門,他就該提前送些金銀玉到觀里。
滕玉意覷見藺承佑的表,忍笑端起托盤,將其高舉過額頭,朗聲道:
“阿玉多謝師公。”
清虛子抬手:
“起來吧起來吧。”
二人剛坐下,藺承佑突然對絕圣棄智道:
“你們倆的四輔和七部學得怎麼樣了?”
絕圣棄智端著點心托盤的手一抖:
“還……
還沒學完呢。”
藺承佑嘆氣:
“年歲太小,學藝不,師兄也不指這回去濮你們能幫上什麼忙了。”
說罷對清虛子說:
“師公,如今只知濮那妖法力不差,卻也不知對方究竟什麼來頭。
伯父指了五道和絕圣棄智同我一道去,但五道慣喝酒誤事,絕圣和棄智尤其靠不住。
原本阿玉有小涯劍,以阿玉的慧黠,往常還能同徒孫一起對付妖邪,可如今的法也沒了。
真到了要關頭,說不定只有徒弟一人支應。
師公,徒孫邊總不能一個得用的人都沒有,您老幫著想想法子。”
清虛子一抖胡子:
“師公想不出法子。”
藺承佑笑道:
“無妨,其實徒孫都幫您把法子想好了。”
“噢?
那便恭喜了。”
清虛子慢條斯理抖抖袍袖起了,“你帶阿玉在觀里轉轉,師公回上房打坐去了。
藺承佑攔住師公,笑著說:
“徒孫的話還沒說完呢,這法子在您上。”
清虛子用力扯回自己的袍袖:
“你那些壞法子,師公不聽也罷。”
說罷,款步往外踱去。
奇怪的是這回藺承佑居然沒攔他,清虛子慢悠悠走到回廊上,陡然意識到不對勁,略一琢磨,探手往寬大的袍袖一,那把他從不離的庫房鑰匙果然不見了。
Advertisement
“好你個臭小子!”
等到清虛子趕到庫房時,藺承佑早把他庋藏多年的寶貝們搬下來了。
十來個陀螺鈿寶箱,或大或小,或長或扁,全都敞著盒蓋,滿屋靈四溢。
藺承佑和滕玉意蹲在箱蓋前挑挑揀揀,絕圣棄智也傻乎乎在邊上幫著出主意。
清虛子一個箭步上前,對準徒孫的后腦勺就是一個栗:
“臭小子,不給你你便是不是?”
藺承佑生生挨了這一下,回頭時一臉無辜:
“徒孫這也是為了您老著想。
此去濮,徒孫對那妖邪的底細一無所知,稍有不慎就會折胳膊折的,如果阿玉能有件趁手的法,徒孫除妖時好歹也有個得力幫手。
絕圣和棄智就更別提了,倘或徒孫和阿玉了傷,他倆也未必能全須全尾回來,到那時候,最心疼的還不是您老麼。”
“心疼不起。
折胳膊折又如何?
橫豎還能長回來。”
清虛子吹胡子瞪眼,話雖這麼說,到底沒把東西搶下來,被藺承佑好說歹說攙扶著坐到一旁。
安好師公,藺承佑拽著滕玉意重新蹲到箱籠前,挑揀一晌,舉起一個樣式古怪的小神龕,回頭對清虛子說:
“您瞧,這個金銀甲龕阿玉拿著是不是正好。”
清虛子懶得搭腔。
絕圣和棄智撓撓頭:
“這個太笨重了,提在手上不好施展。”
滕玉意瞧見藺承佑給使的眼,故意將其托在掌心里掂了掂:
“是有點沉。”
清虛子沒眼看,這挑挑揀揀的架勢,簡直把青云觀的庫房當西市的貨肆了。
他閉上眼睛捋胡子。
藺承佑鼓搗一晌,又掏出一柄紅牙撥鏤尺:
“這個夠輕便了。”
滕玉意搖頭:
“太長了,也太了,平日不好藏到上。”
“那這個呢?”
這回藺承佑干脆取出一把螺鈿紫檀阮咸。
滕玉意很“為難”的樣子:
“……
這也太大了……
況且我不會彈阮咸。”
“蠢小子,你就不能挑一件阿玉能隨時揣在上的嗎?”
清虛子終于沒忍住搭腔了,“你瞧瞧你挑的這都是什麼?”
藺承佑和滕玉意相視一笑,忙皺眉應道:
“徒孫愚鈍,但求師公親自指點。”
“瞧見那雙絳繡線鞋了?
此鞋名引商鞋,取自‘引商刻羽之音’,乃當年元道君邊最善音律的金仙子所制,里頭藏著九地三十六音,慣能迷邪祟,主人越通音律,便越能借此鞋克制邪祟,阿玉穿上這鞋,也就不用琳琳瑯瑯帶上一堆東西了。
“還有那個墨繪彈弓,里頭藏著三昧真火,弓才掌大小,藏在袖子里毫不突兀。
“那個瑪瑙銀薰球紫靈天章球,看著與尋常香囊無異,里頭卻藏著兩條影玉蟲翅,擲地后能化作一對玉蝴蝶,一只蝶翅上纂寫著太上大道君的《大東真經》另一只蝶翅上寫著《命召咒文》法力雖不算多強,但也能幫主人抵好一陣邪魔了,此系在上,豈不比阮咸之類的樂輕便甚多?”
藺承佑邊聽邊把這三樣寶貝找出放到滕玉意面前:
“聽見了?
這是師公賞你的,還快謝謝他老人家。”
滕玉意痛快上前稽首,揚聲道:
“多謝師公賞寶。”
清虛子心腸一,俯攙起滕玉意,然而對著藺承佑時,依舊沒什麼好臉:
“東西好歸好,也得看人家認不認主,先讓阿玉試試。
臭小子,到院中起壇去。”
藺承佑忙捧著三樣法出了屋,先將其放到院中的供案上,忙活得差不多了再請師公壇。
清虛子步罡踏斗,逐一扯下法上的封條,一場法事做下來,三樣法上方的寶似乎更為熾目了。
藺承佑把滕玉意拉到供案前:
“現在可以試了。”
滕玉意最興趣的是那雙引商鞋,好奇上前了,約覺鞋在,只當是錯覺,剛要將其捧下供案,那雙鞋突然像長了腳似的,自行從供案上跳下來,啪嗒啪嗒往另一頭跑了,虧得藺承佑手極快,才將其逮回來。
清虛子搖了搖頭:
“這雙鞋的第一任主人金仙子,第二任主人是玄真人。
兩位真人都是出了名的態,這鞋習慣了那樣的重量,怕是不喜歡格輕盈的主人。”
那就沒法子了。
清虛子忽又一拍腦門:
“瞧師公這記,那枚紫靈天章球素來只認蘊道家真氣的主人,阿玉不通道,香球未必肯認。”
猜你喜歡
-
完結1597 章

嫡長女她又美又颯
前世,鎮國公府,一朝傾塌灰飛煙滅。 此生,嫡長女白卿言重生一世,絕不讓白家再步前世后塵。 白家男兒已死,大都城再無白家立錐之地? 大魏國富商蕭容衍道:百年將門鎮國公府白家,從不出廢物,女兒家也不例外。 后來…… 白家大姑娘,是一代戰神,成就不敗神話。 白家二姑娘,是朝堂新貴忠勇侯府手段了得的當家主母。 白家三姑娘,是天下第二富商,翻手為云覆手為雨的商界翹楚。 · 白卿言感念蕭容衍上輩子曾幫她數次,暗中送了幾次消息。 雪夜,被堵城外。 蕭容衍:白姑娘三番四次救蕭某于水火,是否心悅蕭某? 白卿言:蕭公子誤會。 蕭容衍:蕭某三番四次救白姑娘于水火,白姑娘可否心悅蕭某? 白卿言:…… 標簽:重生 寵文 殺伐果斷 權謀 爽文
284.8萬字8 157245 -
完結10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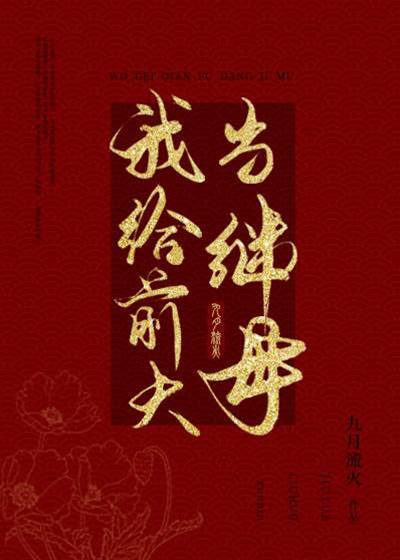
我給前夫當繼母
【微博:晉江九月流火】林未晞死了一次才知,自己只是一本庶女文中的女配,一個用來反襯女主如何溫柔體貼、如何會做妻子的炮灰原配。 男主是她的前夫,堂堂燕王世子,家世優越、光芒萬丈,而女主卻不是她。 女主是她的庶妹,那才是丈夫的白月光,硃砂痣,求不得。 直到林未晞死了,丈夫終於如願娶了庶妹。 她冷眼看著這兩人蜜裡調油,琴瑟和鳴,所有人都在用庶妹的成功來反襯她這個元妻的不妥當。 林未晞冷笑,好啊,既然你們的愛情感動天地,那我這個姐姐回來給你們做繼母吧! 於是,她負氣嫁給了前夫的父親,前世未曾謀面的公公——大齊的守護戰神,喪妻后一直沒有續娶,擁兵一方、威名赫赫的燕王。 後來,正值壯年、殺伐果決的燕王看著比自己小了一輪還多的嬌妻,頗為頭疼。 罷了,她還小,他得寵著她,縱著她,教著她。 #我給女主當婆婆##被三后我嫁給了前夫的父親#【已開啟晉江防盜,訂閱比例不足70%,最新章需要暫緩幾天,望諒解】*************************************************預收文:《難消帝王恩》虞清嘉穿書後,得知自己是女配文里的原女主。 呵呵……反正遲早都要死,不如活的舒心一點,虞清嘉徹底放飛自我,仗著自己是嫡女,玩了命刁難父親新領回的美艷小妾。 這個小妾也不是善茬,一來二去,兩人梁子越結越大。 後來她漸漸發現不對,她的死對頭為什麼是男人?他還是皇室通緝犯,廢太子的幼子,日後有名的暴君啊啊啊! ***本朝皇室有一樁不足為外人道的隱秘,比如皇室男子雖然個個貌美善戰,但是卻帶著不可違抗的嗜血偏執基因。 慕容珩少年時從雲端摔入塵埃,甚至不得不男扮女裝,在隨臣後院里躲避密探。 經逢大變,他體內的暴虐分子幾乎控制不住,直到他看到了一個女子。 這個女子每日過來挑釁他,刁難他,甚至還用可笑的伎倆陷害他。 慕容珩突然就找到了新的樂趣,可是總有一些討厭的,號稱「女配」 的蒼蠅來打擾他和嘉嘉獨處。 沒有人可以傷害你,也沒有人可以奪走你,你獨屬於我。 他的嘉嘉小姐。 註:男主偏執佔有慾強,祖傳神經病,女主虞美人假小妾真皇子與作死的嫡女,點擊作者專欄,在預收文一欄就可以找到哦,求你們提前包養我!
36.9萬字8.36 64041 -
完結427 章

後宮之華妃重生
華妃年氏,前世含恨而終。 不曾想,自己居然重生了。 再次醒來,知道自己的孩子不是端妃所害,對皇上有恨也有愛。 恨的是,他利用自己的感情與對他的癡心顛覆了整個年家, 愛的是,年少時自己所付出真心的那個他。 可是前一世要不是自己蠢笨,怎會樹立了那麼多的敵人,以至於牆倒眾人推,還連累了哥哥與侄子。 不管怎麼樣,這一世自己不能再讓哥哥如此行事,凡是還是要低調。而且自己如果想要保全年氏一族,那麼雖然說要靠皇上的寵愛,可是她也知道,隻要自己不過分,皇上憑著對自己的愧疚,也不會為難自己。 想到甄嬛會成為太後,那麼自己何不與她為伍,不爭不搶,安穩度過這一生足以。
73.5萬字8 9847 -
完結447 章

太子妃今天真夠野
現代頂級神醫,穿越成了廢物太子妃。 綠茶陷害?庶女欺壓,太子厭棄。 這還能行? 她一一反擊教他們重新做人!而,面對肚子里不知道哪里來的野種,蘇月徹底慌了…… 妖孽太子:愛妃,別天天這麼張牙舞爪的,小心嚇壞了你肚子里的孩子。
83.5萬字8.18 13365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