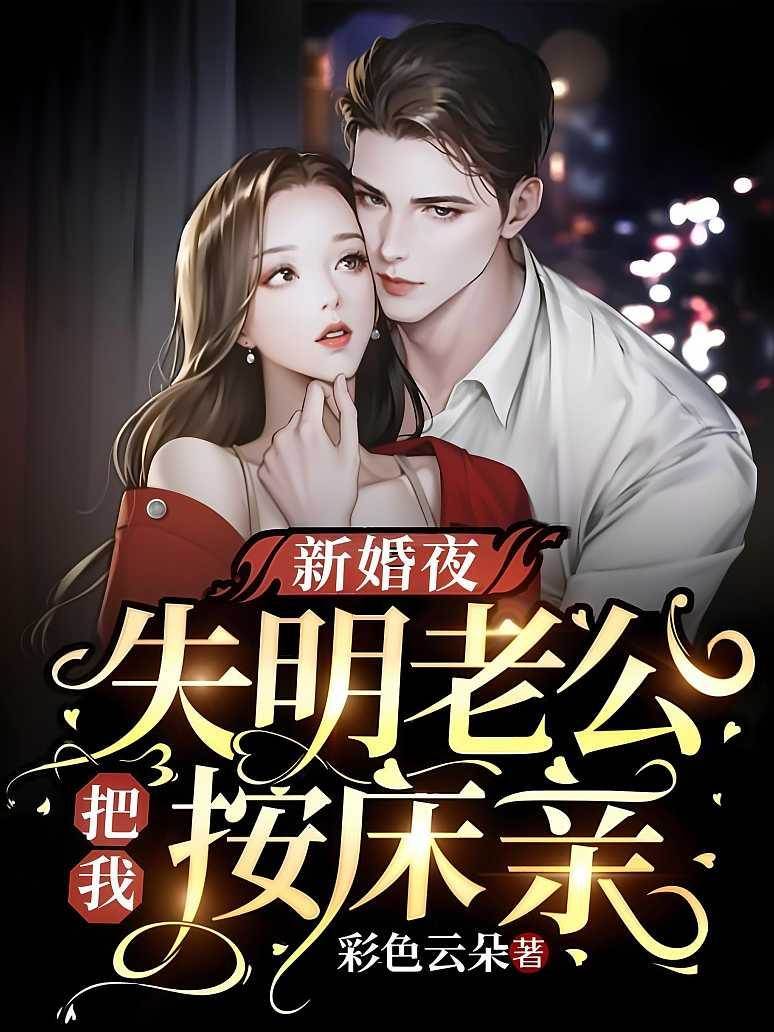《她是翟爺掌中嬌》 第40章半月期限未到
「答應幫你看家的前提是你不在家。」據理力爭。
「所以你要食言?」他反問。
「……」
明明他就已經回來了,可以離開的,怎麼就變是食言了呢?
「你當初說了,回來的時間不確定,半月隻是你給的一個大概期限,它也可能是半月,也可能是一天,潛在意思不就是你這趟出差回來我就可以離開?」
翟南詞:「……」
剖析能力倒是強。
他深眸注視著,麵淡定:「半月為期,到時候不管我回不回來,你都會離開。這話是你說的?」
愣了愣,點頭:「沒錯。」
「也就是說,半個月的時間,不管我回與不回,你屆時都會離開,是這個意思麼?」
「是。」
「那半個月到了嗎?」
「……」
再一次無以反駁。
這時,他突然移步,讓開了一條道。
裡卻說道:「如果你是想食言,那……隨你吧。」
Advertisement
說完,一副『我也無可奈何』的樣子。
暮沉沉:「……」
就像是被瞬間釘在了地板上,讓寸步難移。
背信棄義的事,或許這一輩子都不可能發生在上吧。
一諾千金,這是外公從小教的做人道理。
著幽怨的眸子瞭了他一眼,拖著箱子,默默的轉!
重新又回到了二樓!
著上樓的背影,翟南詞眸底的和煦濃了幾分,角的淺弧也加深。
後的墨羽:爺,您厲害!
就在墨羽心中暗自佩服時,翟南詞忽地轉過臉,看向他。
眼底的和煦不再,取而代之的是嚴寒。
「去查一下,沉沉在室裡是不是遭了什麼罪。」
「是!」
墨羽領命離開。
……
夜已深沉。
二樓的客臥。
經過在室裡的幽閉恐懼,暮沉沉今夜不敢關燈。
平時都會留有一盞小燈,今夜是連頂上的吊燈都不敢關。
Advertisement
一室明亮,才能讓飽恐懼的心得以漸漸平復。
次日清晨。
東屋。
一早,二夫人陳娉茹就聽到了手下的報備。
「什麼,人沒了!?」
保鏢低著頭:「是。」
陳娉茹氣急:「你們是幹什麼吃的!那麼大的一個人關在室裡怎麼就沒了?」
把的犬傷那樣,還想著好好的上那丫頭幾天呢,結果才一夜,人居然就沒了。
麵對暴跳如雷的二夫人,保鏢弱弱的開口:「是……翟爺,人是翟爺帶走的。」
陳娉茹一怔。
翟爺?
南詞?
「你說……南詞?他不在國外麼?」
「昨晚淩晨,翟爺突然回來,而且明顯是奔著那孩兒來的,一到室門口,直接就將門給踹了。」
門……給踹了?
陳娉茹不由得愕住。
之前那孩兒就說隻南詞要留下的,難不和南詞之間真有著匪淺的關係?
這可能麼!
整個翟家誰不知道南詞對人天生厭惡,就是麵對大嫂,他也是一副冰山態度。
「你們……沒弄錯?」不確定的詢問著保鏢,因為這訊息實在是……有點不可靠。
保鏢:「昨晚翟爺親自的手,不會錯的。」
陳娉茹:「……」
猜你喜歡
-
完結990 章

女扮男裝出逃后,我被薄爺通緝了
游離是薄爺養在家里的小廢物,打架不行,罵人不會,軟軟慫慫慣會撒嬌。薄爺對游小少爺就兩個要求,一,八點門禁,二,談戀愛可以,但不能越線。薄爺只顧防著女孩子,卻沒想到真正該防的是男人。游離——懷孕了!薄爺承認自己瞎了眼,這些年,竟沒看出游離女扮男裝。那日,聯盟直播間里千萬人在線,薄爺沉臉誤入。“游離,你肚子里的孩子是哪個狗男人的?我非扒了他的皮。”眾人皆驚,他們的老大竟然是女的?電競同盟:“老大,別玩游戲,安心養胎。”賽車基地:“多生幾個,別浪費了老大的好基因。”黑客組織:“把我們老大睡了的男人,...
166.1萬字8 38654 -
完結74 章

失控
向嘉事業受挫回鄉靜養,陰差陽錯事業開了第二春,還養了個天菜男友。事業漸入佳境,平步青云,她要回到曾經所在的富貴圈了。離開的前一晚,向嘉點了一支事后煙,跟林清和道
29.7萬字8 18957 -
完結13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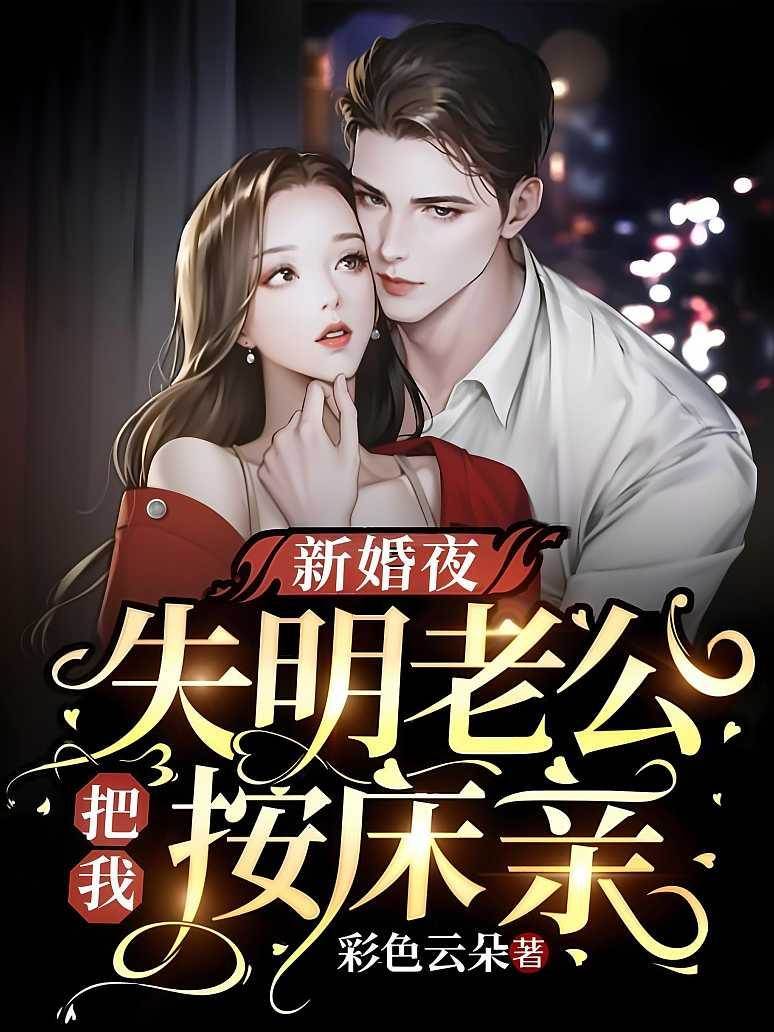
新婚夜,失明老公把我按床親
鄉下的她剛被接回來,就被繼母威脅替嫁。 替嫁對象還是一個瞎了眼的廢材?! 村姑配瞎子,兩人成了豪門眾人笑柄。 她沒想到,那個眼瞎廢材老公不僅不瞎,還是個行走的提款機。 她前腳剛搞垮娘家,后腳婆家也跟著倒閉了,連小馬甲也被扒了精光。 她被霸總老公抵在墻上,“夫人,你還有什麼秘密是我不知道的?” 她搖了搖頭,“沒了,真的沒了!” 隨即老公柔弱的倒在她懷中,“夫人,公司倒閉了,求包養!” 她:“……”
24.7萬字8 1446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