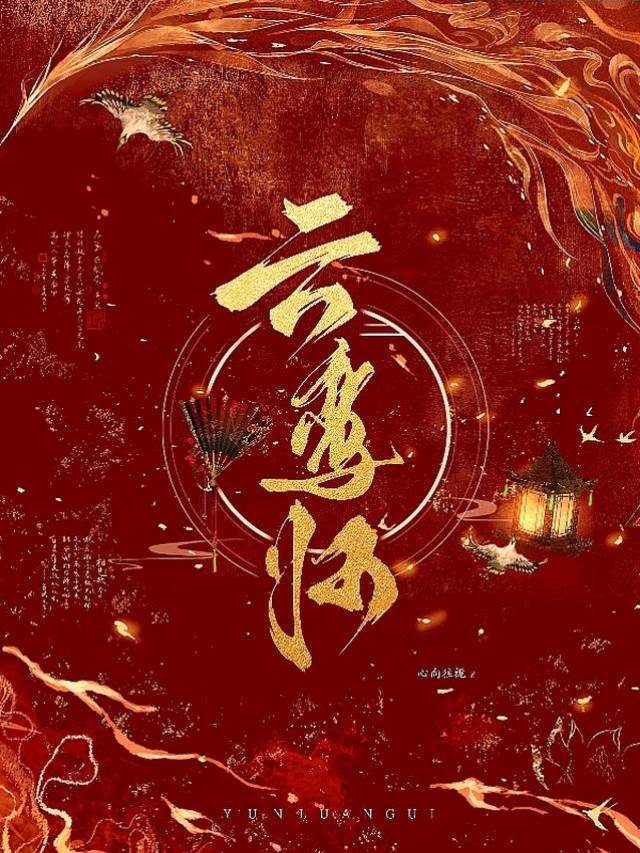《替嫁以后》 第39章
房花燭夜,金榜題名時,是人生的四大樂事之二,前者是小登科,后者是大登科。
岑永春今日將要達前者,然而他心中的喜悅,毫不下于狀元房,大小連登科——或者說,還要有過之而無不及。
這份飽滿昂揚的喜悅都是他去迎來的新娘子帶給他的,而在他騎著高頭大馬,戴紅花地回到隆昌侯府以后,一眼見到正要往里面走的方寒霄時,達到了頂峰。
“寒霄!”
他乃至于在馬上就了出來。
把在門外看熱鬧的眾人的目全引了過去。
方寒霄本來已經被下人引進府里了,他在男客那邊尋了一圈薛嘉言,沒找著,又出來等他,才耽誤到了這一會。
聽到呼喚,他淡淡轉頭,同時不聲地長胳膊把邊的薛嘉言攔了一攔。
薛嘉言不安分地想往外竄:“方爺,你別攔我,不揍他一頓,我心里這口氣下不去!”
他之前見到隆昌侯府過定禮時說要來灌醉岑永春,其實只是戲言,后來不多久由薛二老爺領著走通了錦衛同知的門路,就做校尉到宮里守大門去了,沒把這回事當真記著。
直到喜帖送到了建侯府,他換班回家,聽到下人議論,才知道岑永春究竟要娶誰,氣得暴跳,前天已經跑到平江伯府去過,約著方寒霄要去把岑永春打殘。
方寒霄把他攔下了,只說對徐月本來無意,不沒有什麼可惜之,薛嘉言本已有點被勸下了——徐月若好,沒有什麼對不住他兄弟之,那嫁別人就嫁別人罷,總不能攔著不人出嫁;若不好,那這種姑娘本也配不上他兄弟,去禍害別人最好。
他說服了自己半天,但這會一見岑永春那春風得意馬蹄疾的樣兒,全部破功了,就想把他從馬上拖下來一頓揍。
Advertisement
“寒霄是他的!誰跟他那麼!不要臉!”薛嘉言被攔著竄不出去,氣得只是碎念。
方寒霄意味不明地笑了笑,是的,他從前跟岑永春真的不,幾乎陌路。
所以,要不是有徐月這一出,他都不會確定他對他有這麼大怨念。
京中子弟無數,分門第分文武分才能,各自有各自的小圈子,從前方寒霄領頭的這個小圈子,跟岑永春是沒有集的。
沒什麼特別的原因,雙方就是合不來,他們相同的只有出,志趣都不相投,自然而然漸行漸遠——這是曾經的方寒霄以為的。
他那個時候,太年太飛揚也是太天真了,他不知道對于岑永春來說不是這樣。
岑永春曾經努力接近過他們的圈子,但是沒有功,被排斥了。
那個時候,方寒霄自己是平江伯世子,將來要接方老伯爺的要職;薛鴻興沒有子嗣,薛嘉言過繼給他是早晚的事,薛鴻興掌握的都督府雖然撈錢比不上漕運總兵,但是是中樞要職,位高權重;而岑永春呢,那個時候他的父親隆昌侯上只有一個閑職,于是他這個侯府世子,其實還比不上薛嘉言這個二房長子值錢——
外面看著差不多的子弟們,里面一,其實是差多的。
所以,對岑永春來說,他不覺得方寒霄他們不帶他玩只是跟他玩不到一塊去,他認為自己是被人瞧不起。
這些都是方寒霄到了外面,因故要查隆昌侯府的時候才順帶著查出來的,他為此有一些驚訝,驚訝過后,就沒什麼了,只是把它作為一樁事備案著,暫時并沒想到要怎麼用,又能不能用。
但世事吧,有時候不知道該怎麼說,他沒料到他孤返京沒幾天,岑永春就自己揮舞著把柄撲到他面前來了。
Advertisement
現在,方寒霄在眾目睽睽中,微笑著看著岑永春跳下馬來,昂首地走過來,忽然變得很絡地跟他打招呼:“寒霄,你能來,我真高興,以后咱們做了連襟,就是親兄弟一般的了,一會我單敬你三杯,你可不許早走,我不放人的!”
方寒霄笑著點了點頭。
他看上去仍是當初那樣耀眼,站在人群里仍如鶴立群,所以岑永春還隔著一段距離,都可以一眼把他認出來,岑永春心中為此有一點堵滯,但旋即又舒服起來——他怎麼可能不郁怒,不肯示弱在面上出來罷了,表面上裝得越好,心里肯定越嘔!
岑永春的目還往薛嘉言面上去轉了一圈,看見薛嘉言瞪眼看他,心中更抖擻了——風水流轉啊,當年一個二房的也敢不把他放在眼里,如今他伯父自己得了親生子,他一個侄兒,屁也不是了,想一想都痛快死人。
方寒霄心有別事,忍得下這口氣,薛嘉言可忍不了,拳頭當時就起來了:“看什麼看,沒看過爺?!”
他一直是這個脾氣,對不喜歡的人不肯敷衍的,岑永春從前就吃過他兩回排頭,那時心中深為不忿,但眼下卻覺得很心平氣和:“嘉言,你都多大了,怎麼還這麼沖?我聽說你如今有差事了,這是件好事,恭喜你,不過你得改改脾氣,不然難道在殿前當值時也這麼魯莽嗎?”
薛嘉言才聽他說了個開頭,白眼已經要翻上天了——所以他們從前就不樂意跟岑永春玩!仗著大他們兩三歲,想進他們的圈子也罷了,偏偏還想爭著做老大,一說話就教訓人,好好的,誰愿意多這麼個爹管著,憑什麼呀他。
“我怎麼當差,用不著你管,你撿別人的——哎呦!”
Advertisement
是方寒霄用力掐了他一把。
薛嘉言也知道自己將要口而出的話太難聽了,他子,但其實不怎麼會出口傷人,悻悻地住了口。
岑永春臉難看了一瞬,但很快把自己說服住了,他不是撿,他是搶!
生生從方寒霄手里搶過來的,還反手塞了個庶給他。
方寒霄迫于無奈,只有湊合著把庶認下了——沒有比這更能解他當年那份不得志的心了。
這個時候,噼里啪啦的竹聲已經放得告一段落,有人過來陪笑催他:“新郎,該箭踢轎門,請新娘子出來了。”
岑永春隨口道:“知道了。”
然后不再理會薛嘉言,繼續去跟方寒霄道:“寒霄,三天后我們要回門去,聽說之前你娶妻時,弟妹不慎撞著頭了傷,沒能回去?正好,這回我們一起回去,你可不要不到啊——就算心里有什麼不痛快的,也不能一輩子就不跟岳家來往了不是?想開點,嗯?”
他不著急去迎月出轎,只是等著,看見方寒霄聽見他的邀請后,眼神似乎變了一變,眼底抑住了一點什麼,他更舍不得轉開眼了,恨不得就駐足在這里欣賞。
娶徐月,值,太值了。
方寒霄跟他對視了片刻,快要抑不住眼底的緒似的,微微別過臉去,很草率地點了下頭,好像無法面對他,迫不及待地想把他打發走。
岑永春真是志得意滿,來催他的人把弓箭都遞過來給他,他接了,道:“那我們說好了啊,你要不去,我人到你府上請你去。”
這才走了,背影都是揚眉吐氣。
薛嘉言沖著他的背影揮了揮拳頭:“又聽說,聽說來聽說去的,他聽說的真不,跟那三姑六婆似的。”
Advertisement
方寒霄悠悠負了手,眼底抑住的緒終于傾瀉了一點出來——本不是怒氣,而是笑意。
果然,岑永春娶了徐月,是不會舍得不向他炫耀的,不過,他得意的程度仍然有一點超乎了他的預料,簡直如不了錦夜行的暴發戶一樣。
他連魚餌都不用放,他就上趕著浮上來咬鉤了。
而這不過是個開始,他們了連襟,以后肯定會更多地進行親近,當然,都是岑永春主,落在別人眼里——比如說隆昌侯眼里,他只是被迫,隆昌侯和方伯爺之間的齷齪不會牽連到他上,他就是清清白白,毫無問題。
“好!”
“好箭法!”
喝彩聲響起來,是岑永春向轎門邊上了一箭,同時竹聲喜樂聲又大作起來。
岑永春向前掀開了轎簾,方寒霄沒有興趣看了,扯一把薛嘉言,薛嘉言哼一聲:“便宜他了,不行,等會我一定要灌他,寒霄,你可不要再攔我了,我灌不死他。”
方寒霄在這上面確實沒必要阻攔,做口型:一起。
不讓岑永春覺出他的“失意不忿”,他怎麼會有力進一步來著他呢。
薛嘉言努力辨認了一下,高興了:“好!”
跟著他往里走去。
方寒霄不是虛言,等過小半個時辰之后,岑永春那邊拜堂等禮儀完了,過來敬酒,他伙同薛嘉言,是真把岑永春灌了個足。
有人來勸,他就乜斜著眼,要笑不笑,神間乃至有點江湖氣,擺明了他就是要找茬,岑永春見了,反而得意,他府里替他擋酒的堂兄弟們要代替他喝,他都不要,把人搡開,這是他至今為止喝得最香的酒,每一杯都是他年黯淡時的補償,怎麼可以由別人代替!
他就陪著方寒霄喝,喝得飄飄然,說話都大了舌頭。
方寒霄不會說話,他大不大舌頭是看不出來,不過他上一層重過一層的酒氣是明擺著的,看上去離醉也不遠了。
他們這一桌,幾乎是最后散的——還是岑永春已經醉暈了頭,他的兄弟們看他模樣不像,怕出丑,把他抬走了才了的局。
這時間里,瑩月一直在另一邊等著,越等越冷清,等到后來們那個廳人都快散了,要不是還有孟氏陪著,都要哭了:不會真被丟下了吧?
等終于被領著出去,見到方寒霄,本已委屈了,再聞著他一嗆人酒氣,更覺不樂意了,也不害怕他在這里刺激鬧事了,大著膽子指責了他一句:“你怎麼喝得這樣。”
要跟他一車回去的,好熏人。
方寒霄醉眼朦朧,把了一,忽然傾向前,照著的臉呵了口氣。
瑩月被撲面的酒氣熏得眼都閉了一閉。
待回過神來,就氣得跺了下腳。
他真是一點也不好!
猜你喜歡
-
完結480 章

穿書之沒人能比我更懂囂張
––伏?熬夜追劇看小說猝死了,她還記得她臨死前正在看一本小說〖廢材之逆天女戰神〗。––然后她就成了小說里和男女主作對的女反派百里伏?。––這女反派不一樣,她不嫉妒女主也不喜歡男主。她單純的就是看不慣男女主比她囂張,在她面前出風頭。––這個身世背景強大的女反派就這麼和男女主杠上了,劇情發展到中期被看不慣她的女主追隨者害死,在宗門試煉里被推進獸潮死在魔獸口中。––典型的出場華麗結局草率。––然而她穿成了百里伏?,大結局都沒有活到的百里伏?,所以葬身魔獸口腹的是她?噠咩!––系統告訴她,完成任務可以許諾...
86.1萬字8 11706 -
完結285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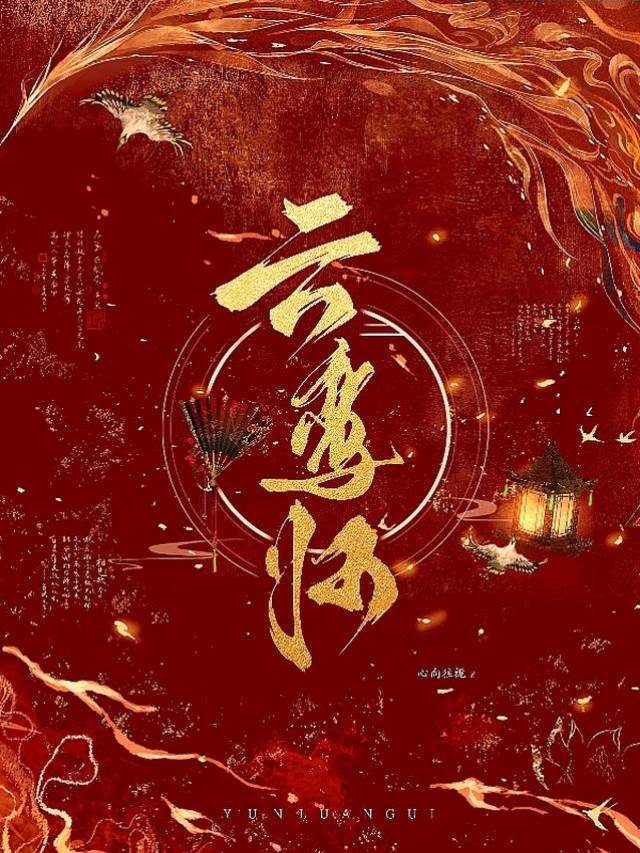
雲鸞歸
【黑蓮花美人郡主&陰鷙狠厲攝政王】[雙強+甜撩+雙潔+虐渣]知弦是南詔國三皇子身邊最鋒利的刀刃,為他除盡奪嫡路上的絆腳石,卻在他被立太子的那日,命喪黃泉。“知弦,要怪就怪你知道的太多了。”軒轅珩擦了擦匕首上的鮮血,漫不經心地冷笑著。——天公作美,她竟重生為北堯國清儀郡主薑雲曦,身份尊貴,才貌雙絕,更有父母兄長無微不至的關愛。隻是,她雖武功還在,但是外人看來卻隻是一個病弱美人,要想複仇,必須找一個位高權重的幫手。中秋盛宴,薑雲曦美眸輕抬,那位手段狠厲的攝政王殿下手握虎符,一人之下萬人之上,倒是不錯的人選。不近女色,陰鷙暴戾又如何?美人計一用,他照樣上鉤了。——某夜,傳言中清心寡欲的攝政王殿下悄然闖入薑雲曦閨閣,扣著她的腰肢將人抵在床間,溫熱的呼吸鋪灑開來。“你很怕我?”“是殿下太兇了。”薑雲曦醞釀好淚水,聲音嬌得緊。“哪兒兇了,嗯?”蕭瑾熠咬牙切齒地開口。他明明對她溫柔得要死!
42.5萬字8 2182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