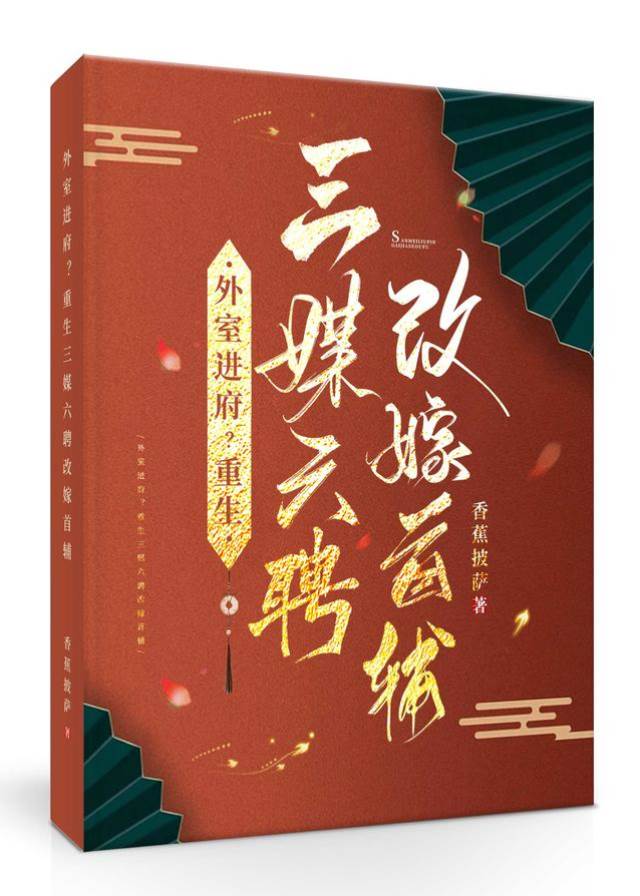《替嫁以后》 第46章
方寒霄回報完這事以后就忙別的去了,他完全平鋪直敘,沒告任何人的狀。但方老伯爺樂過以后,回頭想想,自己心里不是滋味起來,把方伯爺也來訓了一頓,沖他道:“管好你自家罷了!我先病著,沒神管你,如今你倒是說說,你在家閑了三四年了,如今還閑著,你到底是想什麼心思?”
方伯爺想什麼?自然是想與他失之臂的差,而且他沒閑著,搞幾回事了,時運不濟,都失敗了而已。因為里面牽連著算計方寒霄,他不好細說,只能含糊道:“隆昌侯可惡,進讒言搶了咱家的——”
“你可醒醒吧。”方老伯爺只聽他說一句,火氣就上來了,“你技不如人,敗了就敗了,一輩子摔那個坑里了不?沒那個窩兒,你打算從此就賦閑著了?總兵是朝廷要職,就沒隆昌侯告你那狀,換人也是正常的事,老子坐了十來年,那是托賴皇上信任,它不是真就姓了方!”
方伯爺有點不服,辯解道:“若無隆昌侯,本來傳出的信兒,皇上都打算照舊點了我的,霄哥兒在時,您常把他帶運河上去,不也是打著他接班的主意嗎?”
“老子那是盡人事,聽天命,能接自然最好,不能接,老子難道還能去跟皇上鬧事嗎?把本事歷練出來,自然有往別用上的時候!”方老伯爺肝火更盛,“你還有臉提霄兒,你看看霄兒二十出頭的年紀,都比你拿得起放得下,那麼一無所有地出去,一無所有地回來,天天也樂呵呵的,盡心盡力地伺候我,我好些了,他主又往外面找著朋友走去了,也沒悶在家里自怨自艾。看看他的心志,再看看你的!”
方伯爺讓噴得狼狽極了,心里埋怨了方老伯爺十七八遍“偏心”,礙著方老伯爺的暴脾氣,不敢說,只是悶著。
Advertisement
他不回,方老伯爺總算平了點氣,重又問他:“你到底怎麼打算的?我告訴你,朝廷里就那麼些位置,你再閑兩年,那些你從前看不上的差,你都沒得做了,人走茶涼,你懂嗎?”
方老伯爺訓他訓得兇,到底也還是想為兒子好,這一句把方伯爺點得悚然而驚——不錯,場這張網從不靜止,而是不斷在進化編織著,他離越久,屬于他的空間就會越小。
這不是他進行一些日常的際往來就可以維護住的,別人有在,有權在手,就有利益可以換,并因這種換而日漸,沒有的他只會越來越邊緣。
他低了頭:“爹,我知道了。”
這麼大的兒子,方老伯爺也不是很管得了,眼不見心不煩地一揮手:“那就去吧!”
**
且說到徐家那一邊。
前文有敘,徐大太太管的家吧,就那麼回事,看著似乎像樣,其實風。
這一方面是敗落下來的大戶人家在所難免之事,另一方面,也是因徐大老爺的置事外,一個家本該有一對主人,男主外主,徐大老爺常年撂挑子,事都堆在徐大太太上,徐大太太力有時不能兼顧,一些不留神的小地方,漸漸就松懈下來了。
所以,福全在平江伯府差點屁開花,但回到徐家,把銀票給惜月還真沒費多大事兒。
福全在徐家長了十二年,他跟姐姐石楠一樣,都沒混到什麼好差事,從前就是在外院傳傳話跑跑什麼的,因為他年紀小,更早兩年,還可以直接進到后院去,所以他差事雖次,對徐家里外是極悉的,人也都認識他。
瑩月給了他一些額外的跑費用,他就在路上買了些瓜子花生,走到徐家來,說是想從前的小伙伴們了,正好主子使他出來跑,他就順道過來看看。
Advertisement
跟他一跑過的小子們很羨慕他,放了他進去,找了個偏僻地方一坐著,磕著他的瓜子,吃著他的花生,紛紛夸他出息了,又問他平江伯府是不是很氣派。
福全滿胡吹大氣,吹了好一會兒,幾個小子都過夠了癮,福全才說了,吃了他的請,也得幫他個忙。
小子們問什麼忙。
福全嘿嘿笑著,求他們設法把二姑娘邊的英出來見一面,他那天走得急,都沒來得及跟英告別一下。
他說得曖昧,小子們瓜子都忘嗑了,齊齊瞪大了眼:“哎呦,你長齊了沒?就知道想人了?!”
福全推邊的小子一把:“胡說什麼,英姐姐從前照顧我,我聽說現在日子不好過,既然來了,就給帶包糖吃,也是我的一點心意。”
小子手:“那你給我,我替你捎進去。”
福全立刻搖頭:“不,我怕你路上吃!”
“切,誰吃你的,跟誰沒吃過糖似的。”
說是這麼說,這麼大的小子在外院混,于男事上一知半解,正是將開竅未開竅的時候,越是這個時候,越是樂意言說,要湊這個熱鬧,當下真有一個站出來:“等著,我替你去!”
福全忙道:“可避著點人,別太太知道。”
“用你說,太太知道,我也沒個好兒!”
這小子說著,嘿嘿地笑著跑了。
此時惜月跟云姨娘已經直接被勒令不許出清渠院一步了,但英梅兩個丫頭還能走一下,畢竟總得有人去廚房拿個飯什麼的,徐大太太再震怒惜月所為,不能把死在院里,那太聳人聽聞了。
于是一會兒功夫后,英還真被借故找了過來。
從前福全常替瑩月捎書進去——所以瑩月才敢把銀票托付給他,因他年紀雖小,在傳遞上還有經驗,這些別的小子們難免也有類似的勾當,很知道怎麼避人耳目,英無打采地走過來,一路上還真沒人著。
Advertisement
福全在一幫小子們炯炯的目下,從懷里把那包已經捂化了一點的花生糖掏出來,給英:“姐姐,勞你從前照顧我,這糖送給你吃。”
英今年十七了,比福全足足大了五歲,是沒往那些事上想,只是莫名其妙,跟福全其實不,就要推拒:“我不要——”
福全往手里塞了塞:“姐姐,別跟我客氣。”
一個紙團借著糖包的掩護,從他掌心里同時到了英掌心,然后他直接扣住了英還要推拒的手,把往旁邊拉了拉,“姐姐,我和你說句話。”
小子們一看福全這麼大膽,興地發出了怪聲來。
英本要生氣了,福全墊著腳尖,飛快地低聲說了一句:“我們大給二姑娘的。”聲音旋即恢復了正常,“姐姐,你別惱,往后我想見你也見不著了,你就給我個面子,收下罷。”
英眼皮抖了一下,哼了一聲,好像強忍怒氣不得不收似的,住了糖跟紙團,掙開了福全的手,然后轉就走了。
小子們還頭看呢:“這就走了?”
福全做戲做全套,也脖子,很是留的模樣:“唉。”
把小子們逗得大笑,都取笑他:“你真是人小心不小!”
鬧過一回,福全說還有事,要走了,囑咐小子們別把他這事往外說,小子應道:“知道,就你話多,我替你的人,我說了,我有個什麼好?”
福全才走了。
另一邊,英把糖跟紙團都揣到了懷里,順來路提心吊膽地回到了清渠院,一路上只怕徐大太太或者徐大太太的心腹著,幸而沒有。
午后時分,云姨娘和惜月都躺在炕上。
不是午歇,而是在養傷。
云姨娘挨了二十板子,惜月是姑娘,徐大太太還是要些面,沒直接打,但是勒令在院子當中跪了足足兩個時辰,暑天炎熱,惜月不但差點把膝蓋廢了,還中了暑,跪過那半天以后,爬都爬不起來了,徐大太太見這麼慘,才消了點怒氣,這兩天沒再來找的麻煩。
Advertisement
不過同時也沒有給請大夫,兩個人只能生熬著。
惜月對自所痛楚還能煎熬,但是連累了生母,心里過不去,兩天沒大說話了,云姨娘忍著痛,過一會兒,就安一句:“二丫頭,姨娘沒事,你也別懊悔,把這最難的時候熬過去,就好了,太太總得想法安置你。”
徐大太太再嚴苛,不是喪心病狂,妾室庶的命也是命,不管多招厭惡,不能直接下殺手,這麻煩遠大于隨便找個人家、眼不見為凈地把惜月嫁出去,所以只要能熬到徐大太太冷靜下來,想明白這個道理,惜月這一計就算了。
惜月有氣無力地應了一句:“姨娘,我知道。”
其實也不知道自己做的是對是錯,可是沒有別的路走,事已經做下,如今也只能咬著牙往前撐了。
這個時候,英匆匆回來了。
梅見模樣奇怪,說了一句:“你做什麼去了,怎麼做賊似的?”
英沒顧上說,了口氣,把糖包先掏出來,然后又出了那個紙團,走到炕邊,蹲下遞到惜月眼前:“二姑娘,三姑著人捎給姑娘的信。”
不識字,路上怕被人撞見,也沒敢把東西取出細看,見是個紙團,就以為是瑩月寫的信了。
現在在惜月疑問的眼神中幫著把紙團小心地一點點展平,不由愣了一下:“——三姑捎的什麼?這信怎麼怪怪的?”
銀票這樣的件,也沒有機會接過,看見了一般不認得。
但惜月讀過書,就是沒見過,也能認出來寫的是什麼。
在烈日底下跪昏倒了都沒落一滴淚,此刻忽然間眼前一片暈眩昏花,兩大顆淚珠直直落下來,打在銀票上。
英嚇了一跳:“怎麼了,三姑寫了什麼?可是責怪姑娘了?”
云姨娘聽見靜不對,也從那邊努力撐起子,把目投過來。
惜月咬著牙——怕一開口,排山倒海般的悔愧將倒,過了好一會兒,才艱難地梗著聲音道:“沒有。”
把眼睛也閉上了,又過一會,才又道:“我們剩的那二兩銀子呢?”
英遲疑地道:“在呢,姑娘要用了?可是上撐不住了?”
那二兩碎銀是們僅剩的銀錢,之前了罰后回來,云姨娘就想用了,大夫不好請進來,托人買點藥吃還是有門路的,只是們一下傷了兩個人,恐怕這點銀錢一下花空了,徐大太太那里再找事,們就只能等死了。
所以云姨娘的意思是給惜月買降暑及膝蓋的膏藥就行,但惜月覺得自己歇兩天緩過來就好了,云姨娘傷在皮上更重,要讓云姨娘用,母倆爭執不下,最終只能決定先熬兩天再說,誰熬不下去,誰再用。
惜月道:“不用省了,我們有錢了。去外院找個小子,把我和姨娘的傷說清楚,讓他去藥堂抓藥。”
覺得自己的傷已經沒有大礙,但清楚,不用藥,云姨娘也不會肯用的,所以一并說了。
云姨娘發著呆:“怎麼就有錢了?”
“三妹妹——”惜月間又梗了一下,“捎了一千兩的銀票來。”
……
云姨娘和梅英都驚呆了。
惜月沒顧上管們的緒,只是想哭又想笑。
這個傻丫頭,還是一樣的傻,一捎捎這麼大面額,怎麼用呢?!
猜你喜歡
-
完結1640 章

係統小農女:夫君,劫個色
身嬌體柔的白富美穿越成爹死母亡的小農女!不僅被無良奶奶賣給人沖喜,夫君還特麼是個傻子!她心底是拒絕的!幸好,隨身附帶個係統小婊砸,林若兮表示:姐好歹也是個有金手指的人!等等!這個係統好像有點不對勁!發布的任務還能撤回?隱藏任務必須接受?想要獲得高額積分,就得和夫君大人羞羞羞?!坑爹係統求收回啊!然並卵,老天太忙,管不了。從此林若兮就苦逼的過上了快速轉腦,忙於人前,時不時撩漢的幸(詭)福(異)生活!
281.9萬字8 69584 -
完結106 章

囚金枝
柔嘉身為妖妃帶進宮的便宜女兒,自小便知道太子不喜自己,因此處處小心,生怕觸了他的逆鱗。然而,待太子登基后,和親的消息仍是落到了她頭上。是夜,柔嘉走投無路,迫不得已跪到了太極殿:“愿皇兄垂憐……”年輕的天子抬起她下頜,似笑非笑:“那皇妹準備拿…
44.9萬字8 30844 -
完結694 章

神偷王妃
二十四世紀天才神偷——花顏,貪財好賭,喜美色,自戀毒舌,擅演戲,一著不慎,身穿異世,莫名其妙成為娃娃娘,還不知道孩子爹是誰……“睡了本殿下,今后你就是本殿下的人了。”“摸了本世子,你還想跑?”“親了本君,你敢不負責?”“顏兒乖,把兒子領回來…
125.5萬字8 382227 -
完結1013 章

嫡女錦途
前世虞玦被親生母親當做玩物送給權貴換取滿門榮耀,清白名聲儘失,卻最終落得被家族遺棄一杯毒酒含恨而終的下場。一朝重生回到十五歲那年,她一改之前隱忍懦弱,該屬於她的,她一寸不讓!
183.8萬字8 37476 -
完結711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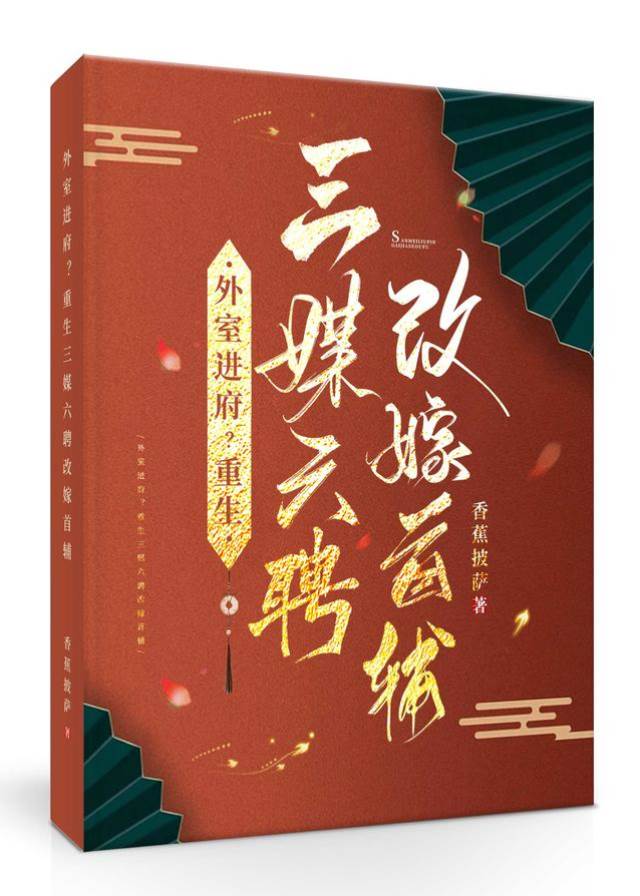
外室進府?重生三媒六聘改嫁首輔
【傳統古言 重生 虐渣 甜寵 雙潔】前世,蘇清妤成婚三年都未圓房。可表妹忽然牽著孩子站到她身前,她才知道那人不是不行,是跟她在一起的時候不行。 表妹剝下她的臉皮,頂替她成了侯府嫡女,沈家當家奶奶。 重生回到兩人議親那日,沈三爺的葬禮上,蘇清妤帶著人捉奸,當場退了婚事。 沈老夫人:清妤啊,慈恩大師說了,你嫁到沈家,能解了咱們兩家的禍事。 蘇清妤:嫁到沈家就行麼?那我嫁給沈三爺,生前守節,死後同葬。 京中都等著看蘇清妤的笑話,看她嫁給一個死人是個什麼下場。隻有蘇清妤偷著笑,嫁給死人多好,不用侍奉婆婆,也不用伺候夫君。 直到沈三爺忽然回京,把蘇清妤摁在角落,“聽說你愛慕我良久?” 蘇清妤縮了縮脖子,“現在退婚還來得及麼?” 沈三爺:“晚了。” 等著看沈三爺退婚另娶的眾人忽然驚奇的發現,這位內閣最年輕的首輔沈閣老,竟然懼內。 婚後,蘇清妤隻想跟夫君相敬如賓,做個合格的沈家三夫人。卻沒想到,沈三爺外冷內騷。 相敬如賓?不可能的,隻能日日耳廝鬢摩。
128.3萬字8.08 5353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