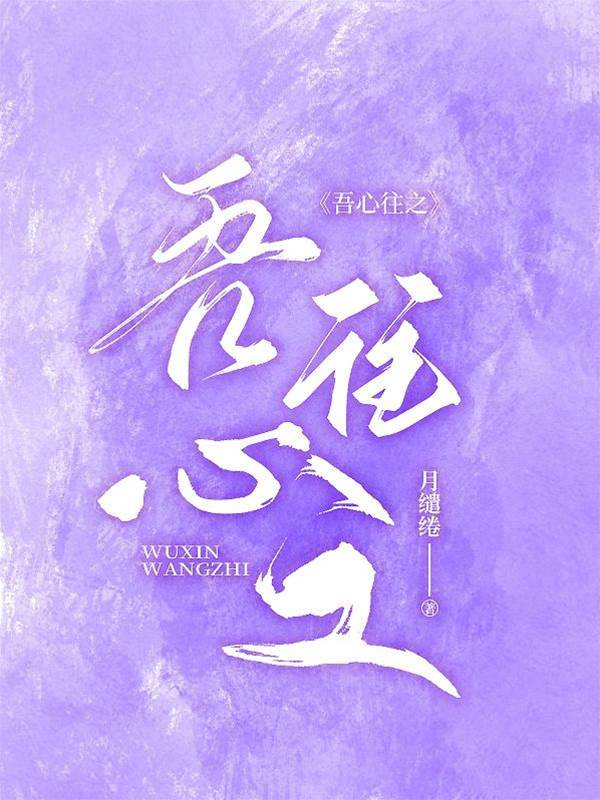《暗黑系暖婚》 第二卷 162:撩人的小妖精啊
風卷著米白的手帕,沒黑沉沉的夜里,月下,不遠的人,比夜更傾城。
162
因為時瑾在云城有個酒店項目,他和姜九笙在云城待了近一周,臨走前的一天,時瑾帶去了墓地。
時瑾牽著走到墓前:“你父親的墓地在溫家的墓園里。”
因為是贅,姜民昌的墓落在了溫家的宗墓里,未經準許,外人不得探。
時瑾說:“笙笙,這就是你母親的墓。”
一孤墳,坐落在墓地的最里面,周圍并沒有別的墓碑。碑文里,除了母親的名字,只有和時瑾,是兒,而時瑾,是立碑人。
時瑾說過,母親是孤兒,孑然一,并無其他的親友。
“你來過嗎?”姜九笙問時瑾。
沒有雜草環生,墓地一看便是常年有人打理。
時瑾說:“我每年都會過來。”
走近去,看黑青的墓碑,因著許久未下雨,落了灰塵,碑上有一張黑白的照片,照片上的人笑著,淺淺的梨渦,很溫婉。
俯,將照片上的灰塵拭去:“我媽媽長得很漂亮。”
時瑾看著,眉眼溫:“嗯,你很像。”
突然紅了眼,緩緩屈膝,跪在了墓碑前:“媽媽,我是笙笙。”
天微,沒有日頭,起了風,風吹飛絮,飄飄揚揚。
抬手,指腹拂過墓碑,是冰涼冰涼的溫度,喧囂的風聲里,只有的聲音,很輕很慢。
“我過得很好,也很健康。”頓了頓,繼續說,“時瑾就是醫生,醫特別好。”神平靜,安安靜靜的。
平時并不是很說話,這時,卻說了很多,不不慢,絮絮叨叨的。
說學了大提琴,遇上了一個很好的老師,還有幾個很喜歡的朋友,會調酒,會和志同道合的人喝著酒徹夜暢談。
Advertisement
說當了搖滾歌手,做著熱的事,有一群喜歡并且支持的人。
說和時瑾在一起了,沒有大起大落,平淡卻很幸福。
說很好,他把照看得很好,無病且無憂。
說了許多,都是報喜不報憂,都是開心的事,說著,會笑,眼里沒有任何霾,只是,微紅,有的淚。
時瑾跪在旁邊,沒有說什麼,只是一直看著,只是牽著的一只手。
說了許久,嗓音有些沙啞,干干的,時瑾扶起來,蹲下,輕輕了跪麻了的膝蓋。
低頭,能看見時瑾的頭發,被風吹得隨意,稍稍了,用手輕輕了,手心的,很。
時瑾抬頭,看。
“你為什麼要跪?”姜九笙問。
他想了想,口吻認真:“岳母大人在上。”
一句話,把逗笑了,紅紅的眼瞳里,有開的影。
時瑾站起來,用手背了眼瞼的,眉頭擰著,很心疼:“笙笙,以后不要哭了,我看了難。”
不哭啊,是流不流淚的子。
他突然湊到耳邊,小聲地又說了一句:“床上不算。”
“……”
他故意逗,心頭那點郁,也徹底煙消云散。
從墓地回酒店后,時瑾就一直陪著。
問是不是項目做完了。
時瑾說沒有,要留下陪。
也沒有說什麼,和他待在酒店,沒有出門,看了一個很無聊的電影,昏昏睡,不知道電影講了什麼,只知道時瑾在耳邊說了許多話,有工作的,也有見聞,甚至是醫學。
晚飯過后,時瑾剛洗漱完,沒見在房間,開了窗,站在臺的窗前。時瑾著頭發,走過去。
Advertisement
“笙笙,你在干什麼?”
姜九笙抬頭,只看了他一眼,就轉開了目,說:“沒干什麼啊。”
時瑾從后面抱住,下擱在肩上,蹭了蹭,用力嗅了嗅。
他說:“你煙了。”
“……”
姜九笙都覺得詫異:“還有煙味?”士煙,味道本就淡,又刻意漱了口,噴了一點香水。
時瑾扶著的腰,讓面對自己,低頭,在上嘬了一口:“有漱口水的味道。”
失策了,為了去煙味,用了一瓶漱口水。
姜九笙很快解釋:“我就了一。”
時瑾摟著的腰,稍稍用力,帶向懷里,表嚴肅:“笙笙,說實話。”
好吧,外科醫生的嗅覺很靈敏。
出兩個手指,鄭重其事地說:“兩。”
時瑾將窗戶關上,牽著坐在沙發上:“有心事?”
“嗯,想到了我母親。”
他拉著的手,沒有松開,指腹在掌心輕輕地挲,沒有說話。
“時瑾,你再和我說說的事好不好?”時瑾知道的比知道的多,的記憶斷斷續續,很模糊,沒有多關于父母的容。
“好。”
他把抱進懷里,一只手攬著,娓娓說了很多。
說母親是孤兒,了資助才念完了大學,的祖父母不喜歡母親孤兒的份,他父親姜民昌便和姜家老家斷了聯系,來了云城打拼,很多年不曾與姜家的人聯系,便是母親也只知姜家在偏遠的地區,沒有任何聯系。
姜民昌是警察,職位越做越高,與母親的分歧也越來越大,后來,姜民昌因為一個商業案子,認識了溫詩好的母親,那時候,溫詩好的親生父親還沒有去世。
姜九笙問時瑾:“我父親是第三者嗎?”
Advertisement
沒有太多緒起伏,不知為何,聽著這些并不尋常的過往,心里竟出奇得平靜,沒有震驚,也談不上失落。
對父親的印象很模糊,并不深刻。
“不清楚。”沒有摻雜任何私人緒,時瑾就事論事,“至,是溫詩好的生父逝世之后,他才與溫書華再婚的。”
時瑾還說,父母離異后,雖然跟著母親生活,不過,姜民昌依舊很疼,偶爾也會接去溫家玩,只是,在錦禹長大些后,姜民昌突然和疏遠了,也不太見面了,不知道什麼原因,連養費也斷了。
聽到這里,姜九笙蹙了眉。
怪不得雖然沒了記憶,更牽念的還是母親,或許,和父親的關系并不那麼好,至,不復當初。
說了許久,時瑾看了看時間:“好了,該睡覺了。”
姜九笙一點睡意都沒有,便說:“時瑾,我們喝點酒吧。”
時瑾猶豫了一下,還是依了:“好。”
他打了酒店前臺的電話,讓人送來了白蘭地,是金黃的酒,一看便是好酒。
姜九笙嗅了嗅,酒香濃郁,的癮便被勾出來了,讓時瑾給倒了一杯,先嘗了嘗鮮,不貪杯,放下杯子,說:“時瑾,要不要玩個游戲?”
時瑾給添了一小杯:“怎麼玩?”
起,去拿來了一對手環。
“莫冰說是贊助商送的,可以測心跳。”按了開關鍵,調好了設定后,給時瑾戴上了,笑了笑,“三十秒,心跳更快的喝。”
跟他玩心跳呢。
時瑾微微小抿了一口酒:“笙笙,你贏不了我的,在耶魯有專門的心理素質課,其中就有心率控制。”
外科醫生,需要臨危不,耶魯專門設了課,而他,是個中翹楚。
Advertisement
姜九笙興致很好:“不試試怎麼知道。”
時瑾也駁了,只說:“我酒量很好。”他似乎對什麼都有些抗力,不容易上癮,也不容易失去清醒。
也從沒見過他喝醉,想必酒量不是常人能及,便說:“那我一杯,你兩杯。”
時瑾也順著:“好。”
將杯子換了小杯,面前一個,他兩個,都斟滿了,然后稍微思忖了一下,提出了第一的規則:“對視二十秒。”
他淺笑著看,目不偏不倚。
二十秒,確切地說,十秒之后,手腕上的數字便了,跳得異常頻繁。
輸了。
時瑾心率很正常,不知是不是刻意,總之,徐徐上升,卻不迅猛。
第二,說要接吻。
時瑾便捧著的臉,吻了很久很久,非常火熱的法式深吻。
可還是輸了,想,耶魯的心理素質課,果然名不虛傳。
“還要繼續嗎?”時瑾了,飲了酒,沾了緒,嗓音異常低沉與。
姜九笙點頭,想了想,繼續:“一人說一句話。”
時瑾給斟了酒,沒有滿,大半杯:“笙笙,你要先說嗎?”
點頭,把酒杯添滿,然后抬頭看著他:“時瑾,我你。”
時瑾看了看手上的數據,跳得很快,他淡淡笑了,也不急,抬頭,不緩不慢地說:“笙笙,我想睡你,做到你下不了床。”
“……”
姜九笙怔了許久。
這是犯規。
十秒,的心跳表了,端起面前的白蘭地,一口飲盡:“下一,你先。”勝負突然起來了,今夜這酒,總得讓他家時醫生喝一些。
時瑾想了一會兒:“一人一個作,只能用手。”
“好。”
時瑾把從沙發那頭拉到邊來,扶的腰,用手撥開耳邊的發,指腹輕輕的耳垂,打著圈按挲,力道很小。
那是的敏地方,一,脖子都紅了。
有點,姜九笙往后了,看了看手環上的數字,然后思索了許久,抬頭,對時瑾莞爾笑了,眼里有玩味,帶了幾分壞。
時瑾一看便知道想做什麼了。
“笙笙,不可以。”
姜九笙揶揄:“為什麼不可以,上一就是你先耍渾的。”
說完,不等時瑾說什麼,坐在他上,用一只手按住他的肩,瞧著時瑾的眼,噙著笑,將另一只手沿著他敞口的浴袍鉆了進去。
他腹上的溫度不同于手,溫度是滾燙的,而指尖冰冰涼涼的,在他實的腹上流連,緩緩往下。
時瑾按住了的手,聲音不知何時啞了::“笙笙,不要再往下了,不然游戲繼續不了。”他把作的手拿出來,端起面前的酒,“我認輸。”
兩杯,他連著喝了。
姜九笙瞧了一眼時瑾腕上的手環,數據還在往上,嗯,終于找到碾他家時醫生的方法了。
等心跳平緩下來,繼續。
姜九笙給時瑾滿了酒,開了局:“取悅對方,”還坐在時瑾上,用手指點了點他的上,眼里都是笑意,有竹的樣子,“只能用這里,時醫生,你先還是我先?”
時瑾想也不想:“我。”
他怕若是先開始,他就不準停下來了。
時瑾把放在了沙發上,推起的服,低頭,落在口。
特別配合,抱著他的脖子,不躲不避,眼神卻大膽,他張,用牙齒,解了的扣子。
燈微暖,皮很白,沒有任何遮掩,映進時瑾眼里。
不過,失策了。
的心跳數據是上去了,只是時瑾的也了。
姜九笙低笑,抱著他的頭,讓他埋在前,低頭,在他耳邊問:“還需要我繼續嗎?”
時瑾嗓音嘶啞得一塌糊涂:“要。”
吻了他,不同以往,一個非常的吻,有曖昧的聲音,在他角拉出了長長的銀,末了,了他的:“時醫生,你又輸了。”
時瑾眼睛已經紅了,染了。
呼吸了,他平息了很久,將酒喝了,然后把抱進懷里,給整理好未扣好的,作慢條斯理地:“哪里學來的?”
“那次我陪謝看片,里面有演。”
人片,拍得特別骨,姜九笙領悟力又一向不錯,或多或懂了一些。
平時,床笫間,并不大膽。
時瑾說:“以后不準看了。”
姜九笙應了他。
“笙笙,”他嗓音低沉,微微有些,“要不要再玩大點?”
克制,卻又刻意蠱,回頭看他,他眉眼里有影沉浮,像一團見不到底的漩渦,能將人拉進去。
像是鬼迷心竅,著那雙眼失了神:“怎麼玩?”
時瑾將抱起來,指著臥室的落地窗:“在那里做一次,若我輸了,便把剩下的酒全喝了。”
玩得真大。
姜九笙嫣然一笑,像只人的貓兒:“好啊。”
猜你喜歡
-
完結1250 章
強勢纏愛:總裁,你好棒(林語嫣 冷爵梟)
結婚一年,老公寧可找小三也不願碰她。理由竟是報復她,誰讓她拒絕婚前性行為!盛怒之下,她花五百萬找了男公關,一夜纏綿,卻怎麼也甩不掉了!他日再見,男公關搖身一變成了她的頂頭上司…一邊是拿床照做要挾的總裁上司,一邊是滿心求復合的難纏前夫,還有每次碰到她一身狼狽的高富帥,究竟誰纔是她的此生良人……
264萬字8 56104 -
完結1446 章

借住後,小黏人精被傅二爺寵翻了
傅二爺朋友家的“小孩兒”要來家借住壹段時間,冷漠無情的傅二爺煩躁的吩咐傭人去處理。 壹天後,所謂的“小孩兒”看著客房中的寶寶公主床、安撫奶嘴、小豬佩奇貼畫和玩偶等陷入沈思。 傅二爺盯著面前這壹米六五、要啥有啥的“小孩兒”,也陷入了沈思。 幾年後,傅家幾個小豆丁壹起跟小朋友吹牛:我爸爸可愛我了呢,我爸爸還是個老光棍的時候,就給我准備好了寶寶床、安撫奶嘴、紙尿褲和奶酪棒呢! 小朋友們:妳們確定嗎?我們聽說的版本明明是妳爸拿妳媽當娃娃養哎。 小豆丁:裝x失敗……
261.7萬字8.18 126691 -
完結596 章

新婚夜植物人老公親哭我
她愛上霍時深的時候,霍時深說我們離婚吧。后來,顧南嬌死心了。霍時深卻說:“可不可以不離婚?”顧南嬌發現懷孕那天,他的白月光回來了。霍時深將離婚協議書擺在她面前說:“嬌嬌,我不能拋棄她。”再后來,顧南嬌死于湍急的河水中,連尸骨都撈不到。霍時深在婚禮上拋下白月光,在前妻的宅子里守了她七天七夜。傳聞霍時深瘋了。直到某一天,溫婉美麗的前妻拍了拍他的背,“嗨!霍總,好久不見。”
105.6萬字7.77 95117 -
完結12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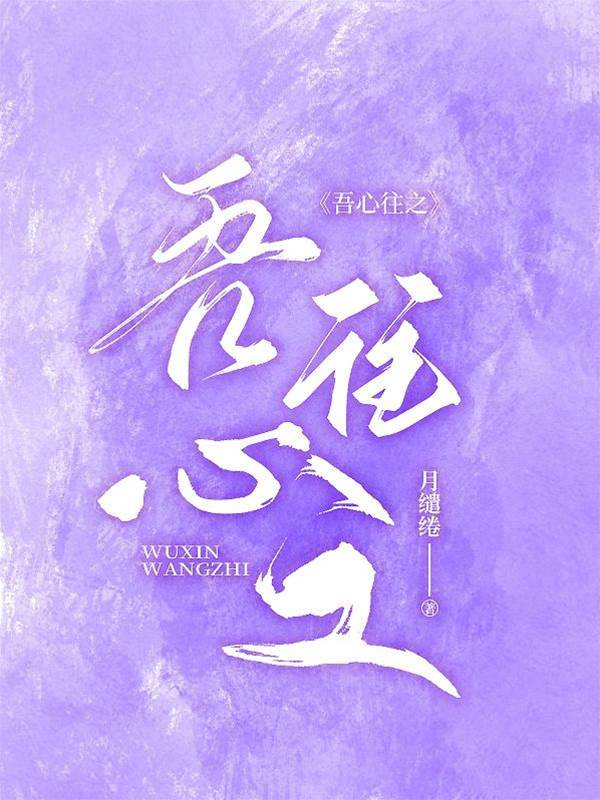
吾心往之
【久別重逢,破鏡重圓,嘴硬心軟,有甜有虐he 】【獨立敏感的高冷美人??死心塌地口是心非的男人】【廣告公司創意總監??京圈權貴、商界霸總】——————阮想再次見到周景維的時候,那一天剛好是燕城的初雪。她抱著朋友的孩子與他在電梯間不期而遇。周景維見她懷裏的混血女孩兒和旁邊的外國男人,一言不發。走出電梯關閉的那一刻,她聽見他對旁邊的人說,眼不見為淨。——————春節,倫敦。阮想抱著兒子阮叢安看中華姓氏展。兒子指著她身後懸掛的字問:媽媽,那是什麼字?阮想沉默後回答:周,周而複始的周。
22.3萬字8 3350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