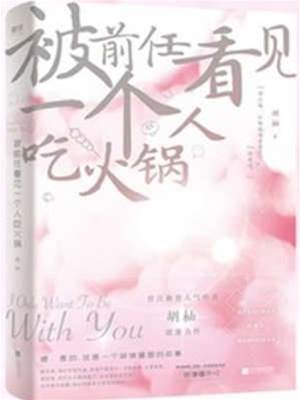《待我有罪時》 第129章
由于陳昭辭已被列為危險重犯,這一次,尤明許和好幾名警察都配了槍。和許夢山、殷逢一輛車,照例是許夢山開車,副駕空著。
“鄧耀的話,可信度大嗎?”許夢山問。
尤明許說:“大。”
許夢山冷哼一聲,說:“這次非要逮住那臭小子。”
尤明許從后視鏡里看了眼許夢山的臉,幾天各自不見,搭檔沒有什麼異樣,好像是從前的老樣子。還是那個心思深沉的許狐貍。好像他已把過去的一切都歸置整理好,好像什麼都沒發生過。
尤明許心頭有些意升起。
手被殷逢握住,許夢山應該看不到,尤明許就沒掙。看向他,小聲說:“剛才審鄧耀,有兩下子。”今天他的推理,比以前明顯更彩準確。
殷逢也覺這一回,腦子里思路比從前更快,更清晰。剛才審鄧耀時那些推理,很流暢就自己跳出來。他忽然想起陳楓說,腦子里淤有消散的跡象,心里咯噔一下。
握的手,乎乎地說:“那要獎勵。”
尤明許:“回家說。”
他又了一會兒的手,說:“你覺得剛才我們倆是不是配合得特別好?”
“嗯?”
“是不是更配了?”
尤明許當他還惦記著上回,不肯承認兩人相配的事,淡笑不答。
他卻自己蓋棺定論:“我們是夫唱婦隨。”
斜他一眼:“說反了。”
他說:“沒反,反正我是在上面的。”
饒是尤明許這樣的糙人,也反應了一下下,才明白他在說什麼,心頭一跳。這時他倒像個敢做敢當的男人了,手臂往椅背上一搭,輕聲說:“不服氣,又要咬我?”
這又是說昨天晚上咬在他背上的事。
Advertisement
尤明許靜默片刻,笑了,嗓音比他更懶散:“忘了和你說,傷好了。回頭就讓你看看,是誰在上頭。”
殷逢含笑盯著,尤明許竟被盯得心跳晃了幾下。心想,果然如此,再純潔的男人,上了床再下床,也會變混蛋。
岳楓山到了。
已是下午了,山里沒幾個小時就會天黑。一群刑警沿著山路,迅速散開搜索。只是這片山麓還大的,一眼去,樹林茫茫,那個傳說中的屬于市縣界的防空,又沒有在地圖上標注,只能一塊一塊搜過去。
尤明許帶著殷逢,鉆進樹林,披荊斬棘,快速推進。天有些,林子里線更弱,搜索線也在漸漸拉得更開。尤明許忽然就想起青年案時,也是在這樣的林子里,后來和殷逢第一次接吻。
而邊的男子,上次跟著,還一路嚷腳板痛,今天卻一聲不吭,和寸步不離。到了需要攀爬,還仗著長,先爬上去,拉——雖然尤明許本不需要,不過還是給了他點男人面子,讓他拉上去。
尤明許想,殷逢在車上說得沒錯,這麼多日子過去了,兩個人之間的默契,早非當初可比。那種可以把后背給對方的覺,兩個人幾乎一的覺,不知何時就存在了。
是在越過一片野山坡后,尤明許發現異樣的。前方有片垂直的石壁,石壁下方,草木叢生。當中竟有間小木屋,看著非常陳舊,里頭有很暗的一點,隔得遠樹木掩映,本發現不了。
尤明許拉著殷逢,往草叢里一躲,同時拿出對講機,低聲通報。最多十分鐘,其他人就能包抄過來。
“你呆這兒別。”尤明許說,“我去看看。”
他握著的手:“一起去。”
Advertisement
尤明許搖了搖頭。
殷逢明白,自己跟著,說不定不如一個人機靈活。他了一下的手:“小心,我看著你。”
尤明許一笑,伏低,潛行過去。
到了木屋外,門是虛掩著的,尤明許藏在暗草叢里,從門往里。赫然看到一個人坐在小桌旁,不是陳昭辭是誰?
數日不見,這人變得又瘦又黑,下一圈胡渣,服也是又臟又破,顯然在警方的追緝下,過得很糟糕。而他后的地上,約有個爐子,米油什麼的。
尤明許看著他就氣不打一來,想到樊佳最后還相信了他的自首,他卻把人送到了殺人魔手里。握手槍。
就在這時。
一直低著頭的陳昭辭,忽然抬眸,兩人的視線,就這麼突兀地對上了。
陳昭辭彎一笑。
尤明許只覺到整顆心都被寒氣包裹,心知有詐,絕不能讓他搶了先機。說時遲那時快,從草叢中一躍而出撞開門,拔槍瞄準:“不許!”
陳昭辭確實彎腰去拔靴子里的匕首了,但尤明許反應實在太快,他的手才到匕首,槍口已指向他的腦門,于是他整個人不了。
尤明許厲喝道:“舉起手來!”
他往后坐直,似笑非笑,慢慢舉起手。看著他這副死豬不怕開水燙的模樣,尤明許的眼睛都快噴出火來,迅速看了眼周圍。木屋很小,只有張折疊床,后面還有道簾子,里頭黑乎乎的,似乎就是那防空。
尤明許的目回到陳昭辭上,說:“你做的事,鄧耀已經一五一十代了。”
陳昭辭臉沉。
“站起來。”尤明許說,“雙手放腦后,出去。”
他慢慢站起。
尤明許看著他心里就恨,抬眼看看支援還沒出現,門外只有殷逢,一槍托就狠狠砸在他頭上。陳昭辭吃痛,撲倒在桌面上,鮮直流。尤明許還不解氣,提起他的腦袋重重砸了幾下,冷道:“你還是不是人?樊佳信了你,帶你去自首。現在人沒了!才24歲!你他嗎還是不是人!畜生!”
Advertisement
陳昭辭趴桌上,半天不,也不反抗掙扎。尤明許提槍又指著他,卻聽見他發出似哭似笑的聲音,“呵呵”幾聲后,他說:“我當時已經帶繞路了,但那只瘋狗還是追上來了。我不想殺。這麼多年我唯一不想殺的人,還是死在我手里。”
尤明許一怔,可心頭恨意依然難消,冷冷說:“走吧,法律制裁等著你。”
他靜了一會兒,說:“說起來你可能不信,這幾天我一直在想,如果我早點遇到,早點對我說那些話,也許……我就不會殺人了。”
尤明許心里卻越發難。
可是沒有如果。
有罪的人,沒有如果。
因罪而死的人們,也沒有如果。
這時陳昭辭站直了,兀自笑了:“可是,我已經被審判過了,你帶不走我,我已經獲得新生。”
尤明許愣了愣,心想他莫不是已經神失常了。
就在這時。
陳昭辭突然轉,朝的槍口撞上來。尤明許一驚,連忙避開,另一只手抓向他的領。
后簾子輕響,有人沖了出來。尤明許整個后背都涼了,連忙轉。
來不及了。
什麼重重打在的頭上,撞在桌上,又跌落在地。陳昭辭手持匕首后退兩步,卻有另一個槍口,指著的額頭。
來人一黑,非常高大。黑沖鋒,黑長,短靴,戴了頂鴨舌帽,得很低,只出個下。
一種非常強烈的、似曾相識的覺,涌上心頭。尤明許的,就像被一層寒冰,慢慢覆蓋住。他抬起了頭。
那是一雙非常深刻的眼。比起幾個月前,他的臉瘦了很多。可只是一眼,就讓那些早已走遠的記憶,涌上尤明許心頭。
無邊的荒野,沉的雨夜,男人隔著車窗著;他和坐在帳篷邊,一起抬頭著星空;他點了支煙,在一段枯木坐下,說:我決定為連環殺手,殺死五個,或者更多。
顧天也著,目不悲不喜。
半陣,尤明許笑了。
他也笑了。
陳昭辭看到這一幕,有些迷。但他很清楚目前的困境,這警是個大麻煩。眼見被顧天打倒,陳昭辭悄悄持刀,想要近,就聽到顧天開了口:“站住。你是個什麼東西,也敢?”
尤明許回頭看了一眼。
陳昭辭一驚,心里又恨又怒,但接到顧天冰冷的目,到底慢慢放下匕首,退到一旁。
尤明許的手就握在槍上。如果現在面對的是別人,有信心后發制人賭一把。但是顧天,不能妄。
顧天盯著的眼睛,仿佛眼里只看見了,輕聲說:“清凈了。明許,我們終于可以好好說話了。”
猜你喜歡
-
完結1795 章
婚內燃情:三叔,別這樣!
“我會負責。”新婚夜老公的叔叔在她耳畔邪惡道。人前他是讓人不寒而栗的鐵血商業惡魔,人後卻是寵妻狂。他對她予所予求,為她鋪路碎渣,讓她任意妄為,一言不合就要將她寵上天。隻因多看了那件衣服一眼,他就直接壟斷了整個商場在她的名下。他說:“隻要你要,傾我所有!”
166.3萬字8.08 304871 -
完結60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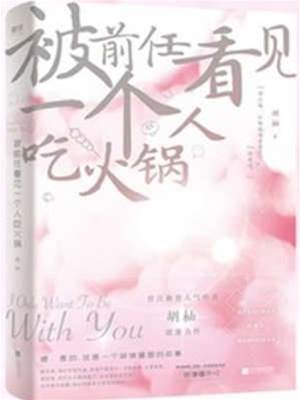
被前任看見一個人吃火鍋
【葉陽版】 葉陽想象過與前任偶遇的戲碼。 在咖啡館,在電影院,在書店。 在一切文藝的像電影情節的地方。 她優雅大方地恭維他又帥了, 然后在擦肩時慶幸, 這人怎麼如此油膩,幸好當年分了。 可生活總是不盡如人意。 他們真正遇到,是在嘈雜的火鍋店。 她油頭素面,獨自一人在吃火鍋。 而EX衣冠楚楚,紳士又得體,還帶著纖細裊娜的現任。 她想,慶幸的應該是前任。 【張虔版】 張虔當年屬于被分手,他記得前一天是他生日。 他開車送女友回學校,給她解安全帶時,女友過來親他,還在他耳邊說:“寶貝兒,生日快樂。” 那是她第一次那麼叫他。 在此之前,她只肯叫他張虔。 可第二天,她就跟他分手了。 莫名其妙到讓人生氣。 他是討厭誤會和狗血的。 無論是什麼原因,都讓她說清楚。 可她只說好沒意思。 他尊嚴掃地,甩門而去。 #那時候,他們年輕氣盛。把尊嚴看得比一切重要,比愛重要。那時候,他們以為散就散了,總有新的愛到來。# #閱讀指南:①生活流,慢熱,劇情淡。②微博:@胡柚HuYou ③更新時間:早八點
19.1萬字8 7230 -
連載601 章

這主播真狗,掙夠200就下播
189.5萬字8.18 8244 -
完結146 章

那月光和你
大學畢業,顧揚進了一家購物中心當實習生。 三年后,他作為公司管理層,和總裁陸江寒一起出席新店發布會。 一切看起來都是順風順水,風波卻悄然而至。 高層公寓里,陸江寒一點點裁開被膠帶纏住的硬皮筆記本,輕輕放回顧揚手里。 那是被封存的夢想,也是綺麗華美的未來。 再后來。 “陸總,您能客觀評價一下顧先生嗎?” “對不起,他是我愛人,我客觀不了。”
41.4萬字8 6805 -
完結122 章

月光渡我
時衾二十歲那年跟了傅晏辭。 離開那天。 傅晏辭懶散靠門,涼涼輕笑:“我的衿衿急着要長大。” 時衾斂下眸子:“她不可能永遠是你的小女孩。” 夜深。 時衾咬着牙不肯。 傅晏辭發了狠,磨得人難捱,終於得償所願換到一句破碎的細語—— “衿衿永遠是你的小女孩。”
18萬字8 1220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