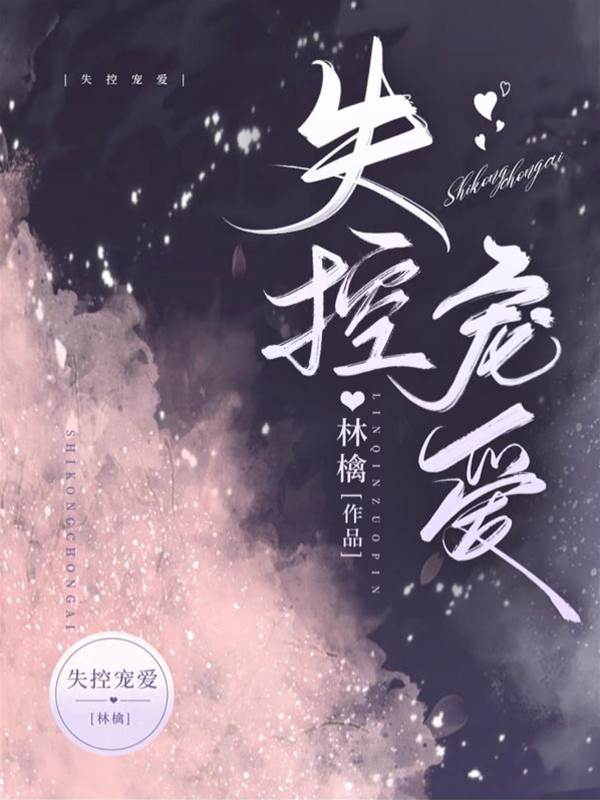《棄妃不承歡:腹黑國師別亂撩》 第2025章 變本加厲,得寸進尺
纖細的脊背,白細膩,在微下散發出羊脂玉般的人澤。
一朵胭脂紅的曼珠沙華,肆意盛開在蝴蝶骨間。
妖嬈,曖昧,
同略顯青的子毫不匹配。
年帶著薄繭的指尖,輕上那朵花,“公主怕是不知道,你背上被我紋了朵花兒。”
“紋了花又如何?!你再這般放肆,本宮就喊人了!”
“我花銀子買下公主,又在公主上紋了記號,公主可不就是我的人了?”年俯,慢條斯理地親吻過的脖頸與蝴蝶骨,“若再我看見公主與旁的男人親熱,我定要把公主全都紋上花兒,那男人看看,你究竟是誰的所有……”
溫溫的語調,卻好似一條獵的毒蛇。
令人心驚。
鰩鰩渾戰栗,因為驚恐,息得十分厲害。
就在不顧一切準備喊人時,年手點了的啞。
他把一不掛的打橫抱起,麵無表地朝屏風外的繡床走去。
一重重緞質繡花床帳被放了下來。
頃刻後,伴著的一聲嗚咽,那繡床劇烈晃起來。
魏化雨低著,在黑暗中摘下閻羅麵,俯親吻鰩鰩的。
所有的委屈都被堵在裡,晶瑩的眼淚滾落眼角,沁枕中,逐漸消弭無蹤。
弧度纖細的**,被架上男人的肩膀。
腳腕上的小金鈴,隨著男人的侵.犯,而發出急促的鈴音。
鰩鰩疼得厲害,於那無邊黑暗中揮雙手妄圖拒絕,可得到的隻是男人變本加厲、得寸進尺的攻城.掠地。
魏化雨單手捉住鰩鰩的雙手,把它們狠狠摁在頭頂上方,掐著的麵頰,一字一頓:“魏文鰩,你是我的所有!紋上曼珠沙華,你就是我的!”
發狠般的語調,昭示著此刻的魏化雨,究竟是何等盛怒。
Advertisement
——鰩鰩,你在鎬京城長大,這裡有你所有的朋友與親人。與我親,乃是你最正確的選擇。
——傻姑娘,我亦不是什麼乾凈玩意兒,何必同我提什麼清白不清白的?我在乎的,不過是你這個人罷了。
他未去參加今夜的宮宴。
隻是在夜宴結束時,瞧見天不大好,怕今夜落雪,於是撐了傘打算去接鰩鰩。
卻在重華閣外,看見花思慕替鰩鰩披上鬥篷的那一幕。
他尾隨了他們一路,也聽了一路花思慕的花言巧語。
那個男人利用鰩鰩對他的疚,變著法兒地哄與他親,還說鰩鰩所謂的不喜歡他,不過是親前的正常心理。
呸,簡直是一派胡言!
年出神的這一剎那,被鰩鰩逮到機會,猛然掙開他的手!
到底是有著大魏統的皇,鰩鰩力氣極大,不顧一切地爪去撓魏化雨的臉。
知曉打不過這個男人。
然而那並沒有關係,在他臉上留道印子,鬼市那邊找人,就會更方便不是?
可魏化雨反應極快。
他抬手擋住臉,鰩鰩的指甲恰恰從他的手臂劃過!
長長的撓傷自小臂一直延到手背,迸開,甚是駭人。
魏化雨低“嘶”了聲,下,猛然一個近。
鰩鰩忍不住地發出一聲婉轉.,很快被男人掐住下頜:“你是屬貓的嗎?怎的還會撓人?!”
小姑娘說不了話,隻一個勁兒在黑暗中瞪他。
“嗬。”魏化雨低笑一聲,毫不在意手臂上的撓傷,隻俯霸道含住的瓣,帶著一道墮慾海。
雕窗外的落雪紛紛揚揚。
黑暗的寢殿裡,床帳低垂,約從裡麵傳出不間斷的啪啪水聲。
伴著咿咿呀呀的難耐.。
明明該是痛苦的,可在魏化雨極致嫻的技下,那嗓音生生逐漸化作纏綿悱惻、婉轉。
Advertisement
於無邊黑暗的床帳中,勾人至極。
翌日。
雪過天晴。
宮中校場上,大清早就熱鬧非凡。
乃是因為今日,大周公主要與安南皇子呼莫邪比賽馬球的緣故。
眾多世家子弟、姑娘都已在校場四周挑了位置坐下,個個兒麵帶興,隻等著觀看等會兒的馬球比賽。
雖然往日也常常有這種比賽,可今日這場比賽的賭注非同小可,自然更值得觀看。
校場附近有專供人更的樓閣。
鰩鰩獨自把自己關在一間寢屋,單手撐著落地青銅鏡,恨了昨晚那個戴閻羅麵的傢夥。
那人不知發什麼瘋,生生索要了一夜!
早上起來,雙疼痛得厲害,待會兒要怎麼上馬?!
正懊惱暗恨時,外麵傳來敲門聲。
佑姬的聲音自門外傳來:“鰩鰩,你換好裳不曾?”
鰩鰩向雕門,咬了咬瓣,聲音悶悶的:“好了,我這就出來。”
在明德書院讀書時,書院中常常會辦這種馬球比賽,不過大抵都是年們參加。
可慣是個爭強好勝的,因此特意選拔組織了一批姑娘,也玩起了馬球,勢要與那幫年爭個雌雄。
離開更樓,與其他姑娘一同往馬廄牽馬。
隊伍裡的姑娘,除了與佑姬外,一共還有五人。
其中之一便是程。
雖然鰩鰩與不和,但程不撒裝弱時,馬上功夫還是相當不錯的,因此才願意讓程進的隊伍。
而此時,鰩鰩牽出自己的棗紅馬,偏頭向程:“你我鬥了五年,雖是仇人,卻比普通朋友還要瞭解彼此。程,你今兒幫我贏下這場比賽,勿要放水,可好?總歸,你我在一塊兒也算熱鬧,我若遠嫁安南,你心裡果真好嗎?此外,等呼莫邪這事兒了了,我自會與思慕哥哥退親,你放心就是。”
Advertisement
程也牽出自己的馬,笑道:“公主說的什麼話,我雖與你不曾同姐妹過,可到底也相識多年,自然不忍看著你遠嫁到那種蠻荒地方。公主放心就是。”
們皆做同樣的打扮,用紅緞帶束起馬尾,穿正紅箭袖勁裝,腳踩一雙黑底牛皮靴,腳牢牢紮在皮靴裡,看起來利落瀟灑非常。
鰩鰩翻上馬,朝程拱手道了聲“多謝”,便一夾馬肚,朝校場疾馳而去。
程扶著韁繩上馬,目送的背影遠去,眼底不覺浮起一重嫉妒。
棄妃不承歡:腹黑國師別
猜你喜歡
-
完結9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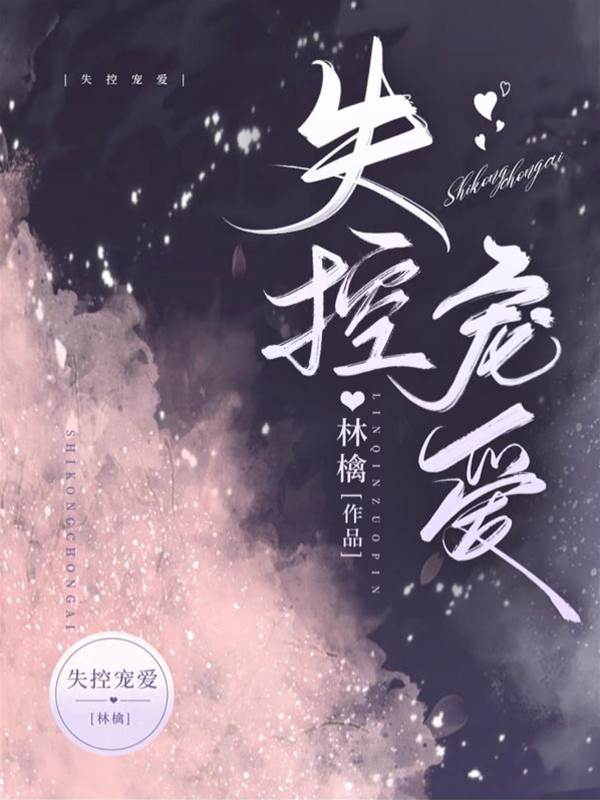
寵愛失控
【爆甜 雙潔 青梅竹馬養成係 男主暗戀】【腹黑爹係x直球甜心】對比親哥許初衍,許悄絕大部分的時間,都是被養在鄰家哥哥陸寂淵的身邊。許悄一直認為自己長大後一定會像長輩們說的那樣嫁給陸寂淵。直到有一天,室友疑雲滿腹的湊到她耳邊:“哪有人會在喜歡的人麵前活得跟個親爹似的啊?”“你們的認識這麼久了他都不告白...而且我昨天還看到他和一個女生在操場...”室友善意提醒:“悄悄,你別被他騙了。”-許悄覺得室友說的有道理。於是想抓住早戀的尾巴,來一場轟轟烈烈的戀愛。就在許悄跟人約會的第一天,陸寂淵黑著一張臉找上門。被人掐著腰抵在牆上,許悄被親的喘不過氣,最後隻能無力的趴男人在身前。室內昏暗,陸寂淵的指腹摩挲著她的唇瓣,聲音低沉又危險。“小乖真是長大了啊。”連膽子都跟著大了起來。
19萬字8 12383 -
完結100 章

餘溫撩人
謝政嶼,你知道的我本來就是一個報複心極強的人。溫溫,你告訴他,你不喜歡弟弟,隻喜歡哥哥。溫溫,你的目的達到了。我的?嗯,也是我的。謝政嶼,我從來沒有想過要跟你在一起。我隻是想要阻止你與吳清婉的婚事,其餘的,別無所求。但是溫溫,從你行動那天起就注定是要招惹我的。喬溫被母親好友的兒子接走照顧,無意間知道了害死母親的同父異母的妹妹是謝政嶼的未婚妻,暗下決心接近謝政嶼破壞婚事。但最後兩人都動了情,被人惡意破壞,又在身份的裹挾中兩人不停掙紮~
26.2萬字8 2823 -
完結328 章

婚後童話
周萱第一次見樑津。橘黃燈光下,男人側顏冷淡,輪廓深邃。嫋嫋煙霧中,眉間神色清冷,帶着拒人於千里之外的疏離。 周萱耳邊自動響起姐姐叮囑過的話。“樑津是你姐夫,你離他遠點。” 樑、周兩家是有聯姻關係的。只不過,既定和樑津聯姻的對象,是她姐姐。 但是那晚,卻是她和樑津,陰差陽錯地有了聯繫。 醉酒醒來的第二天,她落荒而逃。而男人對着她的父母,擺出難得的誠懇態度:“請將周萱嫁給我。” 一樁豪門聯姻就這麼成了。沒人看好這樁婚姻。 樑津手腕強硬、執掌樑家,外人看他清冷禁慾,不知什麼樣的女孩才能入他的眼。而周萱大學畢業,一團孩子氣,畢生夢想是去動物園給河馬刷牙,是個腦回路和常人迥異的笨蛋美人。 所有人都覺得,他們遲早會離婚。 - 婚後,樑公館。 窗外,鳳尾竹的影子投在粉牆上,月影瀟瀟。 男人身體清貴散漫,膝頭坐着的女孩,柔嫩小手拽着他忍冬紋的領帶,明媚的小臉因爲生氣而多了幾分瀲灩,脆聲指責男人。 “你把我娶回來,不就是讓我早點給你生孩子。” 她生起氣來不管不顧,將他抵住她窈窕腰肢的手掌拿起,牙齒咬在他虎口上。 男人輕“嘶”一聲,倒是對她咬他習以爲常,只是手掌放在她粉頸上,粗糲拇指頂着她下頜線,強迫她將臉擡起,兩人對視。他素來無情無慾的鳳眸,因她起了別樣的漣漪。 他嗓音低啞,氣息拂耳。 “別說生孩子,光養你一個都夠我受了。”
50.6萬字8 7692 -
完結492 章

食髓
(雙潔,1V1,男歡女愛,愛如食髓) 靳南城是圈子裏的浪蕩貴公子。 所有人都以爲,這個世界上沒有女人可以讓他動心。 直到有一天,有人看到—— 酒吧衛生間內, 靳南城滿眼欲紅的把一個女人圈在門後,吻得虔誠又瘋狂。
84.7萬字8 2681 -
完結286 章

宮女在逃
殊麗白日裏是尚衣監的女官,夜晚是替帝王守夜的宮女。 無疑,殊麗是受寵的。 可她心裏清楚,自己不過是從不敢多瞧主子一眼的奴婢罷了。 新帝陳述白喜歡安靜,殊麗守夜時幾乎不會發出任何動靜。 兩人井水不犯河水,直到殊麗在宮裏最好的姐妹被權宦強行帶走,纔不得已求上了九五至尊。 帳簾拂動的龍榻上,新帝手持書卷,不置一詞。 殊麗跪在地上,苦苦哀求,可就是撼動不了帝王冷硬的心。她知自己貌美,一咬牙,緩緩站了起來:“奴婢伺候陛下…安寢。” 灰綠色宮衫下,姣好的身段映入帝王淺棕色的瞳眸。 * 新帝陳述白清心寡慾,唯一破例的那次就是對殊麗。 太后得知兒子開竅後,急着爲他充盈後宮。身爲帝王,三宮六院是尋常,陳述白沒有過多在意,只是拍了拍殊麗的腰窩:“認真些,當心朕罰你。” 殊麗知道皇家薄情,沒想蹚這趟渾水,也爲日後謀劃好了出路。可就在選秀的前夕,她發現自己懷了身孕。 這是壞了宮規的大忌。 * 近些日子,宮人們發現,帝王心情不佳,似乎與出逃的宮女有關。
43.2萬字8 25341 -
完結596 章

真千金回眸一笑,京圈大佬齊折腰
被老公算計離婚,又被父母趕出家門,姜柚才知,自己并非姜家親生,而是個假千金, 眾人都嘲諷她出身低賤,親生父母是山溝溝里的窮鬼,五個哥哥都偷渡在國外打黑工, 姜柚無所謂,反正她身價過億~ 她大大咧咧去認親,誰知……親生父母竟是海外巨鱷!五個哥哥皆是頂級大佬! 一夕之間,她成為全球頂級白富美! 霸總大哥:以后整個安家,都由小妹來繼承! 石油大亨二哥:小妹,哥所有的礦山全歸你! 三哥、四哥、五哥:百套房產,古玩字畫,豪車珠寶,哪怕是天上的星星,只要小妹想要,統統都送給小妹! 姜柚擺手,謙虛:不用客氣的,哥,其實這些我全都有。 前夫悔了,跪求回頭草, 京圈大佬手一揮:哪來的舔狗,敢舔我的未婚妻?打斷腿,趕走!
104.8萬字7.75 60453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