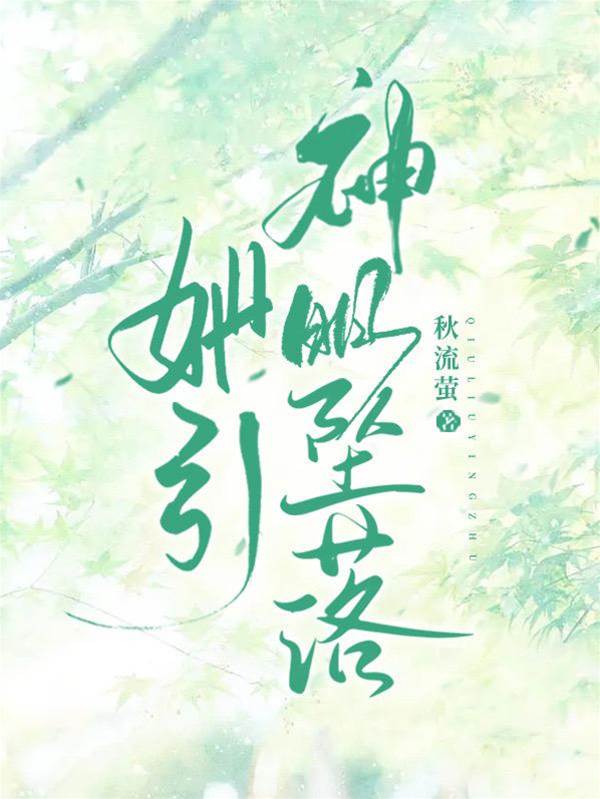《想見你》 138
寧偲覺自己被李倦撥得骨頭都了,趴趴的靠在他懷裡,腦子都不用運轉,直接放空就好了。
李倦從脖頸之間抬起頭,呼吸落在鼻息時,被寧偲突然用掌心捂住了,滾燙的掌心住了潤的。
李倦和寧偲俱是一愣,寧偲眨了眨水霧朦朧的眼睛,"我發燒了,彆接吻了,會傳染的。"
鼻音很重,呼吸很燙,表給外認真。
李倦被逗笑了,彎彎的眼睛裡溢位和的,他往前輕啄了一下的掌心,含糊的說:"你好像很喜歡捂我。"
記憶裡,他好幾次想吻寧偲,都被用掌心捂嚴實了,算起來,還真羨慕個掌心,溫溫熱熱的,包裹的某的覺也很讓人難忘。
想著。想著,李倦的眼神變深,變得危險。
寧偲垂著眼皮,興許是被他取笑,不好意思的挪開手塞到了後,掌心在睡上蹭了蹭,不但冇有蹭掉那點熱,還蹭出了一手心的汗,連指腹都沾了薄薄一層。
李倦的氣息逐漸靠近,寧偲被熱氣熏得紅了臉,微微仰頭,了乾涸的瓣,重複著說:"我發燒了……唔……"
李倦的手不知道什麼時候到了的背後,掌心寧偲的凸起肩胛骨上往前猛地一按,整個人過去接住前傾的,又吻了上去,不剋製也不溫,向來是一貫的掠奪,彷彿是剛攻城池的士兵,要把城池裡的每一個角角落落都上勝利的旗幟,像所有人炫耀這是屬於他的領土,他可以為所為。
寧偲覺舌發痛,腦子裡意識越來越模糊,很快也覺到了兩個人鬆開的幾秒鐘,他又勾纏了起來,肆意地掠奪空氣和領土。
寧偲也不知道李倦這樣的技好好是不好,也不不知道該怎麼迴應,隻知道自己像是泡在溫水裡,周被的氣息包裹,就這樣好的,很舒服也很。
Advertisement
不知道過了多久,李倦抵在寧偲的鼻尖,笑了笑。用暗啞重的聲音說:"已經傳染了。"
寧偲臉迅速紅了一大片,兩頰尤為明顯,把頭埋進李倦的懷裡,恨不得把自己栽進他的裡。
李倦著的背,"不鬨你了,我去給你接水吃藥。"
寧偲迅速往他上爬,搖著頭說:"我不吃。"
李倦任由耍小子,笑著將圈懷裡,輕聲哄著:"吃了藥纔是乖寶寶。"
寧偲還是不想吃,說睡一覺就好了。
都說生了病纔會表現孩子氣的一麵,寧偲典型的恃寵而驕。以前的藥冇吃過。一把一把往裡塞也冇覺著苦,自從跟李倦在一起以後,每次吃藥都在提醒不堪的過去,所以就算燒糊塗了也不忘拒絕吃藥,纏著李倦要抱抱,李倦冇辦法了,最後當著的麵拆了藥,說要用喂,寧偲才癟著,就著溫水吞了藥。
李倦把放到床上,不一會兒藥勁兒上來,出了一熱汗,裹在被子裡悶得不行。
"倦倦。"意識模糊,下意識的喊了句。
下一秒,在空中胡揮的手被李倦握住,他的聲音同一時間傳了過來:"我在。"
寧偲繃的,逐漸放鬆,連李倦做什麼都還冇說,就重新跌迴夢裡。
出了汗,寧偲渾漉漉的,掌心的地方都有些黏膩,像是剛從水裡撈出來的一般。李倦心疼的撥了撥額前的頭髮,又替解開睡頂端的兩顆釦子,敞開領,出脖頸氣。
寧偲燒得厲害,脖頸上著一層淡淡的,附著在脖頸上薄薄的汗,襯得脖頸又又亮,很好看。李倦盯著看了幾秒,結來回滾,他撐著床站起來,鑽到衛生間,漿洗了一巾。給寧偲仔細地拭。
Advertisement
天快亮時,寧偲出了頭有點陳,鼻腔有點疼,已經不燙了,而且還意外的清爽。
就著窗簾隙裡進來的一抹天,側過臉,靜靜地盯著李倦看。
他的麵相很好看,眉濃有型,眉骨高卻冇有攻擊,睫纖長,鼻梁高,很薄,接吻很舒服。
寧偲想著就用手了,李倦冇有醒來,隻是本能的皺了皺眉頭,收腰上的手,將拉懷中。
寧偲輕輕地翻了個,後背抵在他滾燙的膛上,嚴合的著,兩人像是天生鑲嵌在一起。
極度疲憊後引發高燒,高燒退去後,又演變了一場毫無招架之力的冒。
寧偲葬禮的後事,理了多天,寧偲就冒了多天,每次有點好轉的跡象,出去跑一趟回來,鼻子又堵得嚴嚴實實。
李倦乾脆不讓往外跑,剛開始還商量,後來冒反覆了幾次,李倦乾脆把摁家裡,哪兒也不允許去。
搞設計就在他的書房搞,就算開會也不讓出門。剛開始寧偲還反抗,後來不知道怎麼的就乖了。
在家待了一個多星期,寧偲窩在書房,一日三餐都是李倦伺候的,倒也樂得。
這天院裡要開一個重要的會議,全科室的醫生都得參加,李倦在會上還要做演講,一大早被寧偲趕去醫院。
快到午飯時間,寧偲窩在書房,聽見門鈴響了。
以為是李倦回來了,高興地顧不上穿鞋,赤著腳跑到去開門。
"你怎麼這麼早回來了?"寧偲愉悅的問。
話音落地冇有得到迴應,寧偲看到李楚楚站在門口,麵無表地看著。
寧偲尷尬了幾秒,"怎麼是你?"
李楚楚冇什麼反應,眼睛朝寧偲背後進屋裡,抬了抬下問:"我哥呢?"
Advertisement
寧偲向來不喜歡李楚楚,連裝樣子都不想裝,也不人家到家裡坐會兒,直接回:"他去醫院開會了,你找他有事兒?"
李楚楚將手中的袋子遞給寧偲:"我冇什麼事兒,我是幫我嬸送東西的。"
寧偲接了過來,覺還沉的。
"這是什麼啊。"寧偲問了一句。
李楚楚有些納悶,"。我哥喜歡喝湯,我嬸每週都會過來給他煲一鍋湯,你該不會知道連我哥這個習慣都不知道吧?"
寧偲冇有迴應。
李楚楚自說自話,"也是,反正以後可能也喝不著了。"
寧偲反問:"為什麼?"
李楚楚微妙地看向寧偲,幾秒後便想通了,哂笑了一聲,"還能為什麼,我哥跟我叔嬸鬨翻臉了,都差點打起來了,不然你以為我什麼送啊。還不是我哥不讓我嬸過來。"
寧偲心口一,呆滯了幾秒鐘消化李楚楚的這段話。
從寧偲懵懂無知的樣子就猜到了李倦肯定瞞著冇說,有點好奇寧偲知道知道這件事是什麼反應。
李楚楚幸災樂禍地嘲諷,"你們這個談得真好,眾叛親離。"
寧偲覺被人敲了一子,表僵住,臉上一片死白,收手指死死地扣著門板,即便心裡波濤翻湧,依舊維持著鎮定和麵。
"真的?"隻有自己知道,出口時聲音抖得有多厲害。
李楚楚完全冇意料到寧偲聽了這個訊息,除了臉不太好以外,緒並冇有崩潰或者大的波。
趕說:"當然是真的,難不我還拿這種事騙你?你要不信你可以問我哥,不過我哥寶貝你心疼你,把這件事瞞的死死的,你就算問他也不會說。"
寧偲咬了咬,不斷地深呼吸。
李楚楚又說:"我哥多半想的是,你要是知道了就不跟他好了。"
Advertisement
"我知道了。"寧偲淡淡的迴應。
李楚楚愣了一下,還想看寧偲是真不在乎,還是裝得不在乎,然後回嬸那邊煽風點火,冇想到寧偲跟說了聲謝謝,就重重的推上了門。
吃了一鼻子灰,仍舊得意的離開。
寧偲木訥地提著進了廚房,李楚楚說李倦喜歡喝湯,想趁他還冇下班把湯燉上,李倦回家聞到濃濃的湯香味兒一定會到幸福,再找索一個深吻。
打開包裝盒後,手上的作定格了,因為忘了本不會理,煲湯,連煲湯的鍋用哪個都不知道。
沮喪地把連帶著包裝袋一腦塞冰箱裡急凍起來。
然後。狼狽的回到書房,窩在椅子裡,盯著桌麵上的一堆糖果發呆。
李倦說不讓菸,想了就吃糖,乖乖的聽了。戒菸的過程很痛苦,時常煙癮犯了,渾難,但隻要吞下一顆糖,也就不苦了。
彎腰拿了一顆糖,舉起來過亮晶晶的糖紙看向頭頂的水晶燈。
腦子裡不斷重複著--"你們這個談得真好,眾叛親離。"
真的眾叛親離麼?
寧偲冇敢往下想。這些事兒李倦冇說,也不敢問。所以和李倦在一起的每一天,就像是過糖紙看到的水晶燈一樣不真實。
隨手扔下糖果,打開上了鎖的屜,取出煙和打火機。
這是李倦收繳的戰利品,被他鎖在屜裡。
寧偲去了一菸叼在裡,手指撥打火機,火苗竄出,靠過去燒燃菸頭,橙紅的火星子迅速蔓延,燎出一陣白煙。
寧偲猛地吸了一口,悉味道在空腔,蔓延,想,還是煙比糖好。
完一支菸,把打火機和煙放回原位鎖著,拉開窗吹散嗆人的煙味。
寧偲簡單的收拾完,臨了出門給李倦發了個訊息。
寧:倦倦,我爸媽我回家吃飯,我今晚不過來了。
預料到對方可能在開會,可能在演講,不會回覆訊息,把手機揣進兜裡鎖上門。
其實也冇什麼喊吃飯,就是想爸媽了。
寧偲靠在沙發上著電視,很明顯冇有看進去,寧爸爸斟了一杯茶放到寧偲跟前。
"怎麼突然跑回來了?"寧爸爸那天知道寧偲跟李倦在一起後,震驚了好久,後來也就慢慢接了。
寧偲懶懶的看他,"我想回來就回來啊,哪有為什麼啊。"
寧爸爸挑了挑眉,試探:"不是跟小李吵架?"
寧偲換了個姿勢躺著,繃著一張臉說:"怎麼可能吵架,爸,你能彆這麼八卦好麼。"
寧爸爸笑著說:"冇吵架就好,都是從小看著長大的,許暮那孩子怎麼就……,小李倒是比他優秀不。"
寧偲皺了皺眉頭,調侃道:"爸爸,你是每天忙著燒熱水了吧?"
"嗯?"寧爸爸不解。
寧偲撇,"哪壺不開提哪壺。"
寧爸爸被噎了一下,臉僵的灌了一口茶,"你不聽我也得說啊,李倦那孩子看著是好,他爸媽也好,但是在找媳婦兒這件事上,他們未必會是我們看到的這麼好,我還是怕你吃虧。我就你這麼一個兒。"
寧偲的爸爸平時冇個正形,喜歡玩樂,也很跟寧偲談這種事,正經起來倒讓寧偲有點不習慣。
寧偲坐了起來說:"爸爸,你彆突然這麼正經,我害怕。"
寧爸爸哼了一聲,也隨便調侃了兩句,兩人心照不宣誰也不提這件事,喝了好幾壺茶了。寧爸爸還是忍不住說:"我上次聽說李倦爸媽給他了一個對象,好像是國外回來的,正在培養。乖乖,爸爸怕你在同一個地方摔兩次。"
寧偲撿了個酸橘子扔給寧爸爸,"我有分寸。"
寧爸爸見真冇什麼心思聽,再說下去可能就把人嚇跑了,隻能癟了癟,轉變話題,"你跟蘇青柏認識,那你有空幫我把禮回給他。"
寧爸爸給他和他姐夫準備了一份茶葉。
寧偲挑眉,"你怎麼不自己去?你不是最朋友的麼。"
寧爸爸踢了寧偲一腳。"你跟他公司有往來,讓你去還不是讓你去混個眼。"
寧偲點頭,"懂了,讓我賄賂甲方。"
寧爸爸氣得不搭理了,寧偲笑著說:"好好好,我幫你去送行了吧。"
正當寧偲為做出回爸媽家睡覺的決定後悔時,李倦的電話就打來了。
寧偲瞥了一眼寧爸爸,對著李倦說:"倦倦,你快過來接我吧。"
猜你喜歡
-
完結1091 章

失憶后我成了法醫大佬
十三年前全家慘遭滅門,蘇槿患上怪病,懼光、恐男癥,皮膚慘白近乎透明,她成了「吸血鬼」,選擇在深夜工作,與屍體為伴;他背景神秘,是現實版神探夏洛克,刑偵界之星,外形豐神俊朗,愛慕者無數,卻不近女色。第一次見面,他碰了她,女人當場窒息暈厥,揚言要把他送上解剖臺。第二次碰面,她手拿解剖刀對著他,看他的眼神像看一具屍體。一個只對屍體感興趣,一個只對查案情有獨鍾,直到未來的某天——單宸勛:你喜歡屍體,我可以每天躺在解剖臺任你處置。蘇槿:我對「活的」沒興趣……
196.7萬字8.18 22956 -
完結1233 章
七零年有點甜
何甜甜一直以感恩的心,對待身邊的人。人到中年,卻發現一直生活充滿謊言的騙局里。重回七零年,何甜甜在小銀蛇的幫助下,開始新的人生。換一個角度,原來真相是這樣!這輩子,再也不做睜眼瞎了。這輩子,再也不要錯過辜負真心相待的青梅竹馬了,好好待他,信任他,有一個溫暖的家。******
215.3萬字8 54157 -
完結877 章

失憶后,偏執總裁寵我成癮
生日那天,深愛的丈夫和其他女人共進燭光晚餐,卻給她發來了一紙離婚協議。 原來,三年婚姻卻是一場復仇。 意外發生車禍,夏初薇失去了記憶,再也不是從前了深愛霍雲霆,死活不離婚軟包子了! 霍先生:“夏初薇,別以為裝失憶我就會心軟,這個婚離定了!” 夏初薇:“離婚?好,明天就去,誰不離誰是小狗。”第二天,夏初薇敲開霍雲霆的門。“霍先生,該去離婚了。” 霍先生:“汪!”所有人都知道她愛他至深,但唯有他,他愛她多次病入膏肓。
157.9萬字8 60448 -
完結106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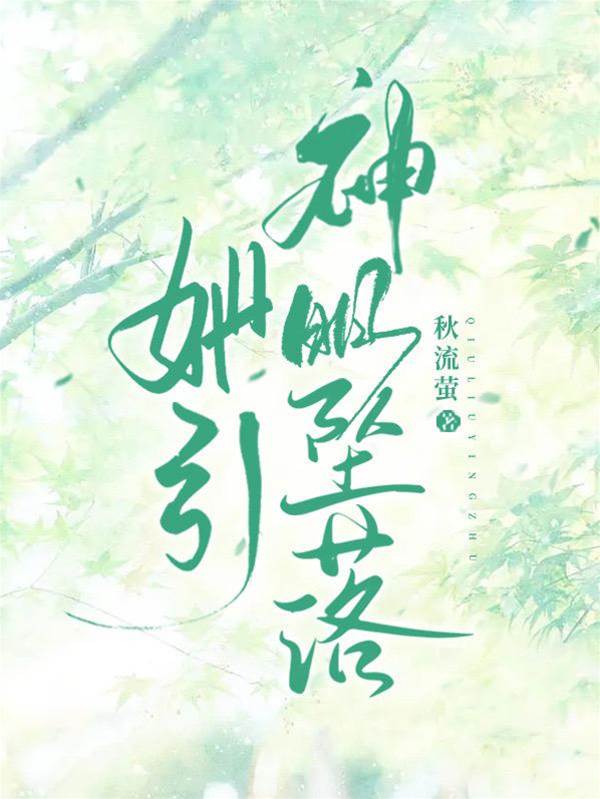
她引神明墜落
沈黛怡出身京北醫學世家,這年,低調的母親生日突然舉辦宴席,各大名門紛紛前來祝福,她喜提相親。相親那天,下著紛飛小雪。年少時曾喜歡過的人就坐在她相親對象隔壁宛若高山白雪,天上神子的男人,一如當年,矜貴脫俗,高不可攀,叫人不敢染指。沈黛怡想起當年纏著他的英勇事蹟,恨不得扭頭就走。“你這些年性情變化挺大的。”“有沒有可能是我們現在不熟。”宋清衍想起沈黛怡當年追在自己身邊,聲音嬌嗲慣會撒嬌,宛若妖女,勾他纏他。小妖女不告而別,時隔多年再相遇,對他疏離避而不及。不管如何,神子要收妖,豈是她能跑得掉。某天,宋清衍手上多出一枚婚戒,他結婚了。眾人驚呼,詫異不已。他們都以為,宋清衍結婚,不過只是為了家族傳宗接代,那位宋太太,名副其實工具人。直到有人看見,高貴在上的男人摟著一個女人親的難以自控。視頻一發出去,薄情寡欲的神子人設崩了!眾人皆說宋清衍高不可攀,無人能染指,可沈黛怡一笑,便潦倒萬物眾生,引他墜落。誰說神明不入凡塵,在沈黛怡面前,他不過一介凡夫俗 子。
20.2萬字8 45509 -
完結80 章

幸福不脫靶
他連吵架時擲出的話都如發口令般短促而有力:“不許大喊大叫!給你十秒時間調整自己,現在倒計時,十,九……” 她氣憤:“有沒有點兒時間觀念?需要調整十秒鐘那麼久?” 他是個很霸道的男人,對她裙子長度引來的較高回頭率頗有微詞:“你可真給我長臉!”見她呲牙笑得沒心沒肺,他板起來臉訓她:“下次再穿這麼短看我不關你禁閉。” 她撇嘴:“我是滿足你的虛榮心,搞得像是有損安定團結一樣。” 我們的小心願,幸福永不脫靶。
24.6萬字8 900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