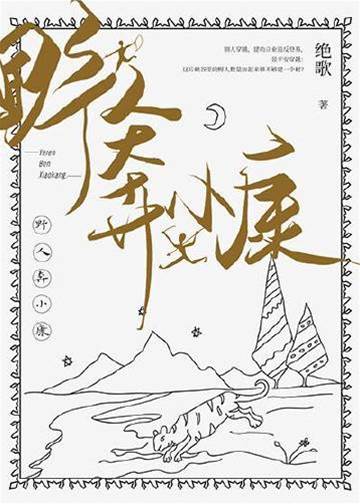《鳳求凰:溺寵醫妃》 第三百零二章 親送書信
提起信一事,阿蘭心里突然一,他是怎麼知道昨晚有人來給送過信的?
今日他拿著自己寫好的信進宮時,也沒有問過這個問題。
阿蘭只好裝瘋賣傻:“什麼信?你不是把我寫給公主的信帶進宮去了嗎?”
蒼冥絕臉上冷冷一笑,反而坐到了一旁的椅子上,昨天晚上發生的事他一清二楚,只是沒有說出來而已。
他一直以為昨晚來送信的人是賽月,直到今日進了宮,對昨晚的事閉口不提,他才發現,昨晚來送信的人并不是。
待在蕭長歌邊有武功的人,除了賽月,就是晟舟國的哲而將軍,但是哲而又怎麼會這麼知冥王府的路?
“不要裝傻,快說。”蒼冥絕狹長的眼眸看向了。
明溪的份在宮中一直都是個,沒有人知道,到底能不能說?
想了一會,阿蘭道:“昨晚那人的臉我沒有看清,不過公主邊有如此武功能夠輕而易舉出宮的人,也就只有哲而將軍了。”
哲而?蒼冥絕聽了這個回答,眉頭一皺,顯然不是很相信。
不過他也沒有繼續追問下去,既然這個哲而有這麼大的本事,能夠在短短幾天的時間悉宮中路線和冥王府的路線,能夠悄無聲息地潛進冥王府送出信,那他也沒有什麼好說的。
但是不管出來送信的人是誰,只要是蕭長歌邊值得信任的人,對于沒有什麼威脅的,就好。
蒼冥絕點點頭,臉稍微好了一點:“好好休息。”
轉便出了門。
屋里頓時安靜下來,只有阿蘭沉靜又有些張的呼吸聲。
這一覺睡的很香,蕭長歌醒來的時候房間里并沒有點燈,外面暗淡的線投進房間,有種半黑不黑的覺。
Advertisement
聽見聲音的賽月進去點了燭火,房間里面頓時亮了起來。
“賽月,現在什麼時辰了?”蕭長歌有些迷糊地問道。
“回公主,酉時剛到。”賽月回道。
也不算太晚,蕭長歌起來梳妝整理了一下頭發,賽月為裹上厚厚的披風,用了晚膳之后,才把那封信拿出來。
“公主,這是冥王府來的信。”賽月遞上了信,外封的字跡是阿蘭無疑。
蕭長歌有些疑地看著這封信,手接過,皺著眉頭看了賽月一眼:“這封信是誰給你的?”
想起早晨蒼冥絕叮囑過的那番話,賽月猶豫了一會,還是按照原話答道:“這是冥王府的一個小廝帶進來的,那時奴婢見公主還在休息,便先收下了。”
冥王府來的小廝?原先讓明溪送出去的那封信是暗中作的,如果是冥王府的小廝送來,定是蒼冥絕已經知道了這件事。
“那個小廝是誰?他日我好尋個機會謝他。”蕭長歌裝作不經意地說道,單純只是為了謝。
面對的步步問,賽月不知該如何作答,只回道:“此人奴婢沒見過,也沒有問是誰,若是公主需要知道此人的份,奴婢一定前去打聽。”
賽月的臉上有幾分約約的愧疚和不安,蕭長歌的視線從的臉上落下,角勾起一抹笑容。
“不用了,我只是隨便問問。我去一趟哲而將軍那邊。”蕭長歌說罷,便攜著信起。
賽月心里明白的意思,顯然是對自己有些敷衍的語氣有些不滿意,但是也無奈,又不能說出實,也無法消除的誤會。
只能這樣繼續下去,等著有一天真相發白,蕭長歌能知道蒼冥絕對的一番良苦用心。
Advertisement
賽月撐著油紙傘,跟在蕭長歌的后來到了哲而將軍的寢殿。
“你在這里候著,我進去說會話。”蕭長歌轉對賽月道。
每次來到這里,蕭長歌都不讓自己繼續跟進去,而每次進去的時間都保持在半個時辰左右,從來沒有誤差。
“是,奴婢在這里守著,公主您放心地去吧。”賽月立在亭臺中,看著蕭長歌的影越來越遠。
為了掩人耳目,蕭長歌特意將明溪的寢殿安排在了哲而的院落中,每次進去的時候,都是繞過正堂,走向后面的房間。
敲了門進去,明溪正在里面藥,手臂上面有一道目驚心的紅,仿佛是被人用刀劃傷的。
“明溪,你怎麼傷了?別,我來幫你上藥。”蕭長歌好歹也是個專業的大夫,知道怎麼上藥對傷口有益。
明溪的眼眸中閃過一的詫異,隨后很快平靜下來,任由著用練的手勢作著自己的手臂。
“明溪,你的武功不至于讓人劃傷,雖然傷口不深,但是看上去十分連貫,是在冥王府被傷的嗎?”蕭長歌上完了藥,一邊包扎著紗布,一邊說道。
明溪攏了袖,搖了搖頭:“不是,昨晚出宮的時候在宮中最后一道城墻的時候,被侍衛發現,幸虧我及時把他打暈,但是手臂也被他劃了一道。
反而是到了冥王府的時候,卻一路暢通,覺好像他們都本看不見我一樣,我找到你說的那個房間,阿蘭并不在里面。我藏了一會,之后才跟著兩個侍找到了阿蘭的房間,竟然離你說的那個房間相隔甚遠。”
相隔甚遠?種種跡象都說明了蒼冥絕費勁千辛萬苦把帶回去,卻沒有花太多的心思在上,又是為什麼?
Advertisement
難道是因為自己?蕭長歌突然被自己的這個想法嚇了一跳,忽而又冷笑起來。
竟然他已經認定了阿蘭就是蕭長歌,又怎麼可能會對自己有一的牽掛。
蕭長歌眉頭鎖:“你去冥王府的時候,他們的人多嗎?”
“有一些。”
“他們沒有發現你?”
明溪卻猶豫了一會:“好像發現,好像又沒發現,總之一切都進行的很順利,順利的有些詭異。”
蒼冥絕的心思向來藏的深,這次他突然把阿蘭帶走,必定料到了會到他的府邸去。
但是為什麼不加以阻攔,反而還默認了讓的人進去。
而今日送來的信,也是由冥王府的小廝送來的,這說明了蒼冥絕已經知道了事發生的一切。
“最大的一種可能就是,我們的行已經被蒼冥絕猜到,他是故意讓你輕而易舉地把信送給阿蘭的。”以蕭長歌對他的了解程度,定然如此。
但是明溪卻搖了搖頭:“這個時候,他應該是對我們千防萬防,不讓我們見到阿蘭才是啊!”
就連一向知道他心里在想什麼的蕭長歌,也不猜不出來他此次的目的。
“不僅如此,今晨,冥王府的小廝還來到東華園,送來了阿蘭的回信,由賽月轉給我。”蕭長歌從自己的袖中拿出了那封嚴實的信。
還沒有拆封,打算拿給明溪,讓他先看。
既然阿蘭能夠回信,就代表沒事,而信中的容,提及明溪的程度,一定會比自己多。
想必阿蘭最想能看到這封信的人,一定是明溪。
但是明溪卻有些震驚地搖了搖頭眼中著疑:“這封信是今晨送來的?”
蕭長歌點點頭,忽而覺得哪里有些不對勁:“有什麼問題嗎?”
Advertisement
“我送信的時候就說過,今晚會再去一次冥王府拿回信,讓等著我,怎麼今晨就讓冥王府的小廝送來了?”明溪有些震驚。
阿蘭不可能不聽他的話,私自改變時間,還讓冥王府的小廝來送信。
“我們能肯定的是,冥王已經知道了我們往來信,而且還是被他默許的。看來我們還真是高估了自己,以為一切都悄無聲息,有條不紊地進行著。”蕭長歌悠然地看著窗外,眉宇之間著淡淡的愁緒。
“這件事被他知道了也好,以后我們和阿蘭往來信的時候就可以更加便捷,不用的。只是信的容不能太。”明溪道。
有利也有弊,想來這種事就算他日別人知道了,也只會以為是公主和奴婢之間的所致,定然不會加以怪責。
“恩。”蕭長歌睫低垂,卻沒有再說話。
兩人安靜了一會,各想著各的心事,時間快到半個時辰時,蕭長歌才開口道:“你打暈宮中侍衛的事估計明日就會傳到皇上耳里,這幾日你都不要出去,先避避風頭。”
“我有分寸,再說在哲而將軍這里,很安全。”明溪點點頭。
蕭長歌擔心的不是這個,早就和哲而說過這件事,況且有哲而在,很放心。
“我擔心的是你的傷口,這幾日一直都要上藥,但是所需要的藥和傷口都必須呈報太醫院,才能拿藥,若是到太醫院去拿藥,定然會知道是刀傷,所以,得想個辦法拿藥才行。”蕭長歌眉頭鎖,冥思苦想。
原來擔心的是這個,明溪笑道:“從晟舟國來的時候,哲而將軍帶了幾名太醫,在他的宮中也有一些金瘡藥,都是上好名貴的藥,所以這個問題不必擔心。”
蕭長歌松了一口氣:“那就好。”
兩人說了一會話,蕭長歌看了看外面的天,已經約莫有兩個時辰了,便告別了明溪。
“明天我再過來看你,記得按時上藥。”蕭長歌說罷,便轉起離開。
外面的賽月一直守候在亭臺,直到過幔帳才看見蕭長歌的人影,連忙撐傘迎了過去。
“回吧。”蕭長歌并肩和賽月一起回到了東華園。
兩人慢悠悠地在路上走著,也不急躁。
“王妃,你頭上的玉飾應該是凰錦玉所制的吧?看起來落落大方,完全不失氣場。”一個連滴滴的聲音沖著難得進宮的溫王妃道。
葉霄蘿聽了的贊揚,很是滿意地勾勾角,向了自己頭上的玉飾,良久都沒有放下來。
猜你喜歡
-
連載1901 章

紅樓之挽天傾
千紅一哭,萬艷同悲。白骨如山忘姓氏,無非公子與紅妝。后世青年魂穿紅樓世界中寧國遠親之上,為了免于被賈府牽連之命運,只好步步為營,然而茫然四顧,發現家國天下,亂世將臨,為不使神州陸沉,遍地膻腥,只好提三尺劍,掃不臣,蕩賊寇,平韃虜,挽天之傾!這一切,從截胡秦可卿開始……
308.1萬字8.18 15107 -
完結209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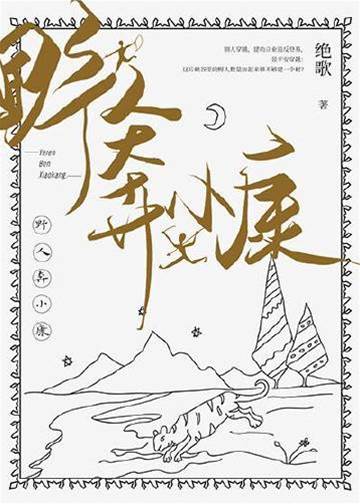
野人奔小康
景平安在職場上辛苦打拼,實現財富自由,卻猝死在慶功宴上,悲催地穿越成剛出生的小野人。有多野?山頂洞人有多野,她就有多野,野人親媽茹毛飲血。鉆木取火,從我開始。別人穿越,建功立業造反登基,景平安穿越:這片峽谷里的野人數量加起來夠不夠建一個村?…
80.8萬字8 5299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