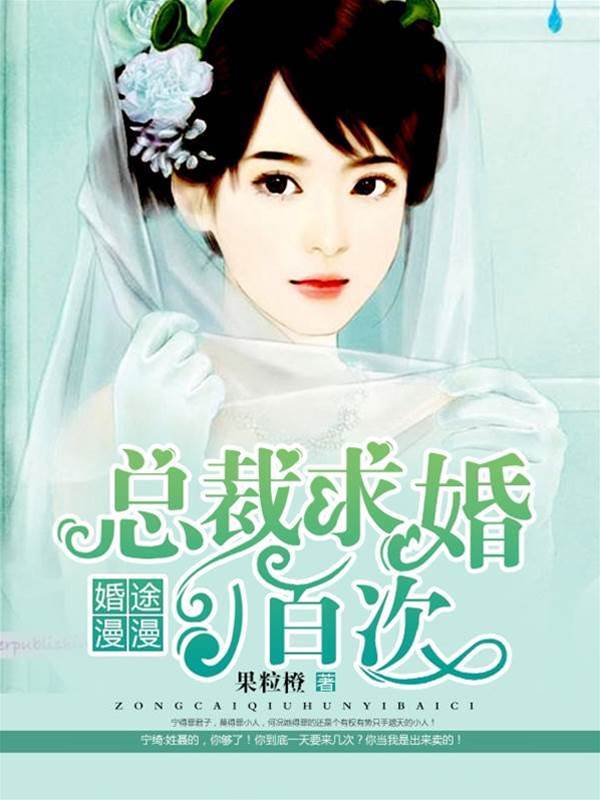《終身妥協》 第62章 晉江獨家首發【一更】……
晚上十點半,公園的天停車場幾乎沒有車的影子,路燈昏黃,四周安靜得可怕。
去停車場的路上,安棠捧著茶邊吸邊抹淚,無論賀言郁在邊如何哄,就是不搭理,甚至連眼神都沒有分給他。
男人拎著的包,語氣溫而誠懇:“棠棠,我錯了。”
“你理一理我。”
“我剛剛只是想逗逗你,結果……咳咳,這是我的失誤。”
“棠棠……”
不管他說再多,安棠渾散發著‘你完了,你惹到我了,莫挨我’的氣息。
他們來到停車的地方,賀言郁到底沒忍住,一把拽住的手腕,把人抱在懷里。
安棠像是被劫持似的,直的靠著他,憋了很久,終于開口罵他:“你不講武德暗害我!”
“是是是,我不講武德暗害你。”賀言郁趕應道。
看在他態度誠懇的份上,安棠的氣也消了大半,哼了聲,問道:“我吃得多嗎?”
賀言郁違心道:“不多,正常食量。”
“下次還敢欺負我嗎?”
“不敢,我給你欺負。”該怎麼哄人,他現在已經自一套。
要是趙子真瞧見這一幕,鐵定要嚇得半死。
他現在哪還像當初的賀言郁,簡直就像換了芯子。
安棠的氣來得快,去得也快,笑道:“這還差不多。”
男人的掌心過烏黑的長發,“現在不生氣了?”
“不氣了,不過……”
突然頓了頓,讓賀言郁心頭一,“不過什麼?”
“先前你踩的水洼,水漬濺我小上了,你得給我干凈。”
安棠很干凈,甚至有點小潔癖,像地上的水漬濺到上這種,其實是不了的。
賀言郁垂眸,掃了眼那纖細筆直的長,安棠今天出門穿的是一淺卡其套,上搭薄款白襯,外面就是套的外套,下有點像百褶,長度及膝。
Advertisement
“車上有巾,我現在就給你干凈?”男人語氣溫和,眼神卻帶著一意味不明的笑。
安棠剛剛吸完最后一口茶,沒注意到他晦暗的眸,把垃圾丟進垃圾桶,聞言,笑道:“好啊。”
“你先去后車座等我。”賀言郁說。
他繞到前面駕駛座,從屜里拿出一包巾,隨即關上車門,打開后車座,彎腰坐進去。
安棠把搭在他的上,也跟著了張巾小上的水漬。
還不忘埋怨:“都怪你。”
賀言郁的掌心握著的小,手上拿著紙巾仔細拭,聞言,笑道:“還在怨我?我這不是已經道歉并補償了嗎?”
“你哪有補償?”安棠很疑。
“給你干凈不算嗎?”
安棠認真提問:“這是補償嗎?”
“那你想讓我怎麼補償?”男人低低笑出聲,握著小的手輕輕挲細的。
他的指腹有薄繭,帶著一礪,安棠只覺得自己的小像是被蛇纏住,一說不出的直躥心頭。
安棠一看賀言郁的眼神,就知道他現在不安好心,撇開視線,轉移話題:“我不要你了。”
說完,想收回搭在賀言郁膝蓋上的小。
寂靜的車響起磁人的淺笑,聽得安棠耳朵一,的小還沒來得及收回,男人握著的腳踝,五指用力,把整個人都往前拖了一小段距離。
現在直接變的大擱在他膝蓋上。
安棠撐著車椅,整個人怔住了。
懵的看了眼賀言郁,反應像是慢了好幾拍,過了會才意識到現在的姿勢有多麼不對勁。
“你給我松開!”安棠微紅著臉,很不好意思,手扯了扯子,試圖把它拉長,然后多蓋住一些地方。
Advertisement
賀言郁注意到的小作,微涼的指尖點了點安棠的大,笑道:“不是說補償你嗎?”
“誰稀罕你的補償,你快松開。”安棠提醒他:“你前不久才說過不會欺負我的,你要是敢食言而,你……你就是偽君子,真小人。”
許是近朱者赤,近墨者黑,跟安棠待久了,賀言郁也從上學到一兩分寫作上的語言天賦。
他握著安棠的彎,微笑著回:“棠棠難道沒聽過一句話?”
“什麼話?”
“牡丹花下死,做鬼也風/流。”
安棠:“……”
一派胡言,有辱斯文,簡直不統!
義正言辭的教訓他這種行為:“齷齪,可恥!”
“哦?”男人尾音上揚,像小鉤子似的,撓得人心,他的手已經探進去,“是嗎?”
安棠的表瞬間繃不住。
輕輕栗著,嗓音快要不調:“把你的手拿出去……”
“棠棠,我齷齪可恥嗎?”賀言郁溫聲問。
“你極其齷齪、可恥!”安棠咬了咬,被他狗得不行的行為氣得淚眼婆娑,控訴道:“你言而無信,你不講武德!”
快要晚上十一點了,萬籟俱寂,公園的草叢里時不時有蟲鳴聲。
寂靜的車響起安棠的啜泣,最開始還嗚嗚咽咽的罵賀言郁,到后面直接變了音調,甚至連句完整的話都說不出來。
臉上淌著晶瑩的淚痕,眼尾泛著不正常的緋紅,整個人噎噎。
安棠幾乎沒有力氣,趴趴的靠在賀言郁上,男人摟著,出巾在面前慢條斯理的了手指。
看得牙,但已經沒力氣去打他。
賀言郁把的子放下來遮住大,他抱著安棠,溫香懷,是每個男人的夢。
Advertisement
他親了親安棠臉上的淚痕,笑道:“緩過來了嗎?”
安棠想到自己先前的反應,臉紅一片,埋頭憤憤的說:“我恨你。”
男人的心大好,“沒事,我你。”
開車回到景莊園已經晚上十一點四十。
安棠走不道,賀言郁只好將打橫抱起。
周嬸見他倆回來,尤其是安棠臉上還帶著紅暈,一個過來人,自然懂得。
沒有湊上去打攪他們,遠遠站著,笑著目送兩人上樓。
安棠抱著賀言郁的脖子,趴在他肩頭,窺視到周嬸的表,頓時覺得自己丟臉丟大發了。
低頭咬了口男人的肩膀,埋怨道:“周嬸肯定以為我兩在外面干了什麼不可告人的事。”
“這有什麼?”賀言郁沒皮沒臉道:“在家里也不是沒干過。”
安棠:“……?”
蹬了蹬,非要下來,甚至很嫌棄他,“我沒想到你竟是這樣的人。”
男人推開臥室門,抱著人進去,隨即用腳踢回去關上。
他把人抵在墻上,從車上忍到現在,已經是極限了。
賀言郁咬著的耳垂,在耳邊輕:“天天罵我老/批,臭流/氓,棠棠……”
“你還真當我是正人君子,嗯?”
猜你喜歡
-
完結831 章

天降三寶:總裁老公壞又甜
本書暫時停更,請大家在站內搜索《天降三寶:總裁老公壞又甜》觀看最新章節~ 傳聞毀容之後,秦三爺心狠手辣,接連弄死了兩個未婚妻,全城的女人冇人敢嫁。但蘇辭月嫁了。“女人,以後我罩你。”“我的媽咪,以後誰都不能碰!”剛結婚,她就被兩個小萌娃瘋狂爭搶。秦三爺一手一個萌寶拎出去,關上門,“老婆,我們該進入正題了。”蘇辭月懵比又彷徨,“我要當兩個孩子的後媽了?”英俊的男人淡淡挑唇一笑,“首先,你是親媽,其次,不是兩個,是三個。”蘇辭月風中淩亂,她什麼時候給秦三爺生了三個孩子?還有,說好了的毀容,說好的心狠手辣呢?為什麼她被他寵上了天?
146.4萬字8.57 998879 -
完結467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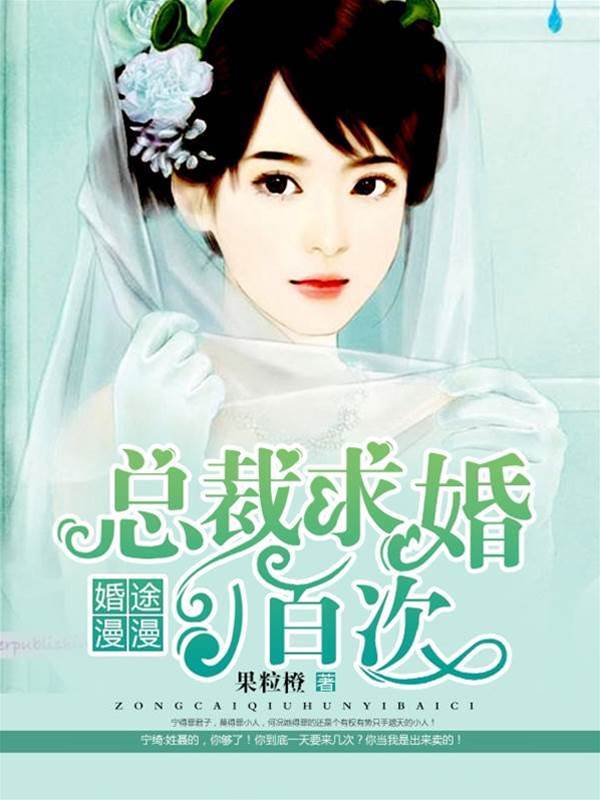
婚途漫漫,總裁求婚一百次
寧得罪君子,莫得罪小人,何況她得罪的還是個有權有勢只手遮天的小人! 寧綺:姓聶的,你夠了!你到底一天要來幾次?你當我是出來賣的! 聶惟靳:1.3億,不多上幾次我豈不是虧死? 寧綺:你去死! 聶惟靳:誰叫你退我婚,退我婚! 天啊,能不能不要再拿陳年舊事來說,你到底要念叨幾年? 真是醉了! 這就是一個腹黑奸詐瑕疵必報作死過頭的大灰狼將小白兔吃得渣渣都沒得剩的故事。
118.4萬字8 17045 -
完結870 章

神秘首席甜寵妻
“跟我在一起吧,我很干凈的。”第一次見面,季溏心在酒店將男人壓在身下,卻被他冷眼推開,“我不找小姐,滾。”第二次見面,他將一紙合約擺在面前,眼底是她看不懂的情緒。“嫁給我,從此J城無人敢欺你,你想要的一切我都能給!”走投無路之際,季溏心嫁給了這個比自己大了將近十歲的男人,他是高高在上身份尊貴的帝國總裁,而她只是一個涉世未深的黃毛丫頭,本以為是一場各取所需的游戲,卻沒想到他處處寵愛,讓她生了廝守一生的心。可是,當她看著驗孕棒的兩條紅杠,還未來得及開口便被進醫院。冰冷的手術臺上,真相昭然令人痛徹心...
156.7萬字8 71938 -
完結742 章

爺!認輸吧,夫人黑白兩道皆馬甲
溫黎一出生就克死了母親,被父親視為不祥之人,丟給了鄉下的外婆帶【短劇已上線】千金小姐就此淪為鄉野丫頭,父親領養的有福之女則從孤兒一躍成了京城名媛。 十七年后溫黎被接回豪門,大家都等著看這位鄉下大小姐的笑話,等著看她這個真千金如何被受寵的假千金欺負碾壓。 怎料真千金不僅貌美如花,一進家門還強懟富豪爹:“我不祥?難道不是你克妻?” 眾人嗤道:逞嘴上功夫有什麼用?溫家大少爺是公司繼承人,收養的有福之女成了設計師,溫家最小的三小姐數學競賽獎拿到手軟,個個都是人中龍鳳。 溫黎一個鄉下長大的拿什麼在溫家立足? 等等,京大宋教授怎麼追著她解題?電競大神求她進隊?郭院長唯她馬首是瞻……??? 數學天才、雇傭兵王、黑客教父、地下拳王、醫學神話、金洲之王、頂級賽車手、著名設計師、全球五百強企業股東……馬甲套了一層又一層。 還差點一槍打死京城權勢滔天的陸五爺。 陸五爺非但不計較,還為人鞍前馬后。她炸城,他點火;她殺人,他收尸… 【天才人狠話不多女主VS腹黑心機戀愛腦男主】 【打臉掉馬虐渣,雙潔,男追女,男狠女強,有敵對馬甲】 注:爽文言情,有男主且非花瓶,男女主在各自領域強。 無腦爽、勿糾結邏輯。
145.8萬字8 28516 -
完結177 章

云朵和山先生
[現代情感] 《云朵和山先生》作者:十三澗【完結】 文案 破鏡重圓|都市插敘 【重逢前:天然病美人vs傲嬌男中醫; 重逢后:算法程序員兼乙方vsAI醫療總裁兼甲方】 1. 十六歲那年,時云舒被接到北城中醫世家江家養病,聽聞江家小少爺江淮景是出了名的離經叛道,桀驁不馴,無人能得他正眼相看。 時云舒謹記外公教誨,對
26.3萬字8 162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