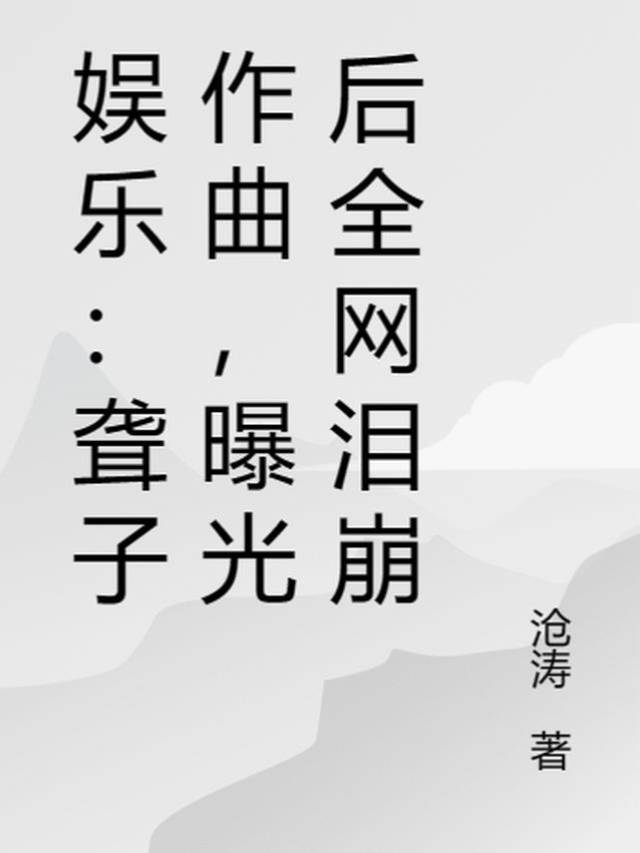《小織梨》 第68章 “寶寶,你耍流氓。”
一個晚上,蕭翎跑了兩次浴室。
頻繁洗冷水澡再加上睡眠不足的緣故,蕭翎也是不負眾的冒了。
蘇明的手中拿著文件恭恭敬敬地站在一旁,看著自家老板那不停打著噴嚏,一臉憔悴的模樣,在心中默默地搖了搖頭。
終於,在蕭翎完紙盒子裏最後一張紙的時候,蘇明趕忙從一邊的櫃子裏拿出新的一包紙將其打開放在蕭翎桌上的紙盒子裏。
他猶豫了一下,還是鼓起勇氣關心地開口:“老板,您要喝點藥麽?”
蕭翎手拿紙的作一頓,抬眸輕掃過蘇明的臉頰。
因為頻繁地鼻子,導致他的鼻尖已經被紙磨得有些泛紅,眼尾也泛著淡紅,早已經沒有了往日裏的氣場,更多的是一種說不出來的可憐。
蕭翎將手中的紙扔進自己旁的垃圾桶中,語氣淡淡地反問著蘇明:“你覺得我需要麽?”
蘇明低下頭,心中暗暗腹誹著。
他怎麽知道要不要啊,他又不是肚子裏的蛔蟲。
雖然心中已經罵了蕭翎一萬句,但為了保住自己的這份工作,蘇明還是試探地開口:
“您......不需要?”
人啊,有時候就不能做違心事。蘇明本來一直想著幹完這個月就走人,但一月複一月,他都沒有提出辭職,而他不辭職的原因不是因為自己有多麽熱這份工作,隻是蕭翎總是會給他加工資。
作為一名社畜,誰能拒絕一個會不定時給自己加工資的老板。
蕭翎低低地“嗯”了一聲,有些疲倦地靠在椅背上:“通知下去,半個小時後行政部門在十五樓會議室開會。”
“好的老板。”
蘇明恭恭敬敬地退出了蕭翎的辦公室,在關上辦公室門的那一瞬間,他也不再繼續忍耐,隔著門對著空氣垂了幾下。
Advertisement
而這一幕,不偏不倚被趕來的趙蘇蘇看在了眼中。
趙蘇蘇有些疑的看著在自己不遠正打著空氣的蘇助理:“蘇助理,你幹什麽呢?”
蘇明被突然冒出的聲音嚇了一大跳,立刻收回剛才自己手上的作,雙手害怕地捂著自己的心髒看向趙蘇蘇。
“趙、趙小姐。”
他勉為其難地出了一個微笑:“你......你是來找老板的?”
趙蘇蘇點了點頭:“蕭總在辦公室麽?”
“在的,在的。”
“好,那蘇助理你繼續去忙吧,我找你老板有些事。”
在蘇明離開之後,趙蘇蘇才敲響了蕭翎辦公室的門。
在辦公室的門被推開的時候,蕭翎才懶散地睜開閉著的雙眼,目瞥見站在門口的趙蘇蘇後,又重新合上了眼睛。
趙蘇蘇的臉上依舊掛著笑:“蕭總。”
與第一次見麵不同的是,趙蘇蘇這一次並沒有像第一次見麵那般故作嫵,反而多了一份正經。
蕭翎沒有睜眼,隻是語氣淡淡的問:“什麽事?”
趙蘇蘇從包裏掏出了一份函,輕輕地放在了蕭翎的辦公桌上的一角:“我爸他走了。”
“節哀。”
“葬禮在後天舉行,要是蕭總有空的話,也希蕭總可以前來送我爸最後一程吧。”
說完,趙蘇蘇見蕭翎什麽反應都沒有,隻是莞爾一笑。
歎了一口氣:“聽說蕭總有朋友了,還是上次帶著一起去錫城的那個。”
蕭翎的眼皮子了,抬眸看向趙蘇蘇,似乎在等把話說完。
“之前那一次給蕭總帶來的麻煩,今天我也在這裏跟蕭總說聲抱歉,其實那天是我父親著我要那麽做的,”趙蘇蘇扯了扯角,“畢竟他知道自己活不久了,又擔心我,才會想著依靠蕭總來穩固我在趙氏集團的地位。”
Advertisement
趙蘇蘇作為趙家的千金,趙東勉從小就將希寄托在的上。
而當得知自己命不久矣的時候,趙東勉唯一放心不下的就是自己的兒趙蘇蘇將來在趙氏集團能否繼續站穩腳跟。
趙東勉比誰都清楚,趙氏集團裏的那些東們都對自己這個董事長的位置虎視眈眈,而自己的兒也沒有多的閱曆,跟那一群老狐貍爭搶一個董事長的位置,勝算是小之又小的。
若趙氏集團董事長的位置真的落了那幾個東的手裏,那麽他兒趙蘇蘇的日子也不會好過。
為了自己兒之後的路,趙東勉唯一能想到的那邊就是跟蕭氏集團聯姻,借助著蕭翎的力量讓趙蘇蘇在趙氏集團站穩腳跟。
於是在那一天,趙東勉強拉著趙蘇蘇去見了蕭翎,並且在蕭翎來之前,趙東勉便一直叮囑著趙蘇蘇等蕭翎來之後要表現得嫵一點。
在這個小圈裏,所有的家長似乎都把自己的兒當作他們在商業場上可以用來站穩腳跟的工。
不過慶幸的是,趙蘇蘇遇到的是最討厭這樣事的蕭翎。
趙蘇蘇聳了聳肩:“真的很抱歉蕭總,其實我也不想那樣的。”
作為一個從小在趙東勉嚴格要求下長的孩,趙蘇蘇這輩子最討厭的事那邊就是按部就班的生活以及參與這種鉤心鬥角的商業競爭。
可奈何自己的父親命不久矣,也隻好假裝聽父親的話,但在趙東勉真的去世之後,卻直接讓位了趙氏集團董事長的位置。
蕭翎的神淡淡:“都過去了,沒什麽抱歉不抱歉的。”
......
沈織梨醒來的時候,的旁已經沒有人了。
舒服的窩在蕭翎的被子裏不願意起床,昨天自己睡了一個有史以來從未有過的好覺,甚至夢到了一些兒不宜的畫麵。
Advertisement
蕭翎的床就好似有一種魔力一般,讓更本就不想起床。蕭翎的床給了一種覺,這種覺該怎麽形容了,就如同“看人家的手機永遠比自己好”的那種覺。
於是,一個下午沈織梨都躺在蕭翎的床上思考著自己該如何霸占蕭翎的床,連飯都忘記了吃。
直到接近傍晚時分,沈織梨才強迫著自己離開了蕭翎的床。
等到沈織梨洗漱好從衛生間裏出來的時候,大門響起了指紋碼驗證正確的聲音,沈織梨立刻朝著大門口奔去,看見蕭翎的影出現在門口時,更是如同以往一樣撲在了蕭翎的上。
以往的時候,每次蕭翎回來,沈織梨都喜歡撲在蕭翎的上,蕭翎也能將孩輕鬆抱住。
可這一次,蕭翎卻被孩撞的向後踉蹌了一步。
隔著服察覺到男人上的溫異常的燙,沈織梨皺起眉頭:“你怎麽了?”
蕭翎搖頭:“沒怎麽,有點小冒。”
沈織梨將手背放在男人的額頭,眉頭皺的更深了一些:“什麽小冒,都已經發燒了,快先去客廳坐著,我去找溫計。”
說完,便跑到蕭翎的後推著蕭翎的後背將男人推到了客廳。
蕭翎聽話的坐在沙發上,目看著不遠正在翻箱倒櫃照著溫計和冒藥的孩。
沈織梨從櫃子裏找出溫計,然後拿著水銀溫計晃了晃,放在眼前看了看,這才走到男人的麵前。
“把服了。”
蕭翎一愣:“嗯?”
“愣著幹嘛?這玩意得放你腋下。”因為著急,沈織梨說話也變得有些語無倫次了起來,“你不的話我就親自手了。”
蕭翎挑了一下眉,逗著孩:“行啊,織梨幫我。”
活了二十九年,他還是第一次遇到測溫要服的。
Advertisement
沈織梨沒有過照顧人的經驗,看著蕭翎穿著西裝的樣子,覺得這水銀溫計很難放進去,這才想到讓他把服了測溫。
沈織梨將手中的溫計放下,一言不發的手掉了男人上厚重的西裝外套,然後手指輕輕的覆蓋在男人白襯的紐扣上,一粒一粒地解著。
反正該看的不該看的都已經看過了,現在人命要,還哪顧得上那麽多。
在沈織梨解到最後一顆紐扣的時候,蕭翎的手卻突然拉著孩的手腕往自己的懷裏一帶。
沈織梨一個重心不穩直接跌在了男人的上,手更是按在了男人落在外的上。
蕭翎悶哼一聲,目含笑的看著自己上的孩,出聲調侃著:“寶寶,你耍流氓。”
“......”
沈織梨瞪了一眼蕭翎,深呼吸了一口氣:“別貧,趕測溫。”
真的是,燙這樣還要先來調戲一下自己。
氣的沈織梨牙很想在蕭翎的鎖骨上咬下一口,可看著男人有些蒼白的,心中更多的還是心疼。
想了想,沈織梨還是決定不跟患者計較這些。
想要站起子,可是男人的手臂卻環著的腰不讓起來。
沈織梨看著蕭翎,示意他趕鬆手。
蕭翎卻垂著個腦袋,出一副可憐的模樣:“親一口再測好不好?”
“蕭翎!”
蕭翎湊近孩的臉頰,怕將自己的冒傳染給孩,克製的在孩的臉頰上落下一個吻:“寶寶,你兇我。”
“.......”
蕭翎鬆開攬著孩腰的手,將自己上這一件已經被解開紐扣的襯下,拿起茶幾上的水銀溫計在沈織梨的注視下,乖乖的夾在了腋下。
“這才對嘛——”沈織梨在蕭翎的臉頰上落下一個吻,“給你的獎勵。”
蕭翎愉快的揚了揚眉,角更是止不住的笑意:
“謝謝寶寶。”
猜你喜歡
-
完結68 章

墜落于你
清初和職業選手顧祁澤在一起兩年。 他年少成名,萬人追捧,被譽為職業野神,清初當了他兩年的地下戀人,卻只是他無數曖昧的其中之一。 一切在無意撞見中破碎,朋友問他:“不是有清初了嗎,怎麼,這個也想收。” 彼時的顧祁澤靠在沙發里,眼瞼上挑,漫不經心:“談個女朋友而已,還真指望我要守身如玉?” 清初知道,他家里有錢,天之驕子看不上她;作為頂級海王,他魚塘里的妹妹數不勝數。 當頭一棒,清初徹底清醒。 她走了,顧祁澤和朋友輕嘲低笑:“她那樣的條件,找得到比我好的?” - S系列總決賽聯賽,清初作為空降播音到臺上大放異彩。 一夜之間,大家都在搜索那個叫清初的女孩,她爆紅了。 彼時的顧祁澤已然是全球總決賽TOP選手,面對臺上熟悉的女孩,他如遭重擊。 仿佛心臟瞬間被抓住,那是心動的感覺。 他知道,是他后悔了。 他徹底想挽回曾經的白月光。 然而來到她門口等兩小時抽了滿地煙頭后,門開了,一個溫柔少年渾身濕漉站在門口,剛洗完澡。 “你找誰?”少年聲線溫柔的問。 顧祁澤當頭一棒,渾身涼透。 此后,這位爺瘋了。他求饒,認錯,瘋狂彌補,決絕的時候甚至跪下求著她哭了一晚。 他說:“初初,我給你當備胎,你看我一眼好不好……” 追妻火葬場/浪子回頭/SC 排雷: 男主感情玩咖,非絕對1V1,有男二,文中所有男人潔,女主隨便。女主和男二后期在一起過會分手,不喜慎看。 注:游戲設定英雄聯盟,正文賽事非實際存在,游戲內所有戰隊等等設定含私設,勿與現實掛鉤,也非電競主線,啾咪。 一句話簡介:后悔嗎?后悔也沒用 立意:在逆境中前行,在逆境中成長
32.5萬字8 6534 -
完結1181 章

分手后,她藏起孕肚繼承億萬家產
葉芷萌當了五年替身,她藏起鋒芒,裝得溫柔乖順,極盡所能的滿足厲行淵所有的需求,卻不被珍惜。直到,厲行淵和財閥千金聯姻的消息傳來。乖順替身不演了,光速甩了渣男,藏起孕肚跑路。五年後,她搖身一變,成了千億財…
205.2萬字8.18 79263 -
連載128 章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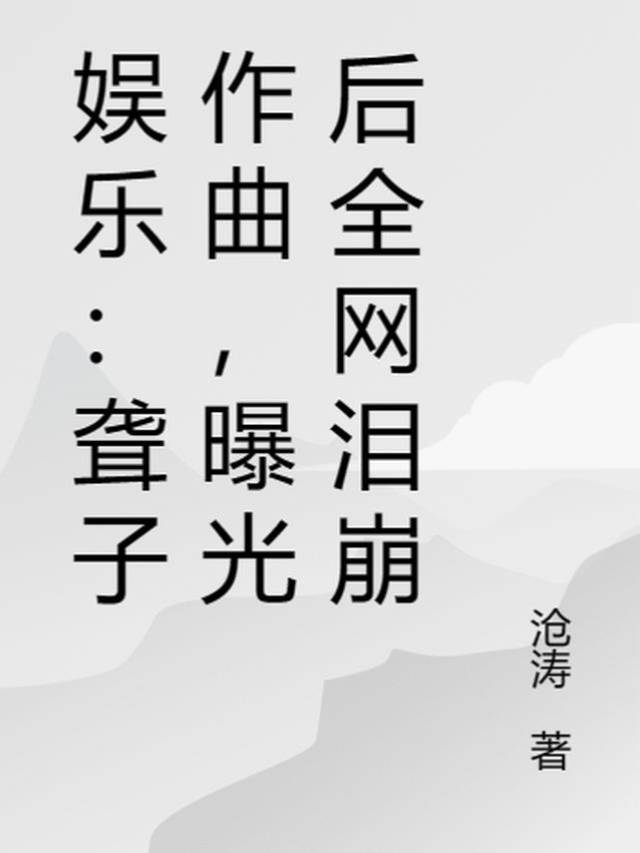
娛樂:聾子作曲,曝光後全網淚崩
微風小說網提供娛樂:聾子作曲,曝光後全網淚崩在線閱讀,娛樂:聾子作曲,曝光後全網淚崩由滄濤創作,娛樂:聾子作曲,曝光後全網淚崩最新章節及娛樂:聾子作曲,曝光後全網淚崩目錄在線無彈窗閱讀,看娛樂:聾子作曲,曝光後全網淚崩就上微風小說網。
23.8萬字8.18 5622 -
完結235 章

分手后,我渣頂流的事被全網曝光了
娛樂圈新晉小花姜云幼,被爆曾渣了頂流歌手宴涔,致其傷心退圈。分手視頻傳的沸沸揚揚。視頻中,曾紅極一時的天才歌手宴涔渾身濕透的站在雨里,拽著一個姜云幼的手,狼狽哀求:“幼幼,我們不分手好不好?”姜云幼只是冷漠的掰開他的手,決然轉身離去。一時間,全網嘩然。都在問她是不是渣了頂流。沒想到,姜云幼在社交平臺上公開回應:“是。”引得網友們罵聲一片。但下一秒,宴涔轉發了這條微博,還配文——“要不,再渣一次?”
40.8萬字8 1329 -
完結508 章

拋我殺我?蘇小姐腹黑歸來
前期小虐+重生+虐渣+爽文+女主超颯,復仇,手撕綠茶和渣男,仇家一個都不放過。爸爸媽媽不愛親生女兒(蘇鳳),卻對養女(蘇雪琳)視若己出。 綠茶+白蓮花妹妹怪會偽裝,搶走蘇鳳的家人和未婚夫. 蘇雪琳聯合未婚夫送她坐了13年的牢獄。 出獄歸來本想復仇,奈何再一次被蘇雪琳謀害,送入緬北,經歷一年半的地獄般折磨。 重生歸來,前世不堪的親情,這一世再也不奢望,她只有一件事,害她之人統統下地獄。
91.6萬字8 178

 上一章
上一章
 下一章
下一章
 目录
目录
 分享
分享
 反馈
反馈